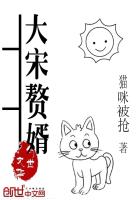额纹。
藏家人刀刻般的额纹。
一个驮在牦牛背上的民族的印记。
弯曲于那张古铜色脸庞之上的额纹,你无论任何时候读它,所获得的感觉都是一种近乎令人辛酸的木纳表情。当然,这是初读。
如果读得久了,你就会嚼出惊喜的特别滋味,那种木纳其实是一种凝固了的虔诚。真的,藏家人的虔诚仿佛都刻在那不动声色的、严厉而森冷的额纹上。
这就是我每次走在环绕大昭寺的八角街上时,看到那些拥拥挤挤地摇着转经筒的藏人的收获。在好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很不以为然这个收获,甚至有几分反感。后来,当这种收获变成整个拉萨给我留下的印象,而且在别处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的思维一下子升华出了这样一个近乎偏执的结论:我们从所谓现代文明把厕所都装扮得像饮食店一样的都市来到拉萨这条僻巷后,你必须校正自己固有的观念。因为这个充满转经简的世界里那种肃穆、厚重的气氛,肯定会把你带到一种真心的祈祷与美好向往相衔接的地方,从而你会不知不觉地触摸到周围那些衣着朴陋,表情冷漠的每个人心里,其实都煮沸着丰富而纯真的情感。这儿起码没有交易所,每一只裸露在藏袍外的赤褐色臂膀都凝聚着沉重的期望。
友人神秘地告诉我:拉萨人在用疑惑甚至仇视的陌生目光审视你的同时,也给了你一分清醒的思考。
这话确实让我深思了许久。
八角街怎么会没有故事呢?它一年年地变老,曾经发生在这儿的故事却永远是新的。
1959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踏上八角街那沉默着的石块砌的路面。天空的灰云像铁块一样压着布达拉宫的金顶。平息西藏叛乱的枪声刚停,千年农奴渴盼的结局还在路上,拉萨才从硝烟弥漫中睁开苏醒的眼睛。路边不时地可以拣到发烫的炮弹壳,不知是什么人的藏靴已经烧成灰烬仍保持着原有的式样扔在路中央。拉萨街头所有的树都没有发芽,包括大昭寺前那棵每年总是率先冒绿的唐柳。唐藩会盟碑成了伤兵,搭在上面的哈达、经幡已经残缺不全。
几乎每座藏搂上都有人探出脑袋来,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八角街虽然少了平日的热闹,仍然有先是零零散散,尔后簇拥而来的身着白皮长袍的各式各样的信徒,沿着这条三里长的环形街一圈一圈地摇着转经筒不紧不慢地走着,每个人嘴里照例念着别人听不清但却能懂得的经语。他们的额纹明显地加深了。
这个春天,拉萨所有的节奏似乎被信徒们手中这迟缓的转经筒摇得放慢了。
一辆给市民送水的军车,来不及挽留就走远了。
我和战友昝义成夹裹在人群中,到八角街的拉萨某地方单位去送一份公文。很不协调,在这藏服簇拥的拉萨世界里,猛不丁地出现了两方国防绿,非常惹眼。那会儿,军人尤其是士兵还不大兴穿便装,我俩只能穿军服上街,而且要带着武器,自卫自然是一方面了,更重要的是为了应付突然情况。八角街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只觉得自己应该多长一双眼睛,方可饱览这些陌生而新奇的藏家风景。
我从大昭寺正前方顺时针方向沿八角街走去——这是藏家的规矩。进入街中不到500米,一处景致便吸引住了我。只见一根竖立在交叉路口的耸入云天的桅杆,挂着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桅杆旁点燃着一大堆散发着浓烈香味的火。一男一女两位衣衫褴褛的藏族老者,领着一个显然刚从蓬头垢面中“修饰”出来的姑娘,手摇转经筒绕着桅杆一圈一圈地转,口中念念有词。周围有许多藏人,有的跟着诵经,有的呆立不动,还有的索性随两老者转圈。凭感觉我看出来了,他们为姑娘祈祷。
我用了“蓬头垢面”这个似乎不妥帖的词儿,完全是想说明这个姑娘很可能是从牧区进城来的。她那被紫外线照成黑红色的脸膛,粗糙的双手以及十分笨拙的走路姿势和很不顺畅的摇转经筒的动作,无不透露着乡下人的小心翼翼。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她的梳妆、衣着、打扮却非常“贵族化”:身穿镶花边的栽绒藏袍,腰系花条长围裙;耳饰、项饰、手镯、指环把她打扮得简直像个金属人似的;她的发型也很特别,三个高高耸起的发髻,呈三角状栽于头顶,每个发髻的顶端都系着一颗圆圆的珠球。三个发髻于脑后编成一根非常漂亮的辫子,长长地垂于身后……所有这些都无法掩饰她牧人之女的原汁原味,反而很让人有一种蹩脚之感。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更不知道二老带着她在做什么。
初次进藏,所闻所见的许多事对我都是谜。
我捅捅昝义成的胳膊:“你知道他们在于什么吗?”
昝说:“我还想问你呢!”稍停,他又说:“两个贫穷的老人!”
我俩止步,凝眸静观这两位老者的形象。他们脸色很黑,人瘦,眼神挂满疲倦。藏袍的表面有一层牧场上特殊的炉灰、酥油、牛羊粪之类的污渍油垢。也就是在这一刻,两位老人的额纹给我留下永生永世都抹不掉的烙印。那是什么样的额纹呢?刀刻的没它生动有神,木雕的难像它深邃丰富。那完全是草原上的风吹出来的,雪山上的霜打出来的。呵,藏家人的额纹,那是最能代表西藏的完美的标志。
我站在人群之外,仔细地看着两位老牧人的动作,那嚅动的嘴唇,那缓慢而有节奏的摇转,那进三步,退两步的双腿……
我确实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我看得很投入。
揭开此事的谜底,是在三年后。那天我坐在临近八角街一条深巷里东赞杰姆阿妈的地毯上,采访老人时她给我讲了这一切……
竖立在八角街的那根大桅杆,在藏语里叫“觉牙达金”,意思是给释迦牟尼佛的供奉。它是用三至四根长长的木头杆子衔接起来的。外围密密紧紧地用竹子裹了一圈,竹层的外面又用刚宰杀的牦牛皮包扎着。风吹日晒雨淋,多日后风干的牦牛皮就紧紧地扎住了木杆。你不必担心风会把杆吹倒,它异常牢固。木杆上飘挂的经幡和轮旗,象征佛教的兴旺,代表佛教法律伦理的尊严。据传,藏王松赞干布建成大昭寺后,八角街上就竖起了这种桅杆,这之前,人们在各自的门口堆起石头堆,寄托对佛祖的心迹。
“觉牙达金”既然是从民间滋生起来的神圣吉祥物,那么出现这样的风俗就不足为怪了:姑娘长到成年出嫁的年龄,要到“觉牙达金”桅杆前举行仪式,一是表示姑娘从此进入成年人,二是预祝她今生来世吉祥如意。
我终于明白了,我那年在八角街看到的那个场面显然是在举行这样的仪式了。让我难以理解的是,看来很贫困的两位老者哪来的钱把女儿打扮得如花似玉?我把心中的疑团告诉给了东赞杰姆阿妈,她听了,脸上罩起一层阴影,说:
“我们藏家人,不分贫富,在姑娘成人后都要到‘觉牙达金’前举行这样的仪式。富家有富家的讲究,穷人也有穷人的办法。你看到那户牧民自然不可能有珍珠、宝石或珊瑚,但是他们可以倾其所有为女儿赶制一身漂亮的衣服,做一双讲究的藏靴。至于珠宝什么的无钱添置,便千方百计地找来假珠饰代替,生养女儿一场,这一天总得风光风光!”
我明白了!
那天,我和昝迈着军人的步伐,挎着钢枪走在八角街上。这完全是执行公务的需要,根本没有威胁藏胞的意思。所以我一再在心里嘱咐自己:放松,一定要放松!然而,难以改变的军人习性,仍使我挺胸昂首地在人头攒动的藏家人中穿行。就像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一样,我并没有十分清醒地觉察到我和昝与这些虔诚的信徒们是多么的不协调呀!直到有两位藏胞出奇不意地突然跪倒在我俩面前时,我才意识到,糟啦,军人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八角街上原来是十分扎眼的。哪怕你有十分善良的愿望。
两位下跪者几乎把头挨到地上,嘴里叽哩咕噜地说着我一点也听不懂的话,但是我可以判断出他们是让我和昝饶恕他们的罪过。说实在的,我并没有发现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更不要说罪过了。我很真诚地上前双手搀扶起两位老人,让他们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我才猛地看清这两位老人正是刚才领着姑娘绕桅杆转圈的那一男一女两个老牧人。他们那破烂得掉索索的藏袍,在寒风中抖索着。旁边一个穿戴很考究、显然属于藏族上层的人物用十分流利的汉语对我们说:“这两个老人是求饶你们不要杀了他们的女儿,他们是为女儿祈祷的。杀人的人佛祖是不会放过他的。”他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挑衅,我正想回敬他几句,他那挂着一把崭新藏刀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人群中了。
两位老人仍旧跪在地上,额头磕着地面。我心里很难受,刚刚平息了一场叛乱,不少藏家人对来到他们身边的队伍还缺乏真实的了解,甚至仇恨带枪的人。也是在这时候,我才看到两位老人的转经筒无声的扔在地上,他们的姑娘站立一旁,不时地抬起怯生生的目光望我一眼。那些围观的人也远远地站着,不说一句话……
这阵子,我反而变得镇静了,昝也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我们根本没有商最就分头拣起了地上的两个转经筒,送到了两位老人的手里。我对他们说:
“阿爸,阿妈,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们是你们自己的队伍,会保护你们的。”说着,我指了指天上,“你们看,拉萨的天空不是已经放晴了么?”
两位老人笑了,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为我和昝祈祷。他们不可能听懂我的话,但是他们肯定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看到两位老人的额头上因为刚才下跪磕头,粘满了泥土,那深深的额纹都填满了土。我忙给老人攘额头,他们赶紧躲开,又摇起转经筒,绕着桅杆转了起来,好像怕我追上去似的,还不时地扭过头看着我。
老人还是怕我们这些兵啊……
我和昝继续沿着八角街的石块路朝前走。
这时,我观赏这条名街的兴趣已经荡然无存。我看着从眼前不时走过的那些驼背、弯腰、艰难挪动着脚步的藏家人,我忧心忡忡地、也是莫名奇妙地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是他们的儿子呢?我确实应该为这样的“拉萨跪娘”尽一份孝心,减轻一点他们的心理负担。可是,我不能,一个小兵,连给他们买一块糌粑的能力都没有,连他们跪在我面前时用藏语安慰他们一句都不会。
那天,我和昝办完事无心拦军车回兵站,坚持步行了20多里路。一路无语。回到驻地同志们正在收拾次日出发的东西,我们都悄无声息地加入到忙碌的人群中。
第一次去拉萨八角街,我心力很重。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对藏族老人给穿着军装的我下跪的情景。我这一辈子都觉得他们总跪在我面前。戳杀,会使一些人死去;和平,能让枯枝开花。哪一个人不懂这个?
每想起“拉萨跪娘”,我都有一种负疚感,责任感,使命感。
因为我是个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