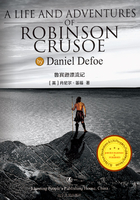青藏高原四季的界限,被仿佛永远也飘落不完的大雪模糊得很难分辨。七月,我在坐落于唐古拉山下的江源兵站一间压着厚厚积雪的小木屋里,正和一位少校及他的妻子畅谈着他们的爱情故事。甜也好,苦也罢,在这个时刻都变成美好的回忆了。兴致浓浓的倾谈使我们竟然忘掉了屋外正是飞雪一泻千里的世界。
丈夫叫陈二位,江源兵站站长。
妻子刘翠,随军家属,待业。
我问二位:江源兵站离八百里秦川的兴平县有多远?
答:少说也有四千里吧!
兴平是他俩的故乡,陈二位1980年一入伍就来到了青藏高原。
我又问刘翠:长江源头离格尔木有多远?
答:一千里只少不多。
昆仑山下的格尔木是部队的家属院,刘翠终年就住在那里。
远山远水,路途遥遥。这夫妻俩的爱情故事便变得凄美而壮丽。我相信这句话了:“距离产生美。”只是这美产生的过程是那样艰难,常常是前脚刚拔出泥沼,后脚又踩进了冰河,有时还不得不伴随着辛酸的眼泪!
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她没想到过起了“随军不随夫”的寂寞生活一九九六年金秋,刘翠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来到格尔木。她虽然辞掉了在老家的一份较为满意的工作,但是一想到从此就能和日思夜梦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失掉的一切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这位心火正旺的年轻媳妇预想的那么美妙。
他们在格尔木家属院的被窝刚刚暖热,二位就接到了要去江源兵站任副站长的命令。
陈二位当然不会对军令讨价还价。然而,把心里的话对领导讲讲还是必要的。他对格尔木大站的一位领导说:“我已经一百四十三次翻越唐古拉山到西藏了。”领导听了笑笑说:“我虽然比不上你翻山的次数多,但是我知道在咱们青藏线上,像你这样的闯山人不会太少。那你就把这一百四十三次当作新的起点,继续攀登吧!”
陈二位说的一百四十三次进藏的里程确实存在。他一入伍就到汽车团,从汽车驾驶员一直干到汽车连连长,每年都要十次甚至十余次踏上青藏线执行运输任务。青藏高原上的每座雪山每条冰河都几乎留着他深沉而炽热的脚印。其实,他给领导说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是摆功,而是想启示领导过问一下他的身体状况。粗心的领导没有透视到下级的内心世界,因而忽略了对他进一步的关怀。当时陈二位因为高山反应落了个头晕的毛病,说有多么严重那倒也不见得,反正一走到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方,就犯病,先是头晕,接着头疼。他是个不会退缩的坚强汉子,咬咬牙就挺过去了,从未给领导讲过。
当晚,二位把自己要去江源兵站工作的事告诉了刘翠。刘翠听了后许久不说话,只是低着头连看也不看丈夫一眼。
二位实在憋不住了,便问:“翠,说话呀,我要上山了,领导让我收拾收拾东西后天就动身,大站首长还要亲自送我去江源兵站。”
原来刘翠哭了,这时她抹干了眼泪,说:“别的我都不担心,就是这高山病折磨着你,不知你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实在让我心有余悸。”
二位安慰她:“高原不比内地,来这个地方工作的人谁能没个头疼脑热的!不要紧,我多加小心就是了。”
“江源兵站的海拔多高?”
“接近五千米!”
“我跟你一同上山,有我在你身边,一切总会好一点的。”
“你净说傻话,那儿海拔太高,上级有规定,不许家属小孩长期居住。去了有危险的!”
刘翠不吭声了。
格尔木是青藏线上各兵站的大本营。因为线上海拔高,缺氧,严寒,荒凉,家属们难以安家,所以部队特地在海拔二千八百米的格尔木修建了家属院,军人的妻子带着孩子住在那里。她们当中离丈夫最远的是一千零八十里;只有遥遥相望,日夜思念,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守空房。她们把这叫做“随军不随夫”。格尔木家属院里军人的妻子们夜夜望着钩在昆仑银峰上的残月,偷偷地咽下了多少相思泪!特别是她们听到隔壁的驻军二十二医院又从线上运下来一个得了高山反应的重病号时,心立刻就提到了嗓子眼里,不住地祈祷着自己的丈夫平安无事。经常也会有这样的噩耗传来:又有一个军人被高山病夺去生命进了昆仑陵园。每在这时候家属院里好几天都是静悄悄地变得鸦雀无声。不幸的事无论发生在哪一家,悲伤的气氛总是笼罩着整个家属院。
昆仑山和长江源头的距离有多长?老司机对刘翠说:你应该知道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吧,就那么遥远!
陈二位上山后的最初日子,山上山下不通电话,也不通邮,他常常把对妻子的思念通过口授给下山的战友传递给刘翠。可想而知,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能传达多少真爱?刘翠每接到这样的口信,不知为什么更加牵挂二位,总想早一点见到丈夫。百闻不如.见,这句话用在这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刘翠终于难以遏制对丈夫的思念,决定上山一趟了。她提前一周将自己的行动日期传送给了二位。她用坚定不移的口气捎过去了这样的话:“我决定这天上山,不改时间。”她知道这样二位就无法阻止她的行动了。过去她多次提出要上山,都遭到了丈夫的阻止。二位总是说:你不要来兵站,这儿条件太差,很苦,你吃不消。至于他自己是怎么吃这些苦的,却不提一字。丈夫越是以这样的理由劝阻她上山,她就越是想上山瞧一瞧那儿到底有多苦。
按照与二位约定的上山日期,刘翠一早就站在格尔木路口拦车了。那会儿,青藏公路上还没有开通旅游班车,她只能搭顺路的便车。一辆又一辆上山的车从她眼前乘风而过,却无一辆停下。
可以理解司机的心情,千里路上捎脚既费力又操心,谁愿意自找这份苦吃?好不容易有一位老师傅怜悯刘翠似的刹住了车,却不阴不阳给她浇了一头冷水。他吊着个脸不热不冷地像审问似的问刘翠:“姑娘,你上山是看老爸吧?”刘翠彬彬有礼地回答:“师傅,我早就成家了,老公在江源兵站工作,我找他去。”老司机听了仿佛更不悦了,反问道:“你知道江源兵站有多远吗?”刘翠摇了摇头。
他说:“你总该知道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吧,就那么远!”刘翠正不知如何回答时,只见老司机把手一挥,说:“上车吧,我就学学雷锋做一回好事!”原来老师傅是个冷面热心人,刘翠边上车边道谢。
按陈二位估摸的时间,一千多里路,刘翠在当日的傍晚六点来钟就能到兵站。五点钟还不到他就站在兵站的大门口等候了。站上的几个兵对陈二位说:“站长,你就在屋里待着,我们在这儿等嫂子。”二位笑着说:“傻瓜,这种事怎么能让人替呢。还是由我来完成这个任务吧!”兵们吐了吐舌头,嘻嘻哈哈地笑着跑开了。
六点钟都过去了,刘翠没有来。陈二位心想汽车不会像火车那么准点,早点或晚点都不奇怪。他继续等着。七点钟到了,天已经麻麻黑了,还不见刘翠的影子。陈二位有些心急了,他在门前走了一阵子,又沿着公路往格尔木的方向走了几百米,公路上连一辆车也没有。他又回到兵站门口等候。
天已经黑得不见五指了,焦急的陈二位心中忽然涌上一个想法,自己这样走来走去,出出进进,妻子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于是他回到站上,点着了一支蜡烛放在窗玻璃处,细心的刘翠即使没有在大门口碰见他,进得站来一看见这烛光烁烁地窗口就会知道这儿便是自己的家。陈二位点好蜡烛又回到了大门口,这时刚好从格尔木方向驶来一辆汽车,停在营门旁,他赶忙上前一看,却没有见到妻子,空欢喜了一场!但是从司机口里得到了一个令他六神不安的消息:离兵站六十里处的地方,有一辆汽车翻了车,一帮人正在夜色里忙忙乱乱地鼓捣车呢!这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二位蒙了。霎时他忘了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立即让站上的司机发动好车子,就向山下飞驰而去,半个小时后,果然看到了那辆翻了的汽车,妻子并没有坐那辆车,他才放心了!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总是那么凑巧,就在陈二位乘车下山找妻子刘翠的当儿,刘翠来到了兵站。当时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整个源头小镇被一片刺刀也戳不透的夜色和寂静笼罩着。刘翠黑灯瞎火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兵站,她是第一次来长江源头,根本不知道兵站在哪个方位。原来兵站离小镇还有二三里地,深更半夜地上哪儿去找?于是,她在好心的司机帮助下,住进了一家小旅舍。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她是睡不着的,她知道二位正在牵肠挂肚地等她,没办法,她只能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盼天亮。她想起了司机师傅说的那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天下的女人为什么都这么多情而命苦?
陈二位自然不知道妻子已经到了长江源头,仍然心神不安地走出走进等候着刘翠。他点在窗口的蜡烛早已燃尽,只留下了一堆蜡泪,他又续上了一支蜡烛,窗口继续闪烁出多情的烛光。
陈二位在公路边不停地走动着,眺望着。他的身影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脚步声远了又近,近了又远。夜色渐渐地被他踏破变淡。东方吐出了曙光……
刘翠终于出现在他渴盼了一夜的视线内。她手里掂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保温饭盒,那是她特地为二位炒的可口的菜,不过,早就冰凉了。她快步走去扑进了他的怀里。
长江源头的晨曦中,这对夫妻紧紧地搂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