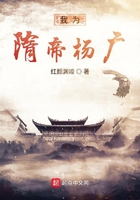李继迁为何会在东胜城里,党崇孝既不知道也琢磨不透。按说李家老二一心巴结辽人,想仗着辽人势大好唆使他堂兄霸了夏州全境反了大宋的话,来这东胜城里转悠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可问题就在这里,东胜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将来李家有事相求的话,不可能不派兵相助。可是个明白人就知道,东胜州里一大半的军权都在库世维的手中,那这李继迁来了东胜城里,为何不去拜访库世维,反而是包了整层的酒肆在这逍遥呢?
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库世维与耶律王六领兵去剿武清军去了。可现在库世维不是已经回来了么,大队人马进城那么大的动静,他李家老二难道就一点也不知道?除非是,李继迁来辽境,求的是更大的官,大到完全可以忽视库世维的存在。只有这样,将来有求时,则只需亮出那位人物的名号来,库世维便不得不从。
党崇孝豁着嘴一个劲地傻笑着往二楼走,脑子里却飞快地转着,想着种种的可能性。李继迁出现在这一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既然让自己给撞上了,就不能这么轻易放了他走。党崇孝想得很明白,对于辽人来说,他与这李家老二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摆在台面上来说,都是在与辽人做交易。党崇孝手里握着的是一笔数目惊人的黄金,而李家手里有的则是相当于两个西京道大小的一个夏州。
如果让金帐里的那位辽人皇帝来选,他自然会选李家,毕竟夏州一旦正式脱离大宋而依附辽国,就好比断了大宋的一只翅膀。可东胜城里既没有金帐,也没有高瞻远瞩的皇帝,有的只是一心向上攀的库世维与耶律王六一众人。
所以即算党崇孝有本事将李继迁杀了,耶律王六这个招讨副使大人也不会在意的。
“站住,你这厮难道没长耳朵吗,没······”
见党崇孝就这样大大方方地上了楼来,一个护卫张口便呵斥,却被党崇孝一个巴掌扇在面上给打断掉了。
“东胜城里什么时候出了你们这几个不长眼的家伙啊!”扇完巴掌后,党崇孝极其嚣张地说道,“知道爷是谁么,不知道就敢当着爷的面这么咋呼,活腻味了是不!”
出来混的,气势最重要。这个简单的道理不仅适用于寻常市井混子,也同样适用于战场交锋上。党崇孝本就是混子出身,在腾威府里闹腾的时候,多半就是靠人多加气势吓住别人的。今天他就吃准了李继迁有怒不敢言,因为党崇孝身边跟着的,可是正儿八经的辽兵。再加上咪洛他们这些与汉人有着明显区别的,个个面色冷峻的党项族牙兵,任谁见了也会犹豫一阵,左右猜测下党崇孝究竟是什么来头才是。
“这位小兄莫要恼怒,都怪在下管束不严,才让这不懂事的奴才冲撞了小兄。”李继迁还真就没弄明白眼前这位面白唇红的少年是什么来头,只见他气度不凡又语气狂傲,可那衣着却又是十分朴素。难不成他就是上京那位喜欢事事都学着汉人的范儿,又常做那微服出行,喜替人打抱不平勾当的公子?想到这,李继迁猛地一个激灵,面上立即堆满了媚笑道,“如若小兄不嫌弃的话,可否赏脸与在下同进雅间饮上一杯薄酒啊!”
望着李继迁那一副作态,党崇孝没来由的一阵恶心。与你一起吃酒,那还是免了吧,咱又不是没钱。不过嘛······
“一杯酒就把爷我打发了,先前你们不是豪气得很吗。”党崇孝伸手环指整座酒肆,轻蔑地道,“整座酒肆的二楼都被你给包下来了啊,这得多大的手笔不是。原本爷心情挺好的,可被你们这一搅合,今儿这酒爷是不想吃了。另外,刚才那护卫吓着爷了,你总得表示表示点吧。”
占了上风就要乘火打劫,这是在腾威府的时候赵嘉祺常说的常用的。因为对方已经在气势上服软了,再顺手打一杆子,对方也只会觉得理所当然。如果党崇孝不这样说,李继迁心中一定会有所怀疑,可党崇孝就这么说了,在李继迁的眼里看来,这就再是正常不过的了。
所以李继迁丝毫不恼怒地从怀中掏出两锭足有二十两重的银子来,笑着塞进党崇孝的手中。
“一点消遣银子,小兄你拿着消气啊!”
用手掂了掂那锭银子,还挺沉手的。党崇孝咧嘴笑道:“好像轻了点啊!”
党崇孝这么一说,李继迁楞了一下。夏州是不产银的,这些个银锭还都是李家自前唐时留下的家底货。今次前往上京拜访南院大王,自是不能带那大宋的铜钱,因此才从内库中拿出几百锭银子来充作一路的用度。可这才入辽境就被人讹去几锭,此去上京还有几千里之遥,一路上未知的花费还不知多少。这要是没了银钱,难不成要变卖掉些许带着的珍玩吗。
可你不给不行啊,没见着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少年,看向银锭的眼神都是那么轻飘飘的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两锭银子他根本就看不上眼。其实他是冤枉党崇孝了,党少爷可不是一个见惯了大笔银钱又或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物,只是他一惯就没怎么自个掏钱买过物事,在腾威的时候全是伊爱帮着拾掇了。到了丰州城,他就更没机会去实际接触这些个事务,寻常听与说的多少多少万贯钱,不过都是些流于口中的数字而已。
也就是因为这样,党崇孝才没怎么觉得这足够换成二十贯铜钱的两锭银子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继迁无奈,他这一路前去本就是预备着去做孙子的,稍有点能耐的辽人,他都不敢惹不想惹也惹不起。咬咬牙,李继迁拉过身旁的一名护卫耳语了几句后,笑着向党崇孝说道:“小兄好手劲,这点轻巧物的确不趁手,请稍等片刻。”
那离去的护卫动作很快,只是几个呼吸便回转了过来,手里还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两排银锭。
看看李继迁的表情,党崇孝怎么瞧着都是一副心甘情愿的模样,于是点点头道:“利格,替我谢谢这位了,这些个银钱你拿去给大家分了。”
利格闻言,瞬时被幸福冲撞得差点就要抱着党崇孝叫上声亲爷了。他跟着库世维做牙兵十几年了,还从未见过这么多银钱。如今这位老爷府上的贵客,张口就将这足足二十锭的银子都做赏赐给了自己几个护卫,这种大手笔这一世怕也就是今儿见着这一次了。
他们这十几个度稽部人虽说都是库世维带出来的亲卫牙兵,可党崇孝的这份慷慨,却足以打动他们在金钱面前原本就不怎么坚毅的心思。于是十几位库府里的辽兵,全双膝跪地行礼,口中呼到‘谢爷的恩赐!’。
利格他们不知道党崇孝姓甚名谁,自然只能是称‘爷’。可这在李继迁的耳中听来,却别有意味。
瞧瞧这派头,瞧瞧这气度,在瞧瞧他身边这些个护卫,李继迁暗道,这也是只有上京里的那位爷才有的啊!看来今次好运,不过是舍了二十锭银子而已,却有机会巴结上这位大人物,不亏不亏一点也不亏啊。
此时,李继迁面上的媚笑更甚了,口中的称呼也变了。“这位爷,老站在这廊间说话也不是个事,要不您移驾去雅间坐坐。”
去雅间?傻子才会应承,万一话多穿了帮,小爷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喽。
清咳几声,党崇孝装腔作势地皱着眉道:“你以为掏出些银子来,爷就会给你这个面子吗,荒谬!如果你真有孝敬心思,就抽空去库府里找爷吧,那是爷在东胜城里的暂居地。”
摇摇头,党崇孝理也不理李继迁,转身便下了楼。身后跟着的是刚得了好处的利格,殷勤的他大力地把咪洛都挤到了一旁,自个像伺候亲主子般屁哈哈地尾随着党崇孝。
这一幕瞧在李继迁的眼中,又是一阵感慨。这一定就是那位爷没错了,瞧这架势,别人就是想装也装不出来的啊。没听他怎么说嘛,暂住的地方都是那手握东胜州实际兵权的库世维的家。想来也是,住在哈音德那可没住在库世维家保险。
待到党崇孝一行出了酒肆半晌了,李继迁这才回复先前那阴沉着的面色,转身回了雅间。
“你真就肯定是他?”
雅间里,一个与李继迁长相很是近似的中年男子,正端着一杯酒轻声问道。
李继迁撩袍盘膝坐在那中年男子的对面,脸色凝重地点头道:“哥,一定就是那位爷,这东胜城里还没有谁有这气量,敢无视门廊上几十个护卫轻率地就上了楼来,还从我这讹去二十锭银子。”
这中年人正是夏州留后李继捧,他点着头盯着手中的杯子,缓缓道:“他说他住在库府是吗?”
“正是!”李继迁很是肯定地说道,“我想,他要不是那位,绝不会有这样的气派,也不会如此轻描淡写。”
“那你就稍晚时去拜访一下库世维吧,咱来了这东胜城连地主也不去拜见下,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是不是。”李继捧锁眉一舒,嘴角浮出丝笑容来,“反正左右都是求人,南院大王不一定就能瞧得上咱拿出的这份礼,可若真要是那位爷在东胜城里,找上他可就比去到上京要有用得多啊!”
这厢李家二位在低声密谋着勾当,那边得了便宜的党崇孝喜滋滋地受着利格他们这些辽兵的奉承。
几个大致知道党崇孝些许底细的辽兵,先前瞧着他的作为还有些不快,可如今党崇孝大方地将银子赏给了他们,在他们的眼里看来,党崇孝比自己的老爷库世维要更亲近得多。库世维可没这么大方过,他自己都想要四处收集银钱好巴结上头,哪会像党崇孝这个败家子这般的慷慨。
所以利格率先拍着胸膛保证说,只要党崇孝在东胜城一天,就一定护卫好他的安全。即算是库世维说往东,利格也会先征求下党崇孝的意见。如果党崇孝说往西,那利格就豁出去的跟着党崇孝往西。
虽说这马屁不一定信得过,可他却拍得党崇孝心里还是爽得很。看来人为财死还真是至理名言啊,党崇孝心道,家生的奴才都能被这点银子给收买了,那这荒诞的世间,还有什么是银子买不到的呢。
正得意着被一众人簇拥着往库府回转,却听到一阵突兀的巴掌声响起。
“好胆识好演技,三言两语的就把夏州留后两兄弟给忽悠得团团转,你这党小鬼的名号还真不是白叫的。”
说这话的是个女子,只是她人在前方的另一处巷子里没显出身形来。话音刚起的时候,咪洛便是一个跃身抽刀向着巷角方向疾去,却又猛地在巷边拐角处定住了脚步。三把明晃晃的弯刀,正架在咪洛的脖子上。见此情形,党崇孝身边的牙兵纷纷抽刀将他护了起来。
利格见状,兴奋地抽出刀来作忠心状。他心里想得很透彻,这位爷出手不凡,身家一定很是丰厚。现在这个局面,自己表现得好一点的话,说不得等会又会有一笔不小的赏赐。因此他一步迈前,嘴里还用党崇孝听不懂的族语叫嚷着其它那些护卫动手。
党崇孝瞧着咪洛被几个身着华服的壮汉架住动弹不得,皱着眉道:“哪家的小娘子在消遣爷呢,就不打算出来亮个相么!”
刚一说完,党崇孝便见得巷角处施施然走出一位少女来。唇若抹朱粉颈柳肩,那一身体贴的十二破留仙长裙,衬着这整个人儿宛如从仙境中走出来的仙女儿般耀眼。只是党崇孝身边还真就没缺过绝色的女子,伊爱是、麦朵是,师娅元悦与元兮同样都是不可多得的美女。这少女虽说气度是不凡了点,样貌是端庄了点,可瞧在党崇孝的眼里,却也只是觉得一般般而已。
那少女先是对着利格这些辽兵说了几句党崇孝同样听不明白的外族语,尔后才对党崇孝道:“你就不怕他们拆穿你的身份?”
看着利格他们一副惊骇得不知所措的神色,党崇孝知道这少女的来头定然不小。再者,她刚才说什么来着,李家两兄弟?难道说除了那李继迁外,李继捧也在那酒肆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里面可就有些机巧了。
夏州两位主事的都到了辽境,这究竟是为什么?
还有这位面生得紧的少女,一瞅她那较为中原人要稍稍宽大些的面颊,很显然是个辽人。党崇孝很是诧异,之前自己从未来过辽地,也甚少与辽人打交道,眼前这位女子是如何知晓自己的身份的呢?
纳闷归纳闷,这话是一定要回的。因此党崇孝很是随意地笑道:“拆穿,拆什么穿。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是谁,又何来惧怕之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