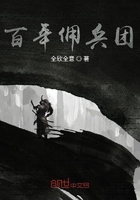我是步行前往大内而没有骑马,一来是坐不惯这颠簸得将人的脾脏都能蹦出来的交通工具,二来是我本就没有置购宝马。
其实步行还有个好处,那就是能欣赏到沿街的风情,还能让我思考一下,等会见了官家老儿该怎么说。不过可惜的是,一路上只顾低头沉思去了,却是忘了环顾四下里的繁华景色。只到感觉身旁的熙攘声逐渐稀去,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邻近大内皇城了。
眼前这片高墙垒筑的建筑群,称不上绝对的恢宏,因为它的前身不过是唐时宣武节度使的衙府,太祖皇帝夺下江山定都于此后,才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建的。
看看东华门那扇沉重的宫门,再抬头望向那高耸厚重的朱红城墙上巍然高出的魏阙,一股敬畏自心底油然而生。这大概,便是对神秘王权的恐惧吧。
“汉子站住,此乃大内禁地,旁人毋许靠近。”东华门旁侍立着一队身披纸甲手持一尺五寸长烈钻的禁军,其中一位都头模样的军官正冲我嚷嚷着。
我翻着白眼,嬉笑着迎上前去,“这位指挥大人,我欲前往大内,不知可否行个方便啊!”
兴许是因为我称他为指挥,那都头的面上稍有些得意之色,不过仍是板着脸道:“你也知道那是大内啊,那你就更应该知道,那里面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啊!”
望着他身后那一群神色嬉戏的禁军,我决定与他们开个小玩笑。“那要随便什么人才能进去呢?!”
那都头听我这么一说,脸上马上变得比先前更要难看,右手握住腰间挎着的手刀就要发火,却听得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大内袛近竟然有人如此不畏的策马奔驰,这可是新鲜事啊。我不免好奇地扭头看去,只见一团火红由远及近迅速清晰起来。
该死,怎地会是她呢。
“党崇孝,你这该死之人跑这来作甚,还嫌命不够长么!”
来人自是那官家的小六儿,公主元兮。我张嘴正欲发言,却被那都头抢了先招。
“叩见六公主殿下!”
元兮勒住马缰,一个跃身下了马来,随手把缰绳递给随从,理也不理那屈膝躬身的都头,径直朝我走来。
“你来这想干什么,难道杀了宋苏乐你还嫌不够,还欲要来这东华门处行刺朝廷大员不成。”元兮只看了我不过两个呼吸,便突地凶狠道,“左右甲士,拿下这个不轨之徒。”
那都头闻言,即地起身抽出刀来,而那队禁军,也哗啦地涌上前来。
这还了得,要是真让元兮这胡闹孩子命禁军将我逮起来,那岂不是小命玩完。我慌忙挥着手道:“且慢且慢,我来这是有事求见官家的。”
可这里元兮最大,她没下令停,这些禁军便只会像是一群见了大粪的苍蝇般继续涌来。哦泄得,这个比喻不大恰当。
元兮得意地瞧着我惊骇失色地退至墙边,一面大声喝道:“抓住有赏,赏钱十贯。不过可别伤着他了啊,谁伤他一根汗毛,可得陪我两贯钱呢。”
这叫什么命令啊,一众禁军全都傻了眼。抓吧,我定会反抗,难免伤着,这刁蛮小娘子的脾性众人全都知晓,那是疯起来便说一不二的主,谁愿意被罚去两贯钱啊!这一月的军薪,也就两贯出头啊!
于是庄严的东华门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幕诡异的场景,我这个身无寸铁且手无缚鸡之力的‘刺客’,被一群披甲禁军围在墙角,却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得前来,就好像我是个人肉炸弹,身上捆在小型核弹一般。
“你们还傻楞着干嘛,上啊!”
元兮在一旁手舞足蹈地指挥着禁军,而我则是气喘吁吁蓬头散发的一脸狼狈,那些禁军也好不到哪去,个个都想着要元兮那十贯钱的赏,却又面面相觑不敢动手,怕被反噬掉两贯钱。
“够了吧,再玩我可就要发火了啊!”我才不管元兮是什么公主不公主的,我心底明白的很,在官家眼里,我现在的分量比起元兮来要重得多,闹到他那去我也不怕,反正是她先胡闹的。
我愤怒地咆哮着,那都头心中却有不满了。毕竟元兮代表的是皇家,而他这个都头食的便是皇家饭。我这样发吼,在他看来自然便是对皇权的不尊重,在向他们这些捍卫者挑战。
于是他也咆哮了,“你这汉子煞是狂妄,公主何许人也,岂能容你如此无礼。来啊,与我将他拿下。”
呃,他还真怒了啊,这可不好玩了。于是在甲士们准备开动的前一霎,我从怀中掏出了那块宫符。“皇上御赐符牌在此,尔等岂敢。”
这一下又让那众禁军头疼了,我手中握着的宫符货真价实,他们这些见惯了的兵士们自然一眼便能知分晓。于是个个又开始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
符牌没有假,出入大内的官员都有这玩意。可是不是御赐,那就没个准了。官家亲手给的物事,那就意味着见物如见人,代表着‘如朕亲临’,可是要行下跪大礼的。如果真是御赐,那跪便跪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要不是御赐,那跪了岂不笑话了去。
一众禁军头痛无比,元兮也是傻楞了一下。不过她迅速地反应了过来,扯着嗓子叫嚣道:“假的,那符牌是假的,父皇怎会钦赐符牌给一个善未脱罪之人。”
“真的,绝对是真的。”我急忙辩解道,“是皇上今早钦赐的。”
这东华门前毕竟元兮最大,若是让她诓了这些禁军去,那我就真是活该倒霉了。
不过那都头虽说听见了元兮的话,却是犹豫不决。他知道这符牌绝不会有假,能随身携带这玩意的人,除了官家的亲信以及身负重责需随时出入大内的高官外,极少有他人还能获赐。毕竟大内是皇家寓所,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资格任意进出的。可这并不能说明,就没有那么一两个极得宠信的近臣获得御赐符牌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比得罪公主更加麻烦。
都头一脑踌躇,那些个禁军们更是郁闷,其中一位凑近都头问道:“咱们咋办?!”
是啊,你们不知道,我同样不知道该咋办。都怪我,好端端的偏地要去戏弄人家都头干嘛,直接掏出符牌来进了宫去的不好么。活该自己倒霉,要在这时候遇上不讲道理的元兮来,要是她狠心来横的,今儿我可真得吃亏。
元兮明显是等得不耐烦了,“怎地还不动手,想抗命是么。”
“这位指挥,你应是知道我这符牌不会有假是吧。”元兮不耐烦,我便更是心急,连忙开口向那都头示好。见他犹豫之下点头认可,我便继续道,“你看我这样也绝不像有行刺之图的刺客不是,只是因我先前与那六公主殿下有些矛盾,才致她见我便生了恼怒。我真是有要事要向皇上禀报,要不你放我进去,在下一定在皇上面前为你及众弟兄们美言几句。”
大概元兮的刁蛮无理是出了名的,这些个禁军们也都是有所耳闻。众人听我这么一说,全向都头投去征询的目光。
“左右,甲士敢抗命,你等上前替我拿了那党家汉子下来。”元兮久等无果生恐有变,随即向身边的仆从们下令。
正在这时,东华门从里打开了。
悠长的‘吱呀’声,打破了门前的尴尬气氛,一位身着玄色素纱的清瘦男子从门内疾步而出。“皇上口谕,着儒林郎党崇孝内苑觐见。”
‘呼’。
真乃天籁之音啊,虽说这宦官那特有的鸭公嗓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过在此刻的我听来,却是无比的美妙。
那群禁军们也全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只是一呼吸间,个个的脸上却又凝重起来。我能想到他们是因为什么才这样,宦官这个时候恰巧出现,这就意味着远在皇宫深处的官家其实早就知晓先前东华门前发生的一切了。他们怕的是,我走之后元兮定会大发雷霆,而当我回转之时,也一定会对他们进行报复。
不过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没必要去为难这些只能身不由己听命而为的兵士们。于是我堆上满脸的笑容,从怀中掏出临来前便准备好的一个装有三百文钱的布包塞到那都头手上。
“刚才不过是误会,别往心里去。大家都是依制办事,怨不得人的。这点小意思拿着,消了职后与兄弟们去吃杯水酒吧。”
我并不是有意收买人心,只是觉得没必要处处为自己留下隐患。不过三百文钱嘛,多不多少不少的,三爷我不在乎。
朝气急败坏的元兮挥挥手,我随在那宦官身后进了宫门,只留下一群禁军们还在原地纳闷。
“有劳大官亲自前来了,还未请教怎地称呼啊!”
官家身边的这些内侍,命虽贱,但潜在的能量也极其之大,不可轻视任何一个。礼貌,那是必然要的。
那宦官也是满脸笑容的应道:“儒林郎客气了,咱家姓朱,唤作大常。”
哇哦,猪大肠啊!这名,还真是起得有够学问的啊!
之后一路无语,随他穿过重重朱墙道道高门,半晌的功夫朱大常才停下脚步来。“进了这迎阳门,里面便是内苑了,官家在橙实亭处读书呢,儒林郎还请自行前往才是。”
点头谢过,我又从怀中掏出一包早已准备好的银钱来塞进他怀里。“有劳大官了,些许酒水钱,还望莫要嫌寒碜。”
他又哪里会嫌少呢,也不推让,只是笑眯着揣入怀中。“如此,便不客气了啊!”末了,又凑近我压低了声道,“官家先前还夸你来着呢!”
我笑了,这钱花得不怨。官家夸我,意味着他心情好,也意味着等会我受到的压力便会小。
皇家内苑是气派奢华的,处处可见各式精致的亭阁散落在极目之处。花坞水榭假山叠翠,令人目不暇接。不过我也是进了才反应过来,偌大一个内苑,没得个向导引路,我又怎地寻得到那橙实亭呢。
不过幸运的是,不远处那散布的披甲禁军表明了目的所在。我大步向前,拐过几条不长的小径便至了那亭阁处。
“微臣叩见皇上,愿吾皇万······”
“好了好了,以后非是正式场合,可免了这些俗套。”官家手一挥,打断了我的话语。“想明白了?”
官家虽然让我免礼,可在未有让我起身之前,我只能是跪趴着答道:“想明白了!”
“我原以为这个时间会长上一点,起码也要一两天的光景,不过你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官家很是满意地点着头继续道,“可是全想明白了么?!”
他仍是不放心,我只好一咬牙斩金截铁道:“温而不躁,缓而不急,能抽丝便彻底剥茧。余下的事,微臣便不擅长了。”
我的意思很明确,我可以帮你将水搅浑,也可以让鱼虾们浮出水面,但你收网之后的事,便不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了。你要杀要剐还是要流放禁锢,那都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官家脸上的笑容更甚了,“起来吧,跪着不疼么。”
废话,我倒是想起来呢,可你没开口,我敢么。
“听说你有酒便有好词,是这样么。”
我愈发觉得官家的思维与麦朵相似,跳跃的幅度之大,常令人跟不上节奏。我犹豫着说道:“只是好事之人讹传,这作词是得看情绪的。”
“我这有十五年的清燕堂,尝尝怎样?”官家向我招手,示意我上得亭阁去。“这可是难得的佳酿啊,还是于先唐的宫城地窖中取得的。一共才六坛,太祖在世时用去了四坛,去年的赏花钓鱼之会时,又用去了一坛。”
我虽不擅品酒,不过当侍女将酒斟满玉杯时,那独特的焦香,还是让我忍不住狠狠地抽动了下鼻翼。
真是好酒啊!
佳酿唯有入嘴细品,才能知道它的魅力所在。这仅剩的十五年清燕堂陈酿,酒气虽说淡雅,不过却是比较醇厚爽口,尤其那余齿的糊香气味,更是让人回味。你一张口吸气,便能享受到那绝无仅有的悠长余味,真真是美煞人也。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酒也就只能是拿来品的,多喝只会乏味,因为度数实在不高,无法让真正的酒君子享受到灼烧的痛快。
想到这,我便是眼前一亮,放下酒杯来道:“这清燕堂比起微臣喝过的银光醇来,更是令人赞不绝口,只可惜空有佳酿之名,却无应有之魂啊!”
“哦,此话怎讲?!”官家老儿被我的话勾起了兴趣,也放下酒杯来盯着我道。
那先进的酿酒之法,我已熟记于心,只是苦于没有找到过了时限的买扑坊场来酿造,又加上随元悦来了汴京,更是没有时间与机会去实践我那造出‘人间最美味’的伟大理想了。
既然我现在是官家手中一颗有价值的棋子,那么适当提出一些并不过分的要求,想来他是不会拒绝的。
“汉时大儒焦延寿曰:酒为欢伯,除忧来乐。”我点头示意一旁的侍女继续斟酒,一边自顾说道,“可现今所谓酿品,皆只能闻其香而馋,饮其味而烦。”
听我这么一说,官家皱着眉道:“饮味而觉烦,你这道理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可有详解。”
我抱拳拱手道:“凡古今佳酿,最深不过欲昏,且耗粮甚巨才得酒一斗。忧天下者,才能知晓饮酒非作乐,而实乃为祸国之所在啊!”
腾威府的老匠霍四早已告知过我,这时的酿酒之法得一斗酒,所耗的粮食比例很大。对比一下我那新法的出酒率,降低粮食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如此一说,官家的脸上就变了好几回色。
我也知道咱大宋的国库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官酒课的收入,禁酒就等于掐断了此项税收重头的来源。可不禁呢,每年耗费的粮食数目,又的确是那般的触目惊心。
“国需强盛才不惧外敌,养兵之所在便是为了安稳。可凡军需皆靠银钱,弓、镞、弩及粮草军俸,样样需银。若禁酒,钱从何来。”
这倒是大实话,当个皇帝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既要时刻提防身边宵小窥觊龙座,又要努力强国壮兵发展经济,事无巨细都得操心,累啊!
我并不畏官家的厉色,摇头晃脑道:“这酒,自然是不能禁的,不但不能禁,还要大肆鼓励国民消费。只要解决出酒的比例大小问题,便无烦忧。”
道理谁都知道,只在于谁敢去实践,且成功论证。我便不怕,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便能让党崇孝这个名字响彻大宋。
官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半信半疑地问道:“你能做到此点?”
“为陛下解忧,本就是为人臣子的职责。”我收回先前的自信,将恭谦浮于面上。“皇上可命人拿来纸笔,且让微臣将那酿酒之法抄写下来。只需按此法子试验一窖,自然可知分晓。”
官家颔首示意侍女去拿纸笔,却又继续问道:“你又是从何而得知的呢,据说你以前可是个口碑一向不怎么好的纨绔衙内,这下作的酿酒匠事,按理说你应是不屑才对啊!”
好嘛,看来你早就在注意我呢是不。不过想想也是,一颗不能控制的棋子,断然不会受棋手们的喜欢。而想要棋子能听话,那就要充分了解他的详细。只有抓住他的弱点,才能令其为自己安心所用。
如此说来,官家能知道我的过去,便不怎么让我觉得奇怪了。
我自然是不能说,那酿酒法子是‘biu’地一下蹦出脑子里来的吧。于是我面色平静地撒着谎道:“微臣过往虽谈不上无恶不作,可也确是有些胡作非为。不过臣本性尚属纯良,以前的种种不过是少不更事。有次臣偶遇一烂赌之徒,他输光了家中所有的银钱,还欠下一笔不菲的钱债。当时那人口口声声说家中有祖上遗传酿酒妙法,愿以三贯之数抵换。”说到这,为了力求让谎言更具真实性,我故作尴尬的神色道,“我的确有些好显摆,也算是败家吧,于是想也未想便给了三贯钱于他。”
“那你可有实验过呢?!”官家不动声色地轻轻问道。
我刚要回答有,却又猛地想到了一件事,随即答道:“还未曾有过。”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咱大宋严令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造酒。与我目前看似得宠无关,这条禁令之所在,是个原则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个底线问题。虽然有些亲王或是高官对这条发令选择无视,在自己府中开炉酿酒,可我不是他们,我只是一个从八品的文散官儿。
回答说有,那就触动了官家的底线。回答说没有,那就得有个说法来证明我所献酒方的真实性。
于是我在官家变脸之前迅速接着道:“臣当时也曾有过怀疑,越想便越是觉得上了当。要知这酿酒由来已久,可所有基本要领都是一样,差别只在原料与火候,又岂会是像那赌徒所说呢。所以臣便请来一位老匠师,让他分辩酒方之真假。依那匠师的经验,虽只是推算,却也得出确实可行的结论。为保险起见,臣又请了多位有造诣的老匠师分别来验对。”
“他们都说可行是吗?!”官家接口说道,“若真是这样的话,功成之后我必有重赏。”
我笑了,笑得无比的诚惶诚恐。“如今正是国家崛起之时,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臣不奢求赏赐。若陛下硬要如此,那就请您将这赏赐,充做军费吧。就当做臣子的,为国尽了一份应尽之力。”
官家明知道我这是在拍马屁,不过他很是受用。“像你这样的臣子,不多见啊!”
又是一语双关,我心中着实懊恼。拜托您每次说话详尽一点好不,别老让我费尽心思揣摩来思量去的,这样可是很累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