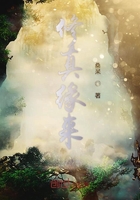1
晨凡在走上楼梯时,心里怀着许多忧虑。她到这里来已经很少有对快乐的进一步的渴望,可她仍然觉得在这里逗留的那些时间是快乐的,即使可能是孤寂的、单方面的欢快感觉,她无法脱离开。
而且她还怀着一点希望,因为晚上待在他这里的女孩子的确就是她一人。
那房间里灯光有点暗,电视屏幕的光则忽明忽暗,显出一些暧昧。那是第一次她单独到他那里,他们的距离忽然变得很亲近,就像久居一个屋子里的一家人,唯独没有那种令人兴奋的情节出现。他们时而地说上一两句话,更多的时间就真的在看电视,他看得甚至有点专心,这让她觉得奇怪。
她不由感觉到这里有什么东西曾经丧失,有人曾在这里失踪。她似乎能感觉到另一个消失了的、但确定又曾在这里的女人,甚至能够接触到那发自隐秘处的呼吸与嘲笑,这使她有瞬间的恐惧。但她很快认为自己这种感觉真可笑,毫无缘由。这样一直到时间很晚了,她说:“我要回家。”
“好吧。”他就说。他就送她回家,一直送到她自己家的楼底下。
结果每次都是这样,他对她很亲切,同时彬彬有礼。
2
女学生晨凡手里拿着一些紫色熟透了的葡萄,她一边走上楼梯,一边让自己飞快地回忆起夏天有一次和他一起去大江里游泳的情景。
阳光明亮,她坐在水泥和石块砌成的很整齐的江岸上,游泳和乘凉的人交织着走来走去。那些湿漉漉光滑的身体在她眼前晃动,那些坚韧的肌肉和柔嫩的肌肤。她望着穿着泳裤的他一次次从水里钻出,身上滴着水珠朝自己走来,宽宽的肩膀令她心动。那时候她觉得他的确是亲切的,与自己没有距离的,仿佛他们已紧偎在一起过。
然而,一回到他的屋里,她不由得对他重新怀着一种敬畏,这不仅仅由于他是她的老师的缘故。
他们并不在一所大学,她和自己的同学兼好友比佳一起到他家认识了他,她们邀请他给自己学校的文学社做个讲座。这之后有一天上午,她在市中心的邮局又遇上他,他看着她的嘴唇(这一点她感觉到了)说:“有时间再去我的宿舍。”她当时没有回答,但过了一天就去了那位于五楼的他的房间。她是在晚上去的,他们随意地聊了一些东西,后来就一起看电视。
他把电视放在卧室,这样,他就靠在床头,而她坐在旁边的一张单人沙发上。
后来每次都这样。她断续(她不是个好说话的女孩)告诉了他自己家的许多情况,还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就像对亲密好友倾诉。他则很少谈他自己。她只知道他一个人在这座城市,一个人住在这座楼的一套房间里。她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或者,他是谁——她几乎都要问这个问题了。
她坐在沙发上,在他的旁边,离他的床有一米。她想,他的怀抱肯定非常坚实,他整个的身体都很坚实吧。想到这,她脸有点发烫。她又觉得这毫无来由,因为他的怀抱实际上不如说是虚幻的。
现在她到了五楼的房门外,她有点不安地开始敲门。这种不安感最近越来越强烈,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对她的态度并没有变化。也可能就因为这没有变化吧。她忽然想到,她是不是也应该失踪了(此时她这样领会了失踪的含意)。
她记起上次他看着她的脚,那脚没有穿袜子,很随便地搁在一双暗色调的皮凉鞋里。她也没有修饰自己的脚,譬如往指甲上涂颜色什么的。她对自己的脸、头发都没有过多修饰与装扮,如果客观地看去,她的嘴唇稍有点厚,眼睛很深,脸两边的线条略微呆板。总的说来,她仍是个漂亮的姑娘。那次他对她说,女孩子的脚还是穿上袜子好,这是否表明他对这一点不满意呢。
她确实有点不安地在期待着他开门,尽管这次她改变了一下。今天她穿了透明的丝袜,皮凉鞋也擦得很干净。
他打开门的时候,他对她一笑,他说:“怎么带葡萄来?”
“今天是中秋节呀!”她笑起来,她的不安和那失踪的想法全然消失去。就像每一次进入这个房间一样,她开始无望地沉浸在亲切与那样冲动的焦虑中。
3
比佳的敲门方式总是很轻,她会重复许多次,最后一次时罗派昂总会听见。
那时候对于大学教师罗派昂来说,晨凡的好友比佳才是自己的性爱对手。(当她们第一次到他家里来时,他就喜欢上那张清纯聪慧的圆脸。)
可聪慧的比佳很少到他这里来,即使他们已经是情人之后。
在此之前她已知道晨凡晚上常到罗派昂那里去,比自己去的次数要多得多,但她对晨凡与罗派昂没有那种关系仅是半信半疑。
比佳不像晨凡那样沉浸于自己的感觉与期待中,她非常明白像罗派昂这样的男人,很难让他做自己的丈夫,或者说他很不适宜于做一个丈夫。这里的原因很多,譬如他对待这个世界过分随意,同时又很苛刻,这从他写的那些诗歌中就可以看出来。这全源于他对抽象的事物过于认真,对具体的物质却常常好像是心不在焉,包括对女人。他也许会沉醉于爱情,如果他相信有爱情的话,但他不会醉心于一个女人。
比佳给自己列出这些她所认识到的情况,她需要这些理由。
当然他很细心,在具体的情境中会极其投入,我也喜欢他的模样。比佳对自己说,她想她也不能忽略自己喜欢他的地方。如当他一开始抚摸她的时候,她的身体总在一种非常宁静的快感中渐渐战栗起来。他会长时间地让她处于这样一种激奋不已的渴望中,最后满足地喊出声。
那时候在冬天,他们在床上把被子完全挤到一边去。比佳细弱的躯体像拉满的弓一样紧张着,她的身体滚烫着,而他在空气中变得滑凉的身躯包容着她,他的汗液湿润着彼此相贴紧的那部分皮肤。
比佳毕业后就去了广东。她才是这篇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个失踪者。
4
有一个晚上,罗派昂听到有人敲门,那人大声地喊:“罗派昂。罗派昂。”他听出来是本市的青年摄影家周到。
周到两年前去了深圳发展,搞广告图片摄影,开了家小公司。周到肯定赚了一些钱,起码不会像罗派昂那段时间正负债出一本诗集。这从周到这时走进门来意气风发的气势就可以看出,他说:“派昂,两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其实罗派昂看周到也是老样子,只是少年老成了些,身上的衣服换成了名牌。他对罗派昂说:“嗨,怎么样,我们找个地方叙叙。”
罗派昂却一下子不能理解:“这里不好吗,屋里又没别的人。”
“不不,我们找个有情调的地方去。”
罗派昂终于明白过来,无奈地说:“好吧,随你。看来你已经有了深圳人的习惯。”
周到哈哈地笑起来。十分钟后,他们走进桃花宾馆的咖啡室,在那里面安坐下来。现在他们可以谈一些与现代生活有关的东西了,有情调的东西,如友谊,爱情,财富……“但不谈艺术。”周到连忙声明。
“你看,那就是艺术。”周到指一指靠墙背对顾客正在弹奏钢琴曲的那个人,那个人的背挺得很直,几乎是正襟危坐。他的头在摇晃,但显得比音乐的节奏慢。显然他没有用心地在弹。但也许周到的指头不仅仅指这个弹琴的人,那里还包括音乐的产生之处。“一小时50元。”他简明地说完这句话。
周到要了一杯叫“蓝梦”的鸡尾酒,和一杯咖啡。罗派昂叹口气,也要了一样的,他一面看着酒单说:“这些酒的名字都够诗意的。可惜也都矫揉造作。”
“正是这样,这世界需要装饰。你不能剥夺它这个权利,对吧。你不正是一个装饰者么,我以前也是。现在还有一大半是。”
“我不会去装饰它的。我从没有这样做过。”罗派昂冷冷地说。
“所以你穷。”周到不客气地指出。罗派昂不再说话,他的心中升起很熟悉的一种感觉——他感到茫然。可实际上他并不很在意这一点,他端起杯子喝一口咖啡,说:
“咖啡不错。”
5
“你还记得樱英吗,那个歌手。”周到探过身子像是十分随意地问。
“记得。”罗派昂回答。“一个挺活泼的女人,好像嫁了一个北方人吧。”
“已经离婚了。她现在一个人在深圳。”
“那她还在唱歌吗?”
“在歌厅唱,在那边还有点名气。她说如果你去深圳,她想和你见面。”
周到这样说后,就盯着罗派昂的眼睛,一边咧开嘴含意丰富地笑着。
罗派昂似乎有点清楚周到话中的含意,但他又不很明白。他也不好意思深问,他说:“好吧。”
“真的,你到深圳,费用我出。”周到加重一句。这倒让罗派昂有些犹豫,他说:
“到时候如能去,我跟你联系吧。最近我忙着印我的诗集。”
“那好,我后天就回深圳了。”周到说着递过去一张名片。
现在事情的缘由已变得不那么清晰,对于罗派昂说来,这次会面可能被涂上了另一种色彩,它的实质变得模棱两可。走出咖啡室时,他的脑幕上突然浮现出樱英的一个唱歌画面,穿着火红的裙子。他想起那是她印在她的磁带专辑盒子上的照片,他曾经看见过。他接着却想到晨凡有一段时间没有到自己这里来了,她是否已经毕业。她的家就在本市,她应该不会像比佳那样到别的地方去。可她为什么如此不告而辞,像失踪了一般。重要的是,她们都在成为自己生活中的失踪者,他想到这一点,继而忽发奇想——是否他谋杀了她们,使她们消失。他沉落于想象中,显得情绪不振,周到拍拍他的肩膀,说:
“我们在此分手吧,记住跟我联系。”
6
后来大半年里,罗派昂一直都没有去深圳。他的诗集印好了,他忙于销售,给读者邮购,收回钱还印刷厂的债务。晨凡也一直没再到他住处来。
这时候有一个叫李晴的女孩以一种孩子气的方式出现在罗派昂的生活中,她在他生活的空中滑过去,像一只城市上空的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