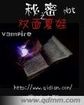视线中终于出现了一栋建筑物,我几乎要感激到涕泪俱下,然而我忘了世上还有一句话,望山跑死马……看起来十多分钟的路程,在加上下山、过河、上山之后,真正抵达那个颇具古意的素墙乌瓦竹篱笆的清秀院落,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的事情。我直觉这里并非重华的居所,因为不适合。
束晟继站在篱笆外头说了一段很长的文绉绉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家里有人吗没有人的话我们就进去了”。没有人答话,所以我们进去了。
院子里种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花,最小的花朵也有海碗那么大,色泽娇嫩明艳,据说太美的东西都有毒,我们匆匆走过花田。门大开着,然而垂下细密的竹帘,随着我们走近,竹帘自动卷起,嗯……还是感应式的,很先进,很先进。竹帘后有一张竹榻,榻上卧住一个白袍青年,他放下手中书卷,抬眼看向我们,客气地笑了笑,顿生一室春风,好一个形容磊落,气质儒雅的古典美男子,和这屋子真是相得益彰。然而细看之下,他的双眸似黑非黑,近乎一种极为幽深的蓝,隐隐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邪气。
白袍青年笑完了之后张口就道:“外热内冷,慧而无心,薄情寡恩,恐非佳偶。”
我愣住了:他这是在说啥?
似乎是知道我们听不懂,白袍美男的袖子甩一甩,空中出现十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外热内冷,慧而无心,薄情寡恩,恐非佳偶。
这里是婚姻事务所吗?我有些黑线。
束晟继倒是淡定:“请问这位先生,这十六个字在说谁?”
白袍青年倒也不客气:“自然是说这位姑娘。”
外热内冷,慧而无心,薄情寡恩,恐非佳偶?我的人品有这么差么?
束晟继不悦地道:“先生缘何口出恶言?”
“世人为什么总是不愿意听到真话?”白袍青年悠悠发问,态度极为泰然,浑然不觉自己已经得罪了人,而且还在继续得罪人。
我瞥向他搁在竹榻上的书,《涅朵琦卡》。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还真的是一个读书人咧,看这么偏门的小说。看在大家都是阅读控(?)的份上,我决定原谅他的大放厥词。轻轻扯了一下束晟继的袖子,提醒他我们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微笑着看向白袍青年:“请问先生,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微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来做什么?”
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决定不把乱指路的小女孩供出来,嘿嘿一笑,我道:“路过,路过。”
他继续微笑:“哦?能路过此地倒是难得的缘分。我便免费为这位姑娘改一下命盘吧。”
“改命盘?”我赶紧摆手:“这个就不劳先生费心了,其实我赶着回家睡觉,您不嫌麻烦的话,把我送回我家的浴室吧——我要刷牙。”
他笑了笑,正要说什么,脸色忽然大变,我还没看到他动呢,他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伸手扼住我和束晟继的脖子:“你们是人!”
我眨了眨眼睛表示赞同。
“人怎么会到这里来?”
我也很想知道呀!
他松开手,掐指一算,脸色更加难看:“你们居然伤了小西!”
咦,他说的是“伤”还是“杀”?这两个字音挺近的,不大好分清。他的表情如此恼怒,那条女白蛇和他是什么关系?我看向他,他也穿白衣服,根据什么蛇穿什么衣服的仙侠小说基本定律,他该不会是那条女白蛇的哥哥或者爸爸吧?
白袍青年的视线在我和束晟继之间转了一个来回,怒极反笑:“你们倒是有本事。居然伤得了小西。”
这一次我听得很清楚,他说的是“伤”不是“杀”,原来那条女白蛇没死啊。
我决定在他追究我们责任之前,把话题导向我们的来意:“请问这位先生能不能算出来是谁把我们掳来?”
白袍青年的语气十分不善:“掳来?”
“是呀,我本来是要去刷牙然后睡觉的,结果一开门就被一条藤蔓卷到这里来了。”
白袍青年很明显不相信我的话:“水月妙境哪有这等事?我从未听闻。”
我指出他的逻辑错误:“刚才我说了,所以你已经听闻了一次。”
他看向我,冷笑一下:“原来不止是外热内冷慧而无心薄情寡恩,还要加上饶舌多口气量狭小锱铢必较。”
要论饶舌多口气量狭小锱铢必较,你和我比起来也毫不逊色吧?当然,识时务如我,这句话只是在心里说一说。
束晟继恭恭敬敬地做了一个揖:“先生大人有大量,然则我们也并没有说谎,的确是莫名其妙就进入了这个地方,不知先生能否把我们送回去?”
白袍青年冷淡地道:“把你们掳来的又不是我,我为什么要负责送人回去?”
“……”我讨厌这个地方,然而我还得继续赔笑:“太子在哪里,先生可否指教一二?”憋文言文真痛苦……
白袍青年露出一点讶色:“你们找太子何事?”
这个自然是问路了。我微微笑一笑:“见到太子就知道了。”
他雍容一笑:“我正是太子。”
“……”我小心翼翼地道:“你该不会是姓‘泰’名‘梓’吧?”
白袍青年哼了一声:“区区人类还不配知道我的名讳。”
我在心里吼一声:俺不是人类,俺是神之子!我略想了想,把重华的名字抛了出来:“先生认识重华吗?”
白袍青年的语气十分冷漠:“重华?那是什么东西?”
这个回答到底是不认识还是认识但是和重华不对盘?都说了我是人际关系苦手,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卷进旁人的恩怨?我痛苦地问道:“先生不认识重华还是不屑于认识重华?”
白袍青年看向我,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外热内冷,慧而无心,薄情寡恩,这样的女人配他倒是刚刚好。”
“他?”这个他该不会是重华吧?
白袍青年一伸手就把我抓了过去,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把扇子在我头上身上到处乱敲,虽说不怎么痛,但莫名其妙被打一顿还是很让人火大的,我无奈地看向他:“先生这是在做什么?”
白袍青年笑道:“自然是改你的命盘让你和他做一对白头到老的怨偶。”
这个他到底是谁呀?我要抓狂了!
束晟继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要把我从白袍青年的魔爪下救出去:“更改命盘乃逆天之举,必受天谴,先生何苦损己不利人?”
白袍青年笑容狷狂之极:“天谴?那种东西我可没在怕。”
拉拉扯扯之间,一个美女走了进来:“若即,你在干什么?”
白袍青年忽然撒了手,我和束晟继一起摔倒在地上。白袍青年把扇子藏到袖子里,笑道:“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有两个路过的来问路。”
美女生得温婉秀丽,声音也是说不出的柔和动听:“路过?”她一脸迷惑:“怎会有路过的?结界坏掉了吗?”
“结界?”我和束晟继面面相觑,我们根本没看到那种东西。
白袍青年冷冷地道:“阿姐,他们是人。”莫非这个结界只防妖不防人?
“人?”美女吃了一惊,又往我和束晟继这边看了一眼:“当真是人!”
美女蹙起眉尖:“水月妙境里怎么会有人?”
白袍青年冷笑道:“他们居然说是被掳来的,真真好笑!”
美女走近我,笑着执起我的手在竹榻上坐下:“这位姑娘如何称呼?”
白袍青年跳脚:“阿姐,你怎么叫她上我的榻?”
上你的榻又不是上你的床,激动什么,我闷闷地道:“我叫相梦梦。这个是我的……朋友,束晟继。”美女的手好软,而且好冰……果然也是蛇。
“相姑娘的名字很好听。我名叫若离,那是我的弟弟若即。相姑娘,你和这位小兄弟是被谁掳来的?”
若即……听起来感觉好像弱鸡……这名字太逊了!不过配那种怪脾气的人正好!我心里很痛快。
束晟继被当成了我的跟班,他的面色顿然一沉,不过没办法,谁叫我长得比他老?
我笑了一下,对美女大致解释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若离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此事当真是闻所未闻,且容我禀明长老,弄清楚事情原委之后再送二位回去。”
“禀明长老?”我故意道:“公主做事还需要禀明长老吗?”
若离笑了:“相姑娘怎么会说我是公主?”
若即瞪了我一眼,我才不管他的威胁,笑眯眯地道:“若即先生说他是太子,那太子的姐姐自然是公主啰。”
若离脸色一沉:“若即你怎么可以拿这种事情胡言乱语?”
哼,我就知道他在说谎。
若即讪讪一笑:“我开玩笑的。”
若离苦笑:“这也能开玩笑?我看是我把你宠坏了。”
若即黏上来在若离身边坐下:“阿姐宠我是应该的!”
若离转过头去在若即头上揉了一把:“坐好。”
我和若即对视,无声地做了个嘴型:恋姐狂!
****************************
第三个美男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