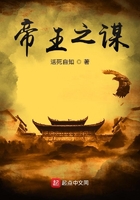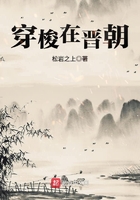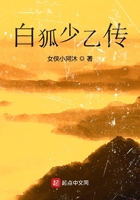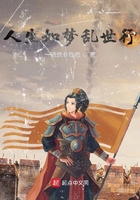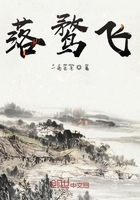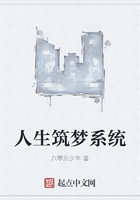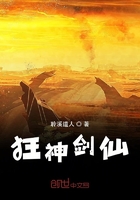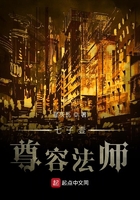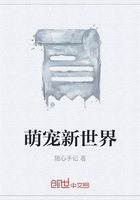于谦担当起拯救明朝的重任时,京军的劲甲精骑都已在土木堡陷没,所剩的疲卒不到10万,北京城人心震恐,对于能否守住京师,没有信心。于谦奏请成阝王调遣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火速开赴北京,组织起保卫北京的铜墙铁壁。当时通州存放着数百万石粮食,朝廷又无力派兵保护,一旦遭到进攻,势必成为敌人的粮饷,若是放火烧掉,人民的血汗白白浪费,十分可惜。于谦于是请命文武京官预支本年10月到明年6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粮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又征用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粮进京,同时号召人民有车之家,每运粮20石入京仓,给脚价银(运输费)1两。他又请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旧操舍人(军官子弟)及应募新兵每人银1两、布2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四门内外官军每人布2匹。于谦有条不紊而又迅速地部署了北京的城守,人心因此安定下来。
9月19日,成阝王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21日,成阝王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没收其财产。成阝王未明确答复,群臣同声放哭请愿,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恶言叱骂群臣。给事中王竑愤怒而起,冲出朝班,挥拳击向马顺,群臣蜂拥而上,把马顺即时击毙。随后又打死王振私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二人。稍顷,又捉到王振的侄子王山,将他捆缚跪伏在殿陛前,众人争相向前唾骂,卫卒汹汹,一时朝班大乱,内外喧动。成阝王害怕,想起身退避。于谦挺身排众上前掖住成阝王,请他当即下令:“马顺等人罪当死,打死不论。”情势于是安定。而于谦的袍袖也全都撕裂了。这场朝臣与阉党的撕打,事起仓促,于谦处理很为得宜。当他缓步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上前拉住他的手说:“国家正有赖于公。今天虽然有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用!”吏部是六部的首席衙门,有关国家大事的廷议,一般由吏部尚书牵头,王直的这番话,表明了朝官对于谦的佩服与支持。成阝王下令,将王山缚赴西市,凌迟处死。又令将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一概斩首,家产籍没。
次日,于谦即着手调换整饬各边镇要塞将领。他荐举廉正刚直的右都御史陈镒安抚京畿内外军民,请封杨洪为昌平伯,仍与罗亨信、朱谦等人镇守宣府。原来“土木之变”后,也先曾在9月4~5日,挟英宗攻宣府,逼迫英宗三次命令杨洪开城,杨洪都予拒绝。当时罗亨信仗剑坐城楼,下令说:“出城者斩!”因此军士决心守城,也先见不得逞,乃引兵西去。成阝王赐谕褒奖杨、罗等人。
于谦又荐举强干的官员守卫北京附近的各个关口。另外,石亨从阳和战败逃回,贬官下诏狱。于谦认为他熟习军事,特请赦免起用,总领京营兵。
古人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当时明朝皇帝被俘,太子又幼小,大臣们很是忧虑,便请求孙太后立成阝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当即首肯,成阝王却吓得躲进了王府。他对群臣说:“有皇太子在,卿等何敢乱法?”群臣不敢发言,于谦正色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成阝王才答应做皇帝,于9月22日举行登基典礼,史称景帝。同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样,明朝失君又得君,英宗在也先手中由奇货变成了空质。后来当他挟持英宗诱使各城镇守官员打开城门时,听到的回答是:“感谢上天保佑,大明有君了。”
10月1日,于谦又推荐坚守大同的副总兵官郭登升任总兵官。大同和宣府是屏蔽北京西面的两大重镇,而大同更为重要。二城不丢,虽然也先能兵临北京城下,但终究有归路被切断、陷入进退维谷局面的危险。
同时,于谦整顿军纪,选拔新进将领操练军兵,分守九门要地,列营郭外。
17日,也先和脱脱不花汗挟持英宗,统率瓦刺骑兵再次入犯明朝,目标直指北京。
24日,景帝授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节制各将士保卫北京。于谦调遣诸将分领官军22万人,在京城九门外严阵以待:武清伯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等列阵德胜门外,同时石亨节制守城诸军。都督陶瑾阵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朝阳门,都督刘聚阵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阜城门,都指挥李瑞阵正阳门,都督刘得新阵崇文门,都指挥汤节阵宣武门。
25日,瓦剌骑兵从紫荆关、白羊口两路进攻北京。石亨建议全军退守城内,坚壁清野,以避贼锋。于谦坚决主张出城迎击,说:“奈何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们。”便委派兵部侍郎吴宁代理部事,亲自率军布阵德胜门,迎击瓦剌主力。下令:“有盔甲军士而今日不出城者,斩!”待部队出城部署就绪,即尽闭诸城门,并颁布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们知道是背城死战,人人效命。
27日,瓦剌进逼北京,列阵西直门外,将英宗放在德胜门外。当天,于谦派副总兵高礼、毛福寿迎击瓦剌军于彰仪门土城北,败其先锋,斩数百人,夺还所掠人口千余,明军军威大振。夜间,又派薛斌等人潜袭敌营,有所斩获。也先此次入寇,以为北京唾手可得,未料明军严阵相抗,撄其兵锋,意气稍沮。降将奄喜宁教也先借口讲和,派使者邀明廷大臣“迎驾”,以试探明廷内情。
也先的计谋被明廷看破,只派了几个小臣前往。也先不与交谈,再次要求明廷派遣大臣前去。景帝倾向议和,使人问于谦,于谦坚决主张抗战,不遣使臣。
30日,瓦剌军与明军在德胜门外展开激战。于谦先让石亨领兵埋伏于道旁空屋,另派小队骑兵击瓦剌军阵,接战后,佯装败退,也先即刻率精骑万余猛追上来。待也先军近城,于谦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随后石亨伏兵骤起,前后夹攻,也先军惊乱,明军副总兵范广跃马当先,冲入敌阵,部众齐上,奋力搏杀,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平章孛罗印那孩,号称铁颈元帅,被明军火炮击毙。
瓦剌军转攻防御较弱的西直门,都督孙镗率明军力战。正当孙镗力渐不支,退迫城门时,石亨领兵从北面赶到。明军三面环攻瓦剌军,也先只得向西南退去。明军与瓦剌军的第一次大会战,以瓦剌的失败告终。
31日,瓦剌军又进逼彰仪门土城,遭到明军伏击。于谦又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率军出击瓦剌军于彰仪门外。明军前队用神铳火器冲锋,后队列弓弩短兵继进,击退瓦剌主力。这时,监军太监想要争功,领数百骑驰马抢前,明军阵乱,武兴不幸中流矢牺牲。瓦剌军乘机反扑到土城,这时北京居民纷纷跳上屋顶,飞投砖瓦,打击敌人,喊声震天地,瓦剌军惊愕不敢进。适逢黄垓、毛福寿、高礼率军来援,瓦剌军望见明援军旗帜,仓皇退去。第二回合会战,明军又取得胜利。
瓦剌军在北京城外,先是玩弄“迎驾”,诡计不成,后经5天激战,屡战屡败,死伤很多,士气低落。这时山西、北京的人民也都自动组织起来阻击瓦剌军的分散劫掠,瓦剌别部5万余人围攻居庸关7昼夜不得逞,反被明兵部郎中罗通屡次抄袭。也先面对前阻坚城,后有归路断绝的危险局势,非常沮丧。
11月1日,瓦剌军夜间拔营潜遁,也先挟英宗先行。于谦侦知,立刻令石亨连发大炮,轰击敌营,瓦剌军死者万余。也先等向良乡方面退去。撤退中,烧了昌平明朝皇陵的享殿祭器,又抢掠州县,受到当地人民的抗击。如王伟在广平县善于鼓励民兵守城,被于谦破格推荐做兵部郎中。
于谦又派孙镗、范广领兵两万追剿瓦剌游寇。到11月23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宣布解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把明朝从败亡的边沿上挽救了回来。事后,论功行赏,景帝升加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京师稍见稳定,但要重振国威,雪国耻,还需要卓有成效的努力。北京保卫战后,于谦又着手加强了北部边防的力量,整饬边将,让他们树立战守到底的决心。又用计擒杀了叛将奄喜宁、间谍小田儿。
也先在北京城下受挫后,又多次派兵骚扰明朝的边境,均未得逞。眼看武力并不能屈服明朝,英宗变成了空质,战争状态又使蒙古失去了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从明朝获取大量生活必需品和赏赐的机会,也先便决定与明朝讲和,送还英宗。
也先要送还太上皇,大臣们很高兴,议遣使迎归。景帝不高兴地说:“朕本不想当皇帝。当时被推戴,实在是出于卿等。”于谦和颜悦色劝解说:“陛下的天位已经定了,怎么会有变化呢?臣等的意思是,奉迎上皇回归,不过是证明也先讲和有无诚意。即使也先怀诈,我们也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景帝听了他的话,才恢复了笑容,说:“从汝,从汝。”先后派礼部右侍郎李实、右都御史杨善充当使者前去迎接英宗南归。
1450年9月1日,英宗当了一年的俘虏后,终于回到北京,在南宫(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面外交学会院内)做起了幽居的太上皇。
在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君王被外族掳去,又无条件地放了回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是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是在于谦等爱国英雄的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胜利。但于谦并没有因此而懈怠。他及时提醒朝廷上下:“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又积极整饬军备,改革体制,加强实力。
拥有一支强劲的京军,是京师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为此,1451年(景泰二年),于谦改革京军三大营的旧制,创立了团营。团营初创时,从三大营中挑选精勇军士10万,编为五营操练。第二年,又将团营军士增加到15万人,分十营操练。到1453年1月,团营制度完全确立。每一团营有军士15 000人,置都督一人统率,叫作“坐营都督”。以下设都指挥、把总、指挥、领队官、管队等各级指挥人员,分统军士,大小联比为一团营。十团营设一总兵官,由石亨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的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做监军。团营不同于三大卫的地方,主要在于加强指挥人员与军士之间以及上级统帅与下级军官的联系,让他们相互熟知,从而增强战斗力。管军官必须熟记每个军士的姓名、年龄、相貌以及卫所番号。战时调遣,不再更调将领。因此,“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不但提高了京军的战斗力,而且节省了军饷。
从各方面看来,景泰时期,明朝的军队和国防,在兵部尚书于谦的整顿下,出现了新气象,国防渐趋巩固,国威重振。
也先从北京城下大败而归,后来多次抄掠明边又不得逞,在蒙古各部中的威信大为降低,于是瓦剌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起来。1451年,也先率部攻打脱脱不花汗。脱脱不花被兀良哈部首领沙不丹杀死。1454年,也先自立为可汗,次年,为阿剌知院袭杀。不久,鞑靼别部酋长孛来又攻杀阿刺,夺去也先的家属及玉玺。自从也先死后,蒙古各部的联合便告瓦解,而瓦剌各部也陷入分裂,纷争不已,势力日衰。可见,于谦的坚决抗战,使蒙古在军事上陷于失败,从而内部矛盾扩大,也就间接促成了也先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