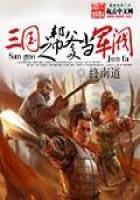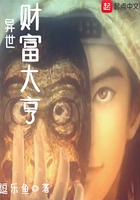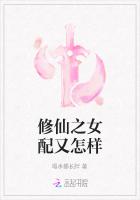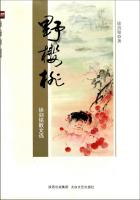政治腐败的显著表现,就是宦官干预朝廷政治。而宦官干政,则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一大痼疾。不过,这个疾病,在皇帝圣明雄武的时候患得轻一些,在皇帝童昏无能时患得重一些。明朝的宦官之害,从英宗开始,一直伴随到明朝的灭亡。其他干政的宦官,后面还要讲,这里先来看看英宗正统年间的大宦官司礼太监王振。
前一章已经讲到,在英宗的父亲宣德皇帝统治的时期,就确立了司礼监和内阁的双重辅政体制。这种体制,为宦官干政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
司礼监和内阁的作用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臣下请示政务指示的章奏先上交到皇帝那里,皇帝就派宦官转给内阁的大学士们,让他们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这种意见用黑色墨汁写在一张纸条上,就叫做“票拟”。阁臣通过票拟,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起很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不过,阁臣的票拟必须通过皇帝的“批硃”,才能变成对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式指示。所谓的“批硃”,又叫“批红”,就是皇帝用红色的笔,在章奏上直接批写指示。批红一般是照抄票拟,但皇帝对票拟不同意时,就让阁臣重拟。阁臣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皇帝又不愿接受,便直接按自己的意思批红。有时候,臣下的章奏太多,批不过来,皇帝就将批红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去做。皇帝犯懒病时,就更是如此。这样,司礼秉笔太监就成了皇帝的代表。他们在代表皇帝行使批红权时,可以对阁臣的票拟提出更改意见,往往得到皇帝的许可,这样,他们凭借批红的权力就可以钳制内阁。
司礼监太监、阁臣与皇帝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阁臣与皇帝之间是一种臣与君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儒家的信条是“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也就是说,对皇帝的忠是有原则、有保留的。而且阁臣全都出身儒士,信仰孔夫子仁义礼智那一套,是文官和国家长远利益的代表,对皇帝有损于国家长远利益和法制纪纲的行为,往往持不合作的态度,因此,皇帝与阁臣之间常有矛盾、冲突。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就阁臣的职能来说的,并不排除有的阁臣放弃信仰与原则,去奉迎皇帝与太监。不过,这样内阁就没有履行他正常的职能。
司礼太监则是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他对皇帝的忠是无原则的绝对的忠,是皇帝利益的代表。所以,皇帝一旦信任他,他的权力就远高出内阁。当然,宦官的权力太大,难免出现“太阿倒持”的局面。汉、唐历史上宦官擅自废立、甚至弑害皇帝的事,屡见不鲜,就是教训。作为明朝的开基者,太祖朱元璋对这种教训是有深刻认识的。但他并不想放弃宦官这个维护皇权的工具。他对这个工具作了一些改造,让宦官的权力有所制约。虽然后来宦官有预政、出使、专征、镇守等权力,但是各宦官之间、宦官与文武官员之间,都有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尽管宦官的权力很广泛,却没有出现宦官废立皇帝的局面。司礼太监不能同时掌握军权,也就不能废立皇帝。不过,他掌握的批红权就足以扰乱朝政、破坏国家法纪了。司礼太监王振便是借这一权力败坏了正统年间的政治。
王振是山西大同府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教官出身。教了9年书,没有什么成绩,按照规矩,要被贬谪充军。眼见就要一辈子翻不了身,永乐帝下诏,这类遭贬充军的教官中生有儿子的,允许净身入大内,给宫女当老师。所谓净身,就是割掉生殖器中的精巢,也就是阉割。王振一狠心,就把自己给阉了,入宫当了宦官。
宣德时期,虽然设有内书堂专门培养小宦官,但宦官的整个文化素质并不高,多是仅能识字而不知文义,王振这位知识型的宦官便显得鹤立鸡群,才能高出同辈。为此,宣德皇帝对他高看一眼,让他进司礼监当了秉笔太监,又让他伺候皇太子读书。
这位皇太子就是英宗朱祁镇。1435年1月,宣德皇帝去世,英宗继位。英宗当时虚龄9岁,实足年龄是7岁零2个月,是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孩子,一个童昏皇帝。小皇帝来日方长,可塑性大,成为王振与辅政大臣的争夺对象。
在这场争夺小皇帝、实际上是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辅政大臣们采取了为小皇帝举行经筵的办法,希望把小皇帝培养成儒家理想中的圣明君主。所谓经筵,就是给皇帝讲授儒家经典。这些干涩枯燥的东西当然无法吸引一个9岁的儿童,而仪式的繁缛,对童心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如果说这种教育方式取得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培养了小皇帝傲慢自大、一意孤行的意识。
然而,在司礼太监王先生那里,小皇帝的童心得到了充分满足。王先生给他安排了观看军事比武、骑马射箭、游园踢毬等等有趣的节目,还教他如何调弄大臣,建立权威。
1437年1月(正统元年十二月),小皇帝让兵部尚书王骥、侍郎邝野讨论边防问题,5天过去了,未见回奏,王振教小皇帝召见王骥,当面斥责他:“卿等欺朕年幼耶?”把王骥、邝野关了好几天禁闭,吓得群臣出了一身冷汗。
不久,右都御史陈智弹劾辅政大臣之一的英国公张辅回奏稽迟,又弹劾六科、十三道不能举奏。小皇帝开释了张辅这位“靖难功臣”,听从王振的意思,将科、道官各打20大板。这样,王振就借小皇帝的威权大灭了辅政大臣的威风。从此以后,言官们奉王振的旨意,专找那些瞧不起王太监的大臣的差子,自公、侯、驸马、伯到尚书、都御史,以及以下的官员,无不遭受弹劾,或者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戴上项枷,甚至被贬充军。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王振在与辅政大臣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英宗刚即位时,日常的大政由他的祖母张太后和辅政五大臣主持,王振只是利用怂动小皇帝的惟我独尊的意识来干预朝政。到1441年底,英宗年满15周岁,开始亲秉国政,全面履行皇帝的权力,王振的干政就发展到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辅政五大臣更不是他的对手,纷纷采取将顺苟且的态度,持禄保位。
王振左右国家大政方针的确定,造成了边防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最终挟持英宗亲征,导致驾陷土木堡。
最大的失误是旷日持久地兴师麓川。麓川是指明朝的土司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位于今天云南西部腾冲县西南。所谓土司,是元朝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民族自治制度。土司的长官和各级官员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中央政府加以认可。土司只须向朝廷缴纳象征性的贡赋。当时,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刚迈入文明社会不久,各部族间经常发生互相攻杀、抢掠人口、霸占土地的事情。1428年(宣德三年)以后,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多次率兵侵占邻近土司的地盘。1438年(正统三年),明廷兴十万大军,历时三年,遭受重大损失,才打败思任发。思任发派人到北京朝贡认罪,请求明廷饶恕。明军虽未取得辉煌战绩,但已达到震慑思任发的目的,面子上也过得去了。战争本来可以就此结束,然而王振、兵部尚书王骥都想借战争建立功业,稳固自己的地位,加官进爵,极力鼓动英宗坚持将战争打下去,把思任发逮捕归案。1441年,麓川战争又重新开始。
在明廷大规模出师麓川之前,翰林侍讲刘球上《谏伐麓川疏》,援古证今,指出明朝的边防重点在西、北蒙古,而不在滇西南麓川的弹丸之地,英宗不听。
1443年6月,雷震奉天殿,刘球应诏上奏向英宗提出十条建议。核心的建议有两条:一是请皇上亲揽大权,不要旁落;二是要停止对麓川的用兵,将防御重点转移到北方。他强调指出:“麓川荒远偏隅,即叛服不足为中国轻重。而脱欢、也先并吞诸部,侵扰边境,议者释豺狼攻犬豕,舍门庭之近,图边徼之远,非计之得也!”
王振对刘球前一次谏止兴师麓川本来就感到不愉快,这次对刘球奏章中讲到要英宗揽权的内容,更是不能容忍,于是找个差子,把刘球抓进诏狱,指使指挥马顺将他杀死,然后肢解尸体,埋在监狱的地下。
刘球遭王振惨害,就再也没有人敢对出兵麓川提反对意见。这一战争一直持续到1449年的春天,耗费了明朝的实力,“骚动天下”,几个月后,土木之变发生,应了刘球的预言。
在直接涉及与蒙古关系的事宜上,英宗在王振的唆使下,也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一是1444年(正统九年),英宗在未了解事态大小与真伪的情况下,贸然对兀良哈三卫用兵,导致兀良哈与明廷的宗藩关系破裂。二是同年瓦剌攻哈密,哈密忠顺王向明廷求救,英宗置之不理。三是1446年,瓦剌东征兀良哈,也先派使者向明朝借粮饷,明廷既不给粮饷,也不阻止瓦剌的东征,坐视兀良哈被也先兼并。这样,明廷就眼睁睁让也先轻易打破自己的防御战略布置,使也先势力坐大,成为对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
不但如此,王振还不惜出卖国家的安全,借以谋取个人的私利。
明代蒙古族社会的基础是单一的游牧经济,植物性的食物和手工业产品,大多数要从内地获得。和平获得这些物资的途径有两条:马市贸易和朝贡贸易。马市贸易类似现在的边境贸易。朝贡贸易是明朝优待边境各族和外国人的一种措施,借以换取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在朝贡贸易中,明朝除了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给贡品付款外,还要给朝贡使团丰厚的赏赐。两项的价值加起来,超过贡品本身市价的好几倍。
在以上两种贸易中,铜、铁、兵器属于严禁出口的物品。市场的规律是越难得到的东西,价格越贵。这些严禁出口的东西在黑市上可以卖很好的价钱。王振于是不顾国家的安全和禁令,做起了走私兵器的勾当。他嘱托同党大同(这里设有马市)镇守太监郭敬,每年向瓦剌走私箭镞几十万只。甚至当时属高尖技术的火铳也走私到了瓦剌。
也先从贸易中不但获得了大量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还获得了大量的战争物资,很是得意,想重温祖先大元帝国的旧梦。他正对明朝虎视眈眈,寻找适当时机,大举南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