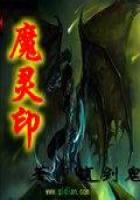在古城墙的保护方面,南京介于西安与北京之间:不像北京那样拆得只剩下几座孤零零的城门楼子,但是跟西安相比却又稍逊一筹。西安的城墙修葺一新,完好地保持着明代的规模,如果不参照周围的景观(高楼呀广告牌呀什么的),几乎察觉不出岁月的流逝。西安人挺自觉的,甚至公共汽车都依旧从城门洞里穿过,舍不得把绵延的城墙挖出两道豁口,以舒畅交通。南京还做不到这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保留一块完璧。譬如城南的中华门,虽正对长干桥,但好多年前就把两侧的城墙打通了,作为来往的单行线;因而城门一直是虚掩的,不买票进去,是看不清城堡里的藏兵洞和倾斜的马道的。还有通往东郊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的中山门,一度供车辆、行人穿行,近来也挖出了地下隧道,现代人要像土行孙一样从隧道里进出南京城。想一想也可以理解,这毕竟是出自善意的保护措施。城门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高枕无忧地赋闲当文物了——享受一番离退休老干部的待遇。
南京的城墙已不完整,就像高龄老人的牙齿,有许多残缺之处;需要缓慢地嚅动,才能消磨或反刍着漫长的记忆。但不管怎么说,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城墙屹立着,聊胜于无吧。在北京若想看城墙,恐怕也只能搭旅游车去八达岭爬长城了——昔日城墙的位置基本上已由车水马龙的二环路取代,某些地段还保留着护城河,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之相比,南京城能留下一副松散的骨骸,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尤其是与秦淮河相衔接的那一段,墙高水深,王气犹存;总体上来说,也对得起“石头城”这个古老的绰号了。毕竟没有被无情的岁月完全翦除了羽翼,能留下只鳞片爪,也已经算是万幸的了。
“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是古人对南京的形容。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胜利、将红旗插上了南京的国民党伪总统府,毛主席在北方即席赋诗,还引用了这一典故:“龙蟠虎踞今胜昔”。看来南京城是属虎的。一只老虎。
跟西安一样,南京现存的城墙,也是明代的遗物。包括北京被拆毁了的那一座也是如此。明朝像个兢兢业业的泥瓦匠,以修城墙为终生的乐事。这恐怕跟开国皇帝朱元璋提倡的口号有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是在南京登基的,甚至死后也安葬在中山门外的梅花山麓。他重筑作为首都的石头城,就像装修自家房屋似的,当然会选择最好的材料。我小的时候,大人指着巍峨的中华门城堡说:“这城砖都是用糯米浆粘接的,能不牢固吗?”那是在70年代,中国的老百姓都很少吃得起糯米,想想几百年前的皇帝却用糯米熬汁来喂城墙,觉得够奢侈的了。现在细想,这个叫化子出身的朱元璋其实挺没出息的,得了江山后立即想圈起篱笆来,生怕邻人眼红——这本身就不是健康的心理。擅长防御的人,肯定会怯于进攻。如何指望这画地为牢的君主去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这种保守的遗传基因也深深影响了他子孙后代的思维,注定了明朝是个紧捂住自己钱包的王朝——虽严加防范,但该丢的还是会丢。明代修的长城,同样是最豪华最牢固的,但也没能挡住清兵南下的铁蹄。保险柜肯定不保险。反而锁住了自己的手脚。
我在南京的城墙下散步,经常会有诸如此类的联想。或许是这古城墙过于深重的历史感造成的吧。
城墙曾经竭尽全力保护过它的子民,现在到了该我们保护城墙的时候了。南京人在默默做着这样的工作。但风雨的侵蚀是防不胜防的。南京的城墙,确实老态龙钟了。
与西安城的焕然一新相比,我其实更欣赏南京城墙的“旧”——这是一种残损的美。或者说,这才是原汁原味的古迹。譬如靠近紫霞湖的那一段,俗称“鬼脸城”,估计一直没有修复过,像一张大花脸似的。城砖仿佛都生了天花,坑坑洼洼的,连棱角都被磨钝了。这还算好的,有的墙砖还不翼而飞,露出里面的泥土来;经常能碰见陡峭的墙壁上长出一棵悬空的歪脖子树——连树都学会飞檐走壁了。我常常仰望着这杂技演员一样的小树,端详许久。它至少使年久失修的城墙不至于太寂寞吧。我看见的仿佛是在失语的老人膝头自得其乐地嬉戏的孩子。更别提墙头乱发一样披散的蒿草了……这段缺乏关爱的城墙,使我看见了一张不化妆的面孔。那一块块斑驳的城砖,是不可能谎报年龄的——因为那种沧桑之美是伪造不出来的。我甚至极难得地从中看出了几分岁月的狰狞。南京的城墙,不如西安的城墙那样受宠,它更像个弃妇——但正因为这样,你才能感受到它不加掩饰的真实心情。南京的城墙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垂危的老虎,但至少也比一件硝制过的华丽的虎皮大袄要多几分活力。你简直能听见它低沉而艰难的喘息。这至少证明:它不是一件悬挂在衣架上的象征性的外套。
我是依靠回忆在异乡写这篇文章的。写着写着,我真想去南京的城墙下走一走啊。写着写着,南京那高高的城墙,又挡住了我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