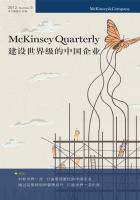情绪已不能够用单纯的心情、感觉、感受等字眼来概括。情绪俨然成了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工作技能,一种可以创造利润或遂行目标的工作手段,甚至是一种专业。
部分研究者强调:情绪表达也可视为一种工作任务,它会影响到工作效能;而不同的工作角色,可能被要求要表达不同的情绪;甚至同一职务,面对不同对象,也要表现出不同的情绪(RafaeliSutton,1987)。同时,依据工作任务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不一定要与内在真实的情绪感受一致。
工作中所做的情绪调节,与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调节似乎有若干不同之处。第一,两者在社会化历程(socialization process)上不尽相同。个人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情绪调节,往往是个人在父母教养、学校教育及社会规范与期待的影响下,透过耳濡目染与潜移默化的历程而习得(Eisenberg,CumberlandSpinrad,1998);严格来说,这种比较是一种非计划性的改变历程(unplanned change)。但是,个人在工作中所进行的情绪调节,却多半是组织通过种种训练与发展计划、监督、奖惩等制度的做法,让员工学习而成;因此,这是一种较具计划性的改变历程(planned change)。第二,两者在控制权的掌握上是有所区别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情绪调节,个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控制权,故可以根据对象、时机及问题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策略。工作中进行的情绪调节方式,常由制度来进行规范,个人的控制权相对减小,正如Hochschild(1983)所言:“……工作人员无法被允许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来看或思考,而是被要求只能以制度化所允许的方式来显示感情……如同一位农夫将眼罩挂在马眼上来引导它前进的方向,制度管理我们如何感觉。”第三,两者所费的心力也有所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多半处于私人领域(private area),涉及的互动对象较为熟悉与单纯,而情绪调节的成效往往只牵涉到个人,因此个人较轻松自在,所花费的心力较小。在工作中,人们多半处于公众领域(public area),涉及的互动对象较为多样且复杂,而情绪调节的成效往往不只牵扯到个人绩效的好坏,还事关组织效能的好坏,因此个人必须更谨慎小心,所耗费的心力也较大。
至于情绪劳动的范围限定在人际互动中,这乃是遵循Hochschild(1983)原先对情绪劳动的想法。他认为凡是涉及与公众面对面接触,且以改变他人情绪为重要工作内涵的职务角色,都需要高度的情绪劳动。本书将范围扩大:举凡在工作中进行人际互动时,对情绪调节所投入的心力,不论是调节自己的情绪或调节他人的情绪,都算是情绪劳动。倘若个人在工作中,是为了非人际问题进行情绪调节,这便不算是情绪劳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某甲与客户接触时,客户傲慢无理,某甲感到心里很不舒服,但基于业务上的目的,暂时克制住愤怒的情绪与骂人的冲动,和颜悦色地与客户沟通。某乙在设计程序时,屡屡失败,他克制住挫折的情绪,继续努力工作,终于完成。在上述两个例子中,虽然都涉及情绪的自我管理,但前者才符合情绪劳动的定义,后者则不算是情绪劳动。
值得说明的是,情绪的自我调节,不论是在人际互动中(如上述某甲的例子)或在人际互动外(如某乙的例子),皆有可能发生,既然如此为何要刻意加以区分?乍看之下,人际互动中与人际互动外所进行的情绪自我调节,似乎可以画上等号,实则不然。就目的而言,个人在非人际刺激中为了情绪自我调节所付出的心力,主要是为了消除不舒服的情绪感受,或是进一步为了增加愉悦的情绪感受;但是,个人在人际刺激中对于情绪自我调节所付出的心力,其重点不在消除负向感受与增加正向感受,而是在掌控外在情绪表现,以符合社会适切性、人际互动的规范、印象整饰的考量,或其他特定的人际目的。因此,人际互动中的情绪自我调节,会随着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远比非人际互动的情绪自我调节更为复杂多变,其所费的心力也越大。
由以上观之,在概念上将人际互动中的情绪调节与人际互动外的情绪调节进行区分,似乎有其必要。许多研究者同意Hochschild(1983)之观点,认为情绪劳动应该在人际的脉络中进行探讨才有意义。如Ashforth与Humphrey(1993)指出情绪劳动与服务接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似乎意味着情绪劳动是人际互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Zapf等人(1999)亦认为,人际互动是情绪劳动的关键成分。
若将“工作中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视为一个集合,“人际互动中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视为另一个集合,则两者交集的部分,即为情绪劳动(吴宗佑,2003),至于“工作中对情绪调节所做的付出的心力”中,未与“人际互动中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交集的部分,则为“情绪负担”(emotional burden)。原本Hochschild(1983)认为情绪负担是蓝领阶层的劳工在面对呆板无聊的工作时,对负面情绪所做的压抑,本书则将其定义范围略加扩大,把它视为是一种工作者(不论是蓝领阶层或白领阶层)在进行工作任务(尤其不涉及人际互动)时,对于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诸如秘书必须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而感到心情烦闷、企划人员为屡屡无法想出的创意点子而沮丧不已、生产线上的员工为了连日应接不暇的订单而心力交瘁,当个人在工作上必须对上述情绪进行调节所付出的心力,即为情绪负担。而在“人际互动中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中,未与“工作中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交集的部分,则称为“情绪工作”(emotional work)。这种区分乃是参考Hochschild(1990)的想法,在此之前Hochschild一直认为情绪工作与情绪劳动是两个可以互相交替使用的字眼;直到1990年,Hochschild才指出情绪劳动一词是用在“个人在公众场合(特别是职场)与人互动的情绪调节”上,情绪调节一词则指的是用在“个人在私人场合(例如家庭)与人互动的情绪调节”上。
最后,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在概念上,虽可将“个人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清楚地区分成情绪劳动、情绪负担及情绪工作,但在实际上,却可能出现若干不易切分的“模糊地带”。举例而言,倘若某人是计算机维修工程师,在客户端维修计算机时,一直找不出问题,并受到客户的冷嘲热讽,工程师一方面对于计算机无法修好感到挫折,另一方面又对客户的讽刺感到恼怒,此时工程师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要算是情绪负担,还是情绪劳动?又如,某人自家经营餐饮服务业,如果太太是老板娘,亲戚是店员,则老板在工作上与太太或亲戚间的情绪互动,有多少应该算作是情绪劳动?针对上述状况,本书认为,在概念上将“个人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区分成情绪劳动、情绪负担及情绪工作,并不表示任何“个人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只隶属于情绪劳动、情绪负担或情绪工作三者之一;事实上,很多“个人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多少都包含了情绪劳动、情绪负担及情绪工作三者的成分,只是多寡各不相同,当我们表示某种“个人对情绪调节所付出的心力”是情绪劳动时,只是表示其大部分的成分是情绪劳动,而不一定表示它完全不含有情绪负担与情绪工作的成分。刻意去计较“纯正性”,反而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