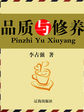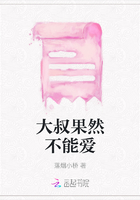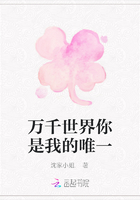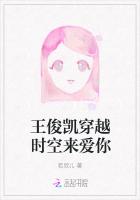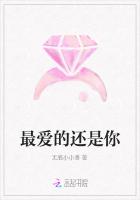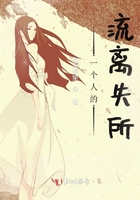我书橱里有外国的诗近百本,坦率地说,我读它们时,从未有过像读中国新诗时的感觉。在我读来,即使是歌德和惠特曼,也不及我们的徐志摩和艾青。
清人赵翼的《论诗》其二是首名诗,但向来人们偏重后两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亟此极富豪气的诗句去鼓动各自时代的文人学子争领风骚;而对前两名“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仅看作是一种铺垫。也就是说,人们注重的是后面引申出来的论点,对前面的论据用不着多加留意。这是正常的。细细体味,开首两句从引导欣赏这个意义上看,对我们的读书生活倒有一点启迪。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赵老先生只说它们不够新鲜,并没有否定其在文学史上的高大尊位。从总体上讲,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欣赏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能赢得万人称颂。但轮到每个读者头上,就不见得都能与“万口”保持一致了,这里面包括读者的欣赏水平和接受心理方面诸多因素。赵翼不愿老去品赏经过了万口传诵的作品,便是其中一种心理。他的话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强调了一条不变的道理:书要靠自己去读,欣赏只有靠自我完成。
造文作诗,古今托他人捉刀代笔者不乏其人,唯有欣赏艺术之事,是绝不可依赖他人替代的。既然是“自我欣赏”,各自间必有差异。而作为读者,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之差异呢?这里就有一个该不相信自己的问题。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峰巨岳,历代读书人无一不去领略。但对具体作者、具体篇章,读者却各自有别。说到唐诗,很多人会首先想到李白、杜甫、白居易,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地位高低次序的显示。但在具体的欣赏活动中,每个读者的天平上未必都是这样排列的。且不说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杜扬李抑的反反复复,就是现在也不一定都认为李在杜先。毛泽东多少次地引用李贺的诗,甚至干脆把他的句子用进自己的诗中,如“一唱雄鸡天下白”等,可见他对李贺诗的喜爱非同一般。李贺的诗有些艰涩,相对前面说到的几位,喜读的人要少些。而毛泽东精通文史,其艰涩不在话下。拿笔者本人来说,虽发表过研究杜甫诗歌的专题论文,但更欣赏李白的豪放飘逸,其次陶醉杜牧等人的悠远画意。读他们的诗时所唤起的美感,是与读其他古人的诗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诗语言都明朗流畅,很少引故据典,但意境奇伟,无须借助他人的解析便可完成欣赏过程。当然,这决不等于欣赏层次低下。因此,我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艺术感觉。
还说读诗。我书橱里有外国的诗近百本,坦率地说,我读它们时,从未有过像读中国新诗时的感觉。在我读来,即使是歌德和惠特曼,也不及我们的徐志摩和艾青。我曾说过,读者对诗的欣赏过程,往往是与诗的语言信号输入大脑的过程同步的。离开了语言艺术,就不存在诗歌的艺术,而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构建规律。因而,再成功的译诗也是失败的。即便是经过诗译界的高手引进的世界名篇,我也只是为读而读。国外有的好诗译成中文,也像政治口号或说教文字。我不懂几句外语,却相信像“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好诗句,翻译给人家也可能只剩下豪壮成分。所以,除了熟悉中文的外国人,还未听说他们哪一个如何推崇中国的古诗。如有,怕也是在符合我们。这样讲,并非否定“优秀的文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其他类的作品恐怕翻译中的阻耗要少得多,理性的东西就更好办一些。为了了解,我才去读歌德的诗,而《歌德谈话录》却读起来不肯释手,一读再读。在欣赏的问题上,我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