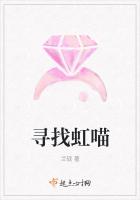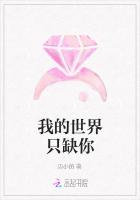一个时代的名著,大都是在一代作家逝后,才由下一代认定它们。这样,读名著大半就是读故人的东西。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不必去等,等到论定了,我们也死了。还是自己挑选着看,认为哪些当代作品能感动你、启发你,你就读哪些。
前些年,名著的身份大大跌落,那时我正在主编一家“读书类”的报纸,曾约请有关人士座谈撰文,为名著走出“谷底”而呼吁。近来,又见名著走俏起来,趋购者日众。名著终究是名著。
读书首先当读名著,这是最经济的途径。但在选择时,不要按通常的概念,把名著理解为仅仅指施耐庵、曹雪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优秀小说家的作品。各类著述中,都有出类拔萃的名著。比如唐诗宋词,就是几代王朝中,许多文人共同完成的内容最为宏大的名著,只要你陶醉其中,就是拥有了名著。首要的,是选择自己所学习、研究的某个门类的名著。世界上决不存在某一本所有读书人必修的书,《红楼梦》诞生之前,中国早有了极其辉煌的文化。
一般来说,名著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淘验,才能确定下来。中国现代的名著,也大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才被评论界认定。其实,每个时代都可能产生名著。当代为什么没有名著呢?历史检验需要一个过程,这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人们总怀疑“文人相轻”这种难以消除的劣根性多少还在起作用。尤其是同辈的文人,是很难让他们将某个作家的某部优秀作品与已经成立的名著相提并论。鲜有可望入流的,也往往靠的是上一辈文人的提携。因而,一个时代的名著,大都是在一代作家逝后,才由下一代认定它们。这样,读名著大半就是读故人的东西。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不必去等,等到论定了,我们也死了。还是自己挑选着看,认为哪些当代作品能感动你、启发你,你就读哪些。诚然,也不一定用它获过什么奖作为你的选择标准。
总体上讲,名著是有标准的;但这个标准并没有量化(或者说具体化),它只是像一把无形的尺子,存在于无数读者的心中。
不久前,有个英国人试图搞出个认定名著的标准,他提出了六条,颇值得玩味,不妨录来:一是名著的内容能长久地吸引读者,是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二是名著在表现上面向大众,通俗易懂,而不是面向专家学者和文学沙龙;三是名著永远不会落后于时代,其内容和内涵决不会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而失去它观照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四是名著隽永深刻,有时一页上的内容能够多于许多本宏论的思想内容;五是名著能言前人所未有,道古人所未道;六是名著探讨的是人生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某个领域里有突破性的进展。
这是一个严格的高标准,如果拿它去衡量我们已经确定的名著,可能有些将淘汰。但就这六条来说,有些指标看起来很硬,若实施起来仍可能被化作软指标。世界上最缺乏“可操作性的”就是文学标准。
正因为文学没有固定的、可操作的标准,所以历史上发生的名著险遭厄运的现象屡见不鲜。1856年,福楼拜将他的《包法利夫人》交给一家出版商,不久就被退回,原因是“整部作品被一大堆甚为精彩但过于繁复累赘的细节描写所淹没。”多少给这位大作家留了点情面,还算客气。最糟糕的莫过于美国伟大的诗人惠特曼,他那部被称为“美国诗坛划时代著作”的《草叶集》,曾被出版商退稿,并告诫说:“窃以为出版大作当属不甚明智之举。”一八五五年七月四日,当他自费印出把集子送到书店时,却无人问津,备受冷落,搁了一个星期,一本也没有卖掉。第二年增订后出了第二版,仅仅卖出十一本。初版出后,他把书寄了一些给美国文坛的名流,大都置之不理,诗人惠蒂稍翻了下就轻蔑地把它扔进了炉火。有的评论家愤怒地骂道:“惠特曼不懂艺术,就像猪猡不懂得数学一样。”最使诗人痛苦的是连他的母亲和弟弟都瞧不起他的书,母亲斥之为“泥巴”。好在大文豪爱默生开始曾对此著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大文豪又收回了自己的热情。还有,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如果作为名著,其遭际更不用说了。当时他接到的退稿信上这样写着:“为了大师的自身利益请勿发表这部小说。”倘若编辑先生们能料到这将是一部轰动世界的著作,也许不是这种态度,尽管他们对作者充满着真诚的爱护之情。
判断文学的优劣决非判断商品那么简单。真正的优秀作品是不怕尘埋土盖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上述名著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相去甚远。我国在上半个世纪诞生的一部名著,坦率地说,我读了两遍竟没有看出它“划破黑夜”的深刻意义,这自然是因为我鉴赏水平很低的缘故。然而后来竟有人指出,它不过是某些章节的内容适应了我们一贯坚持的政治标准。不妨退一步讲(由读者承担责任):并非每一部名著都适于任何一位读者。
是不是一定要把主要的名著都烂熟于心才算学成呢?也不见得。还是得讲点自信,善悟者读一两遍当可悟出其精髓,除了你打算一辈子去“吃”某一部名著。《西游记》写了唐僧师徒的九九八十一难,若要悟出个主题来,甚至没有必要把大同小异的“八十一”逐个地琢磨个没完。《红楼梦》的确博大精深,说是中国的国宝,说是包容了二十四史,可谓说不完,道不尽。它的每个字,每个标点都被红学家们嚼烂了,再过多少年,也许它将达到平均每个字养活一个研究者。一代代红学家的艰辛探研,帮助世人不断加深着对这部巨著的认识,但一般读书人,用不着去不停地细啃穷究。此外,读名著最好是先读原著,再去看别人的评论。否则,许多精彩的东西轮到你去品尝时,总有点吃别人嚼过的馍之感觉。比如《红楼梦》里“凤辣子”出场的描写确实高妙,当你知道曾有许多研究者乐道这个细节后再去读它,就失去了那份新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