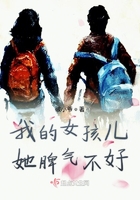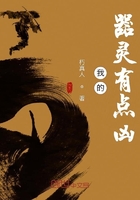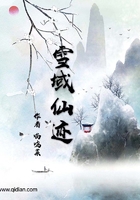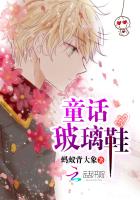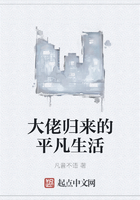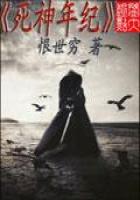想象力是可以培养的,就是要锻炼自己的眼睛,多积累生活,增强诗的敏感,善于运用诗的思维,才能够自如地用另一种事物的形象来准确地表述你所要反映的事物形象。
每年我都要收到数十封在校学生的来信,许多同学附了习作,并提出不少关于诗的问题。因我每日忙碌不堪,加上如“怎样写好诗”这么大的提问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故未一一作复。今天,我想借《少年世界》这间课堂,就同学们习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大家漫谈一次。
来信的同学大都是立志学诗的,诗神的魅力使我惊叹。同学们以大量习作,把我诱入了一个纯真、灿烂的世界,这是充满活力的诗的世界。我看见一股股鲜活的情思,正从创造的源头突突地奔涌出来。这个世界蕴藏着丰富的诗的矿藏,蕴藏着诗的希望,诗的未来。他们中,定会有人将出现在未来诗人的行列。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大家才刚刚接触诗,认识诗,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还了解甚少。因而,大多数习作离诗的基本要求还相差很远,更难以考虑发表了。但这是正常现象,每个诗人都经历过这种阶段。入门有个过程。那么,诗的基本要求究竟有哪些呢?下面,我根据同学们的提问,主要谈三点。
首先谈谈立意。讲求立意,是中国历代诗文的一大共同特点。几千年来,文人们做诗为文,都强调赋予作品一定的思想意义,这说是立意。有同学问,为什么老师在讲立意时,总说与政治相关?我想,可能是老师对你们的要求太高,或者说表达得不够准确。写诗是否要考虑政治,这是文艺界争论了许多年的问题。同学们目前大可不必去探究它。如果一定要问个明白,我只能简单表明我的观点:任何文艺作品都带有作者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为某种政治服务。而它作为一种要求,只能是对文艺的整体而言,不应落实到每篇具体作品的创作中。同学们习诗,只要表达的是健康的情绪,都应当赞许。
同学们目前所熟悉的,大多是校园生活,如同学间的友情,老师的形象,女生的眼泪,清晨跑步的感想,等等。这些生活也可以写出新意来,但大家目前还缺乏开掘的功力。有些诗,同学们自以为“很有感情”,冲动过自己的情绪,却是别人早以感受过的东西。一首题为《啊,友谊》的诗中写道:“你是黑夜里的明灯/你是呼唤灿烂朝霞的金鸡/你是惊喜时姑娘嘴边的笑靥/你是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意……”一口气写了上百行,语言上有的还接近诗,问题是这些诗句都很平,没能表现出较深的意境。作者说,把友谊比作“黑夜里的明灯”这句,他很满意。应当承认,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创造,因为他读的少,不知道别人早已这样写过。
有位同学寄来一首《我爱这和平的大地》,一共八行:“我爱这和平的大地/炊烟在微微飘动/秧苗在茁壮成长/牛儿在贪婪地吃草/小伙儿在纵情歌唱/一片绿色的大地上/东边升起了煦暖的太阳/啊!我爱这和平的大地。”可以想象到,他曾为这片田园景象动过情,很想绘出一幅田园风景画,他也写了一些象征和平大地的景物,但都是一些平铺直叙,什么都写进去,什么也没有写出诗意来。几乎是同样的画面,天门县卢市高中的张志同学却提炼出了较新的主题。他的《窗外》全诗如下:“一头牛/一张犁/一个人/耕了几千年/一顶草帽/两只赤脚/几掬汗水/洒了几千年/许多片土地/许多勤劳人/许多相似形/重复了几千年/窗外/一幅画/挂了几千年。”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历史变化太慢,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些平常景物的描写,去引导读者进行反思的,从而赋予了作品一定的思想意义。
第二个问题,谈谈诗的形象创造。形象是诗表现形式的总和,也就是说,诗人是通过形象来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没有形象,也就无诗可言。诗人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功力,就是描绘形象的功力。从大量的习作来看,不少同学具有形象思维的训练基础,但目前还缺乏捕捉形象的主体意识,有首习作把“老师一张嘴”比作六月的云,“洒下滋润xy的甘霖”,接着又说成是五彩的笔,“画出缤纷的星星”,进而又说它像口针,“有时精挑细绣,有时一针见血毫不留情。”这位同学所运用的三种比喻—云、笔、针,都和嘴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形象上毫无相似之处,所以不能让人想到老师的嘴,后面的讴歌性语言也就不能成立。有位同学在一首《老师窗口的灯》中,说灯“点燃春早的第一缕霞”,语言上不够顺畅,比喻却较恰当,灯火是红色,朝霞也是红色,说霞是灯点燃的,当然可以。但他紧接着来了句“架起一座通向未来的桥”,灯怎么架桥呢?他大概指的是彩虹,显得很牵强,难以使人联想上去。
诗是作者的感觉,不要像写记叙文那样,去照直描写它的固有形态,那样不含蓄。一个人很健壮,很敦实,如果你觉得他像一座矮塔,你就可以照这种感觉去写,这是打个简单的比方。说到这儿,不妨再举个较为成功的例子,是温州市中学生李索索的一首诗《奶奶的吻》,他写道:“奶奶把一个吻/贴在我的唇边/就像把一枚邮票/贴在淡绿色的信封上/我想/信封里装着什么呢/装的是奶奶的希望”。由于作者较好地把握了一个诗的感觉,所以嘴唇印子变成了邮票,进而想到一封信,很自然地又把奶奶的希望装进这封信里了,使无形的思想有了寄寓。全诗是由“吻”展开的想象,始终没有脱离它,并且想象得比较新奇。
如何创造诗的形象?说白了,一个常见的手法是运用比喻。能不能寻到贴近新颖的比喻,是检验一个诗作者想象力强弱的重要标准。想象力是可以培养的,就是要锻炼自己的眼睛,多积累生活,增强诗的敏感,善于运用诗的思维,才能够自如地用另一种事物的形象来准确地表述你所要反映的事物形象。
第三个问题,说说诗的语言。诗是语言的艺术,没有哪种文学体裁,会比诗歌更讲究语言艺术。诗对语言的基本要求是:简练,生动,形象,高度浓缩。所以,古今诗人无不在语言上精雕细刻,费尽心思。有些同学由于经过了比较严格的语言训练,又掌握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他们能够写出很有希望的诗篇。比如,广西岑溪县有位叫肖永瑞的同学,就用纯朴的语言写过一首动人的诗,题目是《山那边有个故事》:“山那边有个故事/很长,很长……/自从那坟茔垒起/风儿就开始诉说/说了三百六十五个白天/三百六十五个黑夜/说不清墓里那副眼镜有多深/教鞭有多长/说不清那身上粉笔气味的浓度/说不清那双眼睛熬过的夜晚/说不清他留给人间的温情……”就这么几行诗,却充满了无限的情感,作者说清了那“说不清”的怀念思绪。这就是诗歌语言容量丰富的结果。
然而,更多的同学由于驾驭语言的能力本来就不很强,加上没有寻到诗的意境,没有构思出诗的形象,所以在写诗时显得吃力。有的写起来漫无边际,一提笔就是几十上百行,乍看像首诗,仔细读起来,不知他要写什么。有的同学情思涌动,想用诗把它抒发出来,但没有自己的语言可用来表达。比如,一位同学写了首《灵魂》,其中有这么一段:“这是一个普通的灵魂/负载着不平凡的憧憬/凭借刚刚燃烧的炎焰/要使五岳俯首,五洲浪静!”他的抱负很大,大概是想做一个拔山盖世的英雄和伟人,但他只是把几句豪言壮语生硬地拼在一起,没有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志向,可能还会使别人主解他“狂妄”。另一位同学写了首《心愿》,想反映出他准备到社会上去经受生活磨炼的心情。因为他对人生道路上的艰辛缺乏感受,也无法想象,只好写了一串“任狂风猛割面颊,任雪水狠咬足尖”之类的句子,显得很生硬。
今天,我想主要帮同学们找找问题,所以很少提到大家的成绩。总的说来,同学们的习作中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少同学还是很有学诗基础的。我曾多次对人讲过,这一代中学生不简单,他们逢上了好时代,也有好条件,将来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以及在整个文学创作上,将大大超过我们这一代人。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大家不气馁,多看多练,是一定能够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