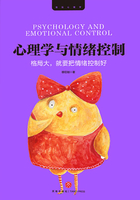第一眼看到何凡丽,她笑的十分艳丽,比深圳的夏天太阳还要剌目,我想嘲笑她俗气的搬照了瑞丽的化妆,却画得像一个婊子,可是,我什么也没有什么,只是挽着她的臂说:“你真的越来越漂亮了!”
语气真诚,她几乎感动,握着我的十指说:“杨惠,你变了,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
我纠正道:“叫我娘子好了,我实在听不惯别的叫我别的名字,我会反应不过来,结婚的女人自然和从前不一样。”
是啊,我把痴肥,懒惰,不上进都怪到了结婚这件事情上,好似结婚的女人就应该这样心安理德的肥下去,就应该把脸上的死皮乱掉,就应该穿这种孕妇装样的工人大伯裤,满世界的穿梭,最好还提一个菜篮。
不是不恨自己的,结婚罢了,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就这样心安理德的做黄脸婆,才多大,再多几年一定会有狐狸精来缠我家老蔡,老公是个情场白痴,当年我就是在用极烂的招数泡到了他,而且还让他正儿八经的下跪求婚,然后再拿着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招摇上床。
我几乎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一个肥得变形的女人,拖着一个惨巴巴的小孩,小孩在餐桌上做作业,而我在厨房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对孩子数落他爸的种种不是,比如什么夜不归宿啊,有小老婆啊,××啊!而那孩子看我的眼神都是活该。
我看着何凡丽,她的眼神和那个幻境中的孩子是何等的相似,我的指甲都掐进了肉里,但还是挥手叫了出租车。
何凡丽极不情愿的钻进了红旗出租车中,她似乎不满意我不开宾利来接她,她是否认为从飞机上一下来,就有精壮男夹道欢迎,真丝红地毯,还有戴白手套的司机拉开宾利的车门,最好有一个真正的钻石王老五把她要去。
她把小包抱在胸前,眼睛望着外面,从地面上飘了过去,直奔香港。
那也难怪了,香港目前来说,客观的说,还是比深圳要漂亮那么一点点。
其实在上海也可以嫁老外,不一定要跑到深圳来,而她却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杨,不,娘子,你知道不,我们学校的易明在香港开公司,混的很不错,上千万,听说现在还在深圳办了一个总部。”
易明,就是那个高个子,然后喜欢打篮球的时候往女人胸前瞟的那个男生,好似是长得不错,可是,怎么长没有成个二流子,倒成了一个企业家。
难道何凡丽是跑来深圳泡这个二流子企业暴发户的,我暗地里傻笑,她倒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凭什么认为易明会喜欢上她呢?
但何凡丽的眼睛似乎还是那样的充满着希望,那就让她充满吧!她望我的时候,似乎总是在躲避着什么,我们之间一定是要躲避一些什么的,但是我们的手又握得那么的紧,像是在感谢对方,感谢对方这么多年来一直都保守着秘密。
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何凡丽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感觉你家很阴!”
这真是一句让我十足不满意的话,现在已经不再是孩子时代了,说什么话怎么还是没有个轻重,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触我的霉头,但是,她人已经进来了,而且大大咧咧的坐在沙发上,摆成了个地主婆样,等着我这个主人兼丫环送上香茶。
她从沙发上窜起,把窗帘都拉开,然后惊奇的说:“娘子,你有多久没有打扫地了,看上面的灰尘都可以集成一座坟了。”
我趁她去洗澡的时候,已经做了一桌的好饭菜,她出来的时候,一边笑一边望着我,然后说:“娘子,你真的是,太贤惠了。”
不知道为什么,人人看到我围上围裙的时候都会这样表扬我,是因为我真的有一手好厨艺了吗?我与何凡丽相对着坐着,我们一起吃着饭,一股温暖慢慢的袭进我的脚底,感觉到踏实,从此不必再害怕恶梦。
女人就是这样,互相讨厌,互相提防,互相嫉妒,又互相怜爱,互相关怀,互相呵护。
我们一同伸手去拿餐后的苹果,手触到一起,我才真诚的说:“欢迎你来深圳。”
而她的笑也一样的真诚:“谢谢你。”
这也许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唯一一次真诚的对待对方吧!
她还送我礼物,一条非常漂亮的围巾,长长的流苏下是美丽的小碎铃,温柔的羊毛捂在脸上非常的舒服,我捧着围巾把头埋进去,在我低头那一刹,忽然看到围巾上有一个女孩的笑脸,是那样的清楚,而那张脸上的左脸上有一块淡红的胎记,像一片盛开的桃花,想要得到我的热吻。
我目光呆呆的望着那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女孩的微笑,笑的是那样的甜,身后是开不完花的洋槐树,那白色的花,像一层雪一样铺在路上,铺了一层又一层的,像是要把那个女孩给埋在照片中。
而她脸上那桃花色的胎记却一点也无损于她的美丽,相反,让人感觉到特别的神秘吸引,总想要去追问她的过去,而她的嘴向上轻轻的抿着,是那样的骄傲自豪,像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挫折。
我眼前发黑,那张照片的女子眼和鼻里慢慢的渗了水来,不,那不是水,是鲜红的血,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伸手去摸,入手处冰凉湿润腻滑,带着一股腥味,是血,腐烂又怨恨的血。
那照片就在我手心里化了,化成了一片血水,何凡丽却跑来说“怎么搞的,你划伤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