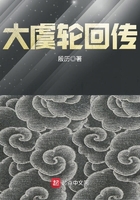二
一天下午,王国光和田景明正在聊天,电话铃呜呜响起来,田景明接起电话,一听是袁主任打来的,通知他去市里吃饭,田景明放下话筒,歉意地对王国光说:“袁主任请站区的管理人员去饭店吃饭,我得换一换衣服。”
王国光笑一笑说;“你尽管忙你的。”说完,离开田景明的办公室。田景明去洗漱间洗一把脸,回来换好衣服,下楼去站台,登上了那辆大轿子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只等他和袁主任。苟发庆正给大家讲他在原单位的事情,无非还是他如何有本事,如何办事得当,受到领导的重视等等,田景明听见无聊,两眼望向窗外想心事。不一会儿,袁主任上车。坐到前面副驾驶的座位上,回头扫视一眼,问道:“都上来没有?”
苟发庆急忙答:“主任,都上来了。”
袁主任对司机说:“开车。”
司机扭转马达钥匙,挂好档位,踩动油门,大轿车稳稳驶出站台,沿着砂石路朝伊金霍洛旗开去。
大轿子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天黑时,终于驶入了城区,在一长串路灯的指引下,溶入辉煌的街道,轿子车三拐两拐,最后停在一座大酒店的广场上,大家鱼贯下车,跟着袁主任推开酒店的玻璃转门,进入漂亮的大厅里。前台上女服务员马上迎过来,笑盈盈问道:“你们要定包间?”
袁主任说:“已经定好啦,有一个姓胡的人来定的。”
“知道了,在二楼。”女服务员指一下大厅东侧的楼道,说道:“请在那里上楼。”
楼梯铺垫红地毯,一直延伸上去,楼口有门童迎接,让人觉着敞亮舒展。站区的会计小胡西装革履,站在走廊里等侯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优雅地把大家领进一个宽敞的宴厅里。厅间正中,摆设一张豪华的大圆桌,十四把雕花的木椅围靠在桌边,格外引人注目,桌子上方挂着一枝华丽的吊灯,屋顶用洁白的石膏板装饰,雕刻着蒙古特色的图案,墙壁贴有蓝绿色的印花壁布,更显富丽高贵。正墙上挂有一幅巨大布画:俩个儿童天真嬉戏,女童端着银碗,男童拿着哈达,呈现欢乐吉祥。整个房间都铺垫厚绒地毯,给就餐的客人增添了一份尊贵。
大家依次落座,随后俩名红装女服务员端上餐具,一名绿装男服务员提着锃亮的茶壶,为大家倒满清香的奶茶。人们客气地说笑着,气氛渐渐融和起来。几分钟后,服务员开始上菜,全一色的蒙古风味:甜饼,酸奶,炒米,牛肉干,香肠,烤羊排……在桌边一溜儿摆开。酒全都上的是三星的河套老窖,口感醇香。袁主任先讲几句祝愿辞,说完,把手一伸,招呼大家吃喝。刚开始大家都文绉绉地拿捏着,三杯酒过后,就放开了手脚,大声说笑起来。田景明爱唱歌,忍不住站起来,为大家唱了一首《夸河套》,大家鼓掌应和,齐声喊好。工务专业的曾队长不甘落后,也为大家表演本地曲目《罗干妈》。他向服务员要一块白毛巾围在额头上,离开坐席,走到门口,突然罗圈起身体,模仿着小脚老太太,扭扭捏捏地说唱起来,“我叫罗干妈,今年六十八,前生命不好,嫁了两次人,认了干儿子,名字叫鹏飞……哎,我年老体弱,不知还有几年活,赶紧替鹏飞,张罗一房媳妇,,省得他孤独难熬,想女人心焦……”说唱到此,引得人们一阵哄堂大笑。
曾队长表演完毕,袁主任让旁边的苟发庆表演一段给大家助兴,苟发庆摇头说不会,别人不让,要罚他三杯酒,他无奈,连干三杯了事。
席面上,大家推杯换盏,把酒言欢,气氛渐入高潮。这种超级享受,对于站区的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件愉快而有意义的事情,既满足了胃口的欲望,又满足了自尊的需要。
桌上摆的八瓶酒喝完,大家都有些醉意。小胡出去一趟,不一会儿,领着几个穿蒙古袍的演员进来,有的拿着乐器,有的捧着哈达,有的拿着酒瓶,笑盈盈地坐在屋角的大长沙发上,等待为客人表演。小胡回到席位,笑呵呵对大家说:“咱们请来当地有名的乐队,为大家唱歌助兴。”随后他走到乐队前,跟一个女演员低声交代几句。音乐猛然响起,厅间里流动起清新欢快的旋律。大家转头观看,神情为之飒爽,第一曲是《祝酒歌》,一位窈窕女子手捧蓝色的哈达来到袁主任面前,另一位漂亮的女子端着银色的酒碗跟在身后,一名男子拿起酒瓶在旁倒酒,另一名男子则站在袁主任的侧面,转动歌喉,用蒙古语为客人放声歌唱。歌声刚落,捧哈达的女子将哈达挂在袁主任的脖项上,敬酒的女子将身一欠,把一杯酒敬给袁主任,袁主任接过酒碗,也欠一下身,按照当地人的礼节,用手指蘸一下酒水,对天一弹,对地一弹,对人一弹,表明上敬天,下敬地,中间敬人,然后一饮而尽。大家齐声鼓掌叫好。接着音乐声又响,《鄂尔多斯之恋》的曲调升起,悠扬的旋律激荡着每一个人,敬酒队走到曾队长面前,曾队长痛快喝下一碗,有人起哄,让歌手再为曾队长献一首,曾队长摆手推辞,歌声早已唱起,曾队长只得再喝一碗,大家欢呼。下一个轮到苟发庆,苟发庆摇摇晃晃站起来,引得大家一阵大笑,他稀里糊涂把酒喝完,一蹲身子坐下去,木着脸,呆在那里傻笑……十几个人轮流敬完,大家仍觉着意犹未尽,不忍叫停。然而天下没有长久的盛情,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最终,大家还是回到大轿车里去,把剩余的能量放在车上喊叫出去。车行一路,歌唱一路,说笑一路。他们从原野上来,粘一点城市的繁华,又回到原野上去。
回到站区,已是深夜,大家相互搀扶着下车,回到办公室,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又是一阵畅谈。
第二天早晨,苟发庆双眼通红,王国光看见,不由得咯咯发笑。吃早餐时,田景明坐在王国光旁边,王国光问他,苟发庆的眼睛怎么了?田景明说他昨天喝醉了酒,碰到自己的房门上了。
“他喝了多少?”
“差不多有一斤。在酒店里就喝多了。”
“酒店里的饭菜怎么样?”
田景明小声说:“一色的蒙餐,不错。”
“花了多少钱?”
“大概也得两三千。会计结的的帐,具体钱数不太清楚。”说完,俩人都默默吃饭。
到了九月份,运量突然猛增,每天运行列车达到六对,公司内部酝酿起一股乐观情绪。但是运量上去了,人员缺乏问题又显现出来。每一个站区都缺工人,每一个专业都超负荷干活,一人多用,一人多能,见活儿就干,渐渐成为站区员工的常态。
星期五下午,王国光正在运转室检查控制台,列检的熟练工马瑞飞来运转室看行车计划,坐下来和值班员张立江抱怨:“干活时间太长,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人熬不下来了。”
张立江苦笑说:“我们也一样。”
小马子说:“你们累,起码在屋里,安全,我们在外头,在车轱辘底下,不小心就玩命。”
“听说还要增加两对列车,那样就更忙不过来了吧?”王国光插话问。
小马子说:“要是增加两对,车辆的安全就保证不了。你想想,人过于劳累了,检车能精检细查吗?现在已经到了极限。有的人都已经坐在地上爬不起来啦。”
满屋子人都叹气。
小马子抱怨说:“东铁公司用人太小气,运量上来了,舍不得招人。”
“他就是舍得招人也招不来呀。”张立江接过话茬说:“每月二千块钱工资,没明没夜地干,谁来这里干?来的人都是不知道情况,来试一试的,试上几天不合适,跑了,像电车司机已经换了多少茬了?咱们估计也干不了多长时间。”
供电专业的姜队长不知几时来到运转室,这时插上话说:“主要还是待遇问题,公司给熟练工每月挣五千块钱,你看招来招不来?那时人多得随便挑。”
张立江立刻反驳道:“公司能舍得给你五千元?法定节日的加班费都没有,夜班费,奖金更甭提,这样的单位能舍得多给你三千元?”
“就是!”大家都有同感。
小马子说:“文件上写得尽是骗人,条款上这也有,那也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咱们刚应聘时说有两个月试用期,试用期过了,结果又搞出什么三个月的考察期,考察期过了,还不知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一提考察期,王国光就心烦,气哼哼地说道:“它这样搞是违反劳动法的,劳动法规定,试用期最多两个月,两个月一过就按正式工待遇。”
小马子说:“咱们说啥也没用,控制权在公司手里。”
王国光不服气说:“咱们应该一起去找公司,让公司给一个说法,人多了公司就得给答复。”
张立江不以为然地说:“怎么联合人?人今天来,明天走,就咱们几个人?顶啥用?”
大家一想也是,都沉默不语。并且还有一个问题,谁来带头?枪打出头鸟,谁也不想挨枪子。人们发发牢骚可以,真到了出头时,谁也不去冒这个险。大家普遍存有一种心理:愿意做幕后的诸葛亮,不愿做爱出头的猛张飞。
王国光却不合时宜地说:“有两三个人也算,这些问题不说出来,公司就当咱们是傻瓜。”
张立江咧嘴一笑,“你以为公司把咱们当人才啦?充其量不过是干活的工具。他们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能多剥削一天是一天,咱们说了也白说。”
王国光见人们退缩,心里有些不痛快,“我明天给人力资源部打电话,反映咱们的情况。”人们都看他,相视而笑。
王国光从运转室出来,往宿舍里走,刚踏上楼梯,就被姜队长一嗓子喊住,姜队长也是三原人,性子直,他把王国光拉到楼角,悄声说:“老王,我劝你不要给公司打电话。”
王国光皱皱眉问:“为什么?”
姜队长直言不讳道:“现在站区不稳定,你向公司反映问题,公司就要追查站区,恐怕对袁主任不利。”
王国光一听说要影响袁主任,只好作罢,说道:“电话我不打了。”。
姜队长笑道:“这就对啦!识时务者为俊杰。”
王国光对后一句话很反感,做人都识时务,就都成了软骨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义。
吃完晚饭,王国光去站台上散步,正碰上电车司机薛师傅,薛师傅是山西人,今年六十一岁,花白头发,上身穿圆领衣衫,下身穿宽腿灯笼裤,全身打扮得像一个耍把式的江湖艺人,他去年刚从国铁退休,闲着没事,趁身体还硬朗,应聘来东铁公司开电车,每次出车回来,一下机车,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在外面溜达。今天他刚从家里休假回来。他俩互打一声招呼,边走边聊天,王国光说:“这几天每天跑六对列车,运量上来啦。”
薛师傅抬头看了看站场,不满意地说:“光知道他们挣钱,不给咱们开资,今天都二十三号了。”
公司规定每月十号以前开资,现在都已经拖延了半个月。王国光揶揄笑道:“东铁公司没有一个月是按时开工资的,他们的规定都是说着玩的。”
薛师傅鼻腔里哼了一声:“这单位不是什么正经单位。”
王国光正要答话,忽见前面一辆汽车上下来几个人,提着沉重的行包,拖拖拉拉向站房走来,这些年轻人都戴着眼镜,像刚毕业的大学生。
“又来了一批人。”王国光有些兴奋地说。
薛师傅满脸不屑:“又骗来几个学生,人家能不能在这穷山沟里呆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