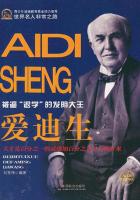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不能企求完美,而应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审视。关于世人对杨士奇有些方面的看法,我想谈点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忠贞仁义”
明初的政治斗争是复杂尖锐而且残酷的。惠帝刚刚继位,当他欲行削藩时,便引起了燕王朱棣的反叛。朱棣美其名曰“靖难之役”,实则是“清君侧”的故伎重演而已。不到四年,惠帝便被他赶下了台,生死不明。燕王继位成了成祖皇帝,年号永乐。藩王纂位,宫廷易主,这对明王朝是一场极大的变故,刚刚休养了三十多年的百姓,又一次横遭战争蹂躏,而以方孝儒为首的建文旧臣,因为坚持封建的法统观念,不堪新命,被列为奸臣,成批成批地遭到屠杀。在这场政变中,杨士奇曾与解缙、胡广、金幼孜、黄维、胡俨、周是修等约同死义,可是朱棣一进城,除周是修在国子监尊经阁自缢而死,还有一个吉水籍的王艮也饮鸠身亡外,解缙、士奇等人则改弦易辙,皆“叩马首迎附”,参加了迎燕王入城,拥燕王登基的行列。
对杨士奇的这种做法,世人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是纯粹从封建宗法、伦理的角度出发,持“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和“食人之禄,死人之事”的迂论来诋毁杨士奇;另一种则截然相反,称赞他“有拥立功而口不言,类文彦博。”是政治家明智的抉择。燕王与建文之争,是皇室内部的权力争夺与转移问题,与秦、汉改朝,魏、晋换代不同,与宋和元、明和清的********更不相同。“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他还是认清了大势,顺应了潮流,没有稀里糊涂地成为殉葬品。论人是非,尤其是历史名人的是非,应看他对当时的国计民生起的什么作用,对后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春秋时齐国的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与纠在父亲齐襄公死后,兄弟争国,最后公子纠失败死了,他的两个主要助手一叫召忽,殉难而死,一个叫管仲,没有殉难,反而投靠小白,作了桓公的宰相,忠心耿耿地辅佐桓公。后来他以“尊王攘夷”之策,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对其评价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清代的论者称杨士奇“公之功,更甚于管仲。明代非词林不谥‘文’,‘文贞’之谥尤不多见,公由荐辟出身而竞得之,是岂可以‘贞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绳之耶迨我朝雍正二年,诏公配享历代帝王庙,事久论定,愈足见公之勋业,在明代固当首屈一指矣!”(肖敷政《重刻东里全集序》)倒是很有见地。
二、关于台阁体
明朝前期,在政坛和文坛都以“三杨并称”,杨士奇是明台阁体的盟主,他对台阁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文风成为台阁体的典范。后人对台阁体颇有微词,但我们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作为应制唱和歌颂盛世气象的一种宫廷文学,台阁体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来看,是有其文学传统和历史背景的。台阁体属于我国古代宫廷文学的一种,我国宫廷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的“雅”和“颂”,然后是西汉大赋,始于南朝的宫体诗,唐朝上官体,宋代西昆体,接下来才是台阁体,之后有茶陵派。这些宫廷文学派具体来说各有特点,但总的看来,都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歌颂太平盛世,在文学地位上都起过引领和规范一代文学的作用。
与宋之西昆体派相类似,台阁体派也带有激发文学革新思潮的因素。它是在当时特定政治和时代环境中产生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阁作品是台阁大臣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三杨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们不仅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还是四朝政治的参与者。他们生活在涵濡深恩,优游帝侧的环境中,鸣太平之盛,颂天子之恩,是其内心的自然愿望和当然责任。
杨士奇的诗文多为应制、应人之作,飒飒雅音,风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实平正。他的诗歌题材较广泛,数量也多,虽然有时会因为题材相同而显出浅易单调的毛病,但总体上应该值得肯定。其文多序跋、墓志铭、墓表等应用、应酬之文,继承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关乎教化,温柔敦厚。
台阁体的出现和兴盛,与其所处的时代境际与所怀的个体时代体验是紧密相关的。出生于元至正末年的杨士奇,切实地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兵火和****,见证了由此造成的巨大创伤。(《东里文集》)进而将前后时代对比而言:“自吾之幼而壮而老,于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礼教修举,四境晏然,民远近咸安其业,无强凌众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乐,朝恬夕嬉,终岁泰安而恒适者。”(《东里续集》)这种由乱而治的人生经历,体现到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展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情调。而且史实表明杨士奇生活的主要时期永乐至正统年间,与元明之际和明后期相比,这一时期不能不说是政治比较安定、社会比较太平,史称“仁宣之治”的历史局面就是这期间出现的,欣逢盛世,可谓是不能不有感而发。他的诗作都是当时社会盛况和作者心情的一个真实反映,而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纯然的阿谀粉饰之作,它是诗人主观情志在诗歌创作中的自觉表现。
综上所述,杨士奇的应制诗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应制诗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但从个体与社会所处的历史交点来看,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杨士奇的应制诗虽然高唱时代赞歌,但却不是纯粹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内心的真情流露和创作的自觉追求,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和时代意义。因此,即使反对“台阁体”的以明代中期文学家李梦阳为首的“七子”对他的诗文也大加推崇,如李梦阳就曾写诗称赞道:“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
至于三杨过后台阁体弊端百出,主要还是由于末流者浅薄模拟,而且当初的太平盛世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这种紧跟政治和时代的应制文风,也必然会随着政治时局的转变而衰落。《四库全书总目》卷170《杨文敏集》提要称:“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并回护后来之衰,亦不可以后来之衰并淹没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与荣哉。”我认为这是对台阁体比较公允的评价。
三、关于家族教育
《明史》称杨士奇有学行。有学行又居高位,杨士奇应该不仅会“治国平天下”,更会“齐家”,我们从《杨氏族谱附录·文贞公家诫》可以看出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他虽然远在京师做官,但不断通过书信的方式训戒自己的晚辈,要诗书传家,团结乡邻,安守本分,不能借他的势力欺负人。他的一个侄子在衙门做事,有次用官府的纸张给他写信,竟因此而遭到了他的训斥:“尔在衙门内岂可向人索官纸写私信?虽是半张,亦系官物,但举发即有罪,今后切戒,毋蹈前非!”(《文贞公家诫·示侄孙挺》)凡片纸之利,只要系官物,亦不图之,其廉也若此。
对待后辈,他首先是不思广置家产,而是再三劝戒他们努力读书,不可断绝读书种子。他在正统二年《文贞公家诫·示长新妇》中讲道:“吾儒者之家,不可思量要富,户下田不许过百二、三十石,户下粮不过三四十石,尽足岁月,切不可过多。过多则后来必累子孙,为父母不可无远虑,切记切记!只是许多田粮在户,后来科举,子孙也自难当。”在大地主阶级开始大肆侵吞百姓,兼并土地的时候,士奇仍然坚持不让子孙广置田产,这种思想真是难能可贵,他和那些千方百计渔肉乡民的贪官豪强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在《示稷子》中写道:“吾儿须谦和处乡里,凡事忍耐,不可使气性,但凭道理为上策也。子路大贤,喜闻自己过失,所以令名无穷。今人有过失,不喜闻规戒之言,所以终陷为小人,而灾害及矣。吾儿自今宜勉力为善,有人进善言者,便虚心听从,切不可拒善言不纳也。”“乡邻有过一切容之,勿与计较,凡灾伤之处,田租当体恤宽免,慎毋过刻也。”他教导儿子谦和处世,宽厚待人。对一些违法不善者,不惜劝戒族人动用家法,甚至送官治罪。“吾先世皆贫,然从来清白相传,不肯苟利。故出仕者皆有冰蘖声,……”“子侄有善行好学者,交共礼之重之。若有分外不律,不受训诫者,稷会诸兄弟数其罪而笞之,不可容恕。如又不悛(改过),明告于官,请治以不孝之罪。”(《文贞公家诫·示侄孙挺》可以说在对家族成员如此严格要求、严厉训诫,在中国历史上的大臣中也是不多见的。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也许因年老体弱精力所限,也许是杨稷顽固不化,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
一生清廉,严于律己的杨士奇哪经得起这样的打击,一代名相最终忧郁而死。
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泰和人罗璟(1432-1503),字明仲,号冰玉,明朝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探花,自小生活在杨士奇家,后科举入仕任职翰林院,应该说耳闻目睹了杨士奇的言行,他对杨士奇的德行非常称道,在《冰玉集》中载:“燕山岳先生正,姑苏陈先生鉴,琼山邱先生浚,适同史事。三先生博学,傲睨一世,人物少可其意者。独推服公,谓公立朝遇事直言,虽忤不易,类唐魏征;处置大事不动声色,类宋韩琦;有拥立功口未尝言,类文彦博;凡有荐引不使人知,类王旦;心在国家生民,先忧后乐,类范仲淹;文章雍容醇厚有三代气象,类欧阳修。”时人有如此高的评价确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