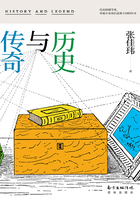贝,又称贝壳,为海洋特产。就其功能来说,见诸于历史记载的不外有两种,一是作为货币;二是作为饰品。
在我国,贝是最早的一种货币。《尚书·盘庚》中载有:“兹予有敌政,同位具乃贝玉。”疏:“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在商周时期的墓葬里,经常出土这种贝币。此外,贝作为货币这一点,可以从汉字的结构上看。如:贵、贱、买、卖等字都是从贝得义。可见在这些字形成时,贝壳已是价值的尺度了。在中原一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统一了币制,废除了贝币,改用钱币。而在云南一带,贝币一直使用到清朝初年。《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云南民族“用从海里捞取一种白贝壳作为货币,亦可作为项饰……”谢肇《滇略》卷四《俗略》:“海内货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诸海中,不远千里而捆致之。”
再从审美的意义上讲,现今世界所有的海洋民族几乎都风行珠贝装饰。如爪哇人、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等等。就云南的少数民族而言,以贝壳制成饰物连缀成美丽的图案缝在衣服的明显处以示其美丽的民族,也很多。除此而外,贝壳在一些民族中还具有代表生殖繁衍的意义。
不过相比之下,基诺族对贝的崇拜则更为虔诚,贝在基诺族中不仅具有审美的价值,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宗教意义上,贝是基诺族所崇拜的神灵中最为神圣的一种神灵的象征物,因而在基诺族的贝崇拜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贝壳,基诺语称“伊叟”。是基诺人所崇拜的“贝神”的象征物。贝神主要有三个,即“雷贝神”(或称天贝神)、“谷贝神”、“山贝神”,有的村寨有五个或七个之说,但根据调查,都是从这三个主要贝神派生的。雷贝神,基诺族称为“努发伊叟”,主管人的命运,部分基诺人认为这个神就是司生育造人的丕嫫女神。谷贝神,基诺族称为“伐靠伊叟”,主管农耕方面的女神。山贝神,基诺族称为“啦特伊叟”,主管野兽和狩猎的女神。
在基诺人的观念中,基诺族的巫师白腊泡就是因为拥有了贝,而脱离了自身的控制,成了贝神的代言人,可以往来于阴阳两界,替神赐福,为民治病。但一个人要成为白腊泡,不是靠师承祖传,而是与天意有关。要成为白腊泡的人,必定会有预兆,据白腊泡本人讲,曾遇到一些完全不符合现实生活的离奇现象:如去打猎,安置在林中的扣子会扣住鱼;才猎到的麂子,肉里会有蛆;采来的野菜煮熟后会变成肉;其最关键的是在他的生活中会突然出现贝壳。贝壳的出现在基诺人的传统观念中就意味着贝神已经来找它的代言人了,如不举行剽牛仪式与贝神结为一体,就要深受其害。因此,凡在生活中有贝壳出现的人,都要慎重其事,用自己的衣服包上米和蛋,请老白腊泡为其算卜,以确认是否贝神来找。确认后,立即着手准备仪式用品。
此仪式为剽牛仪式,一般需准备一头水牛、一只狗、三至七头小猪、一对鸭、鸡若干、酒米、蜂蜡、槟榔、绿肉包、粽子、皆波花,矣波罗花、炮仗花、半生半干的树皮、老母猪棕、笋叶壳、不死叶、灯台树板、胖登果树蕊等等,并请一约卡约卡:基诺族对于助手的称谓,本意是“女性长者”,即老奶奶,后来各种议式中的助手均由男性承担,但仍沿用此称谓。
“贝神”的象征物贝壳的木制小屋。这种小屋用红椿木板制成,一尺见方,板壁上贴有胖登果树蕊(像泡沫塑料状)切成的薄片,里面铺上傣族织的白细布。待一切都准备好后,即去借来锣、钹,然后请寨中会算日子的老人算好举行仪式的日子,在仪式的前一天去请父寨的老白腊泡为其主持仪式。仪式前的夜晚,主人在家准备仪式所需祭品,父亲寨的老白腊泡则在自己家中,根据主人所述情况,杀一只公鸡,鸡血留在碗中,半夜时分,端上鸡血到阳台上去召唤将与该主人结为一体的贝神。
举行仪式的这天一早,由主人去村寨长老卓色家请出公木鼓。寨中小孩应邀帮主人上山摘花,扎成4个人形花架放在寨外路口。然后主人率全家迎至寨外。待父寨的老白腊泡来时,锣鼓齐鸣,由4个青年抬着花架随老白腊泡之后进寨。进寨门后,后面两个花架逐一被儿童抢拔一空,意为献给寨神后面的众鬼神。留下的两个待进主人竹楼时又被抢拔的只剩下两个花架头,意为献给了无名婴儿的鬼魂。两个花架头即是献给贝神的。此时,父寨的老白腊泡、本寨的白腊泡和主人先行祭鼓,然后在正厅摆上祭品,念诵祭祀贝神的经文,待念诵完毕,3人绕“转柱”3圈下楼,象征性地给水牛洗澡、喂食,然后用剽将水牛杀死。3人上楼继续念诵经文,待饭后进行“蒙贝”。
蒙贝时,父寨的老白腊泡先祭祀贝神,然后用锣做托盘,中心粘上一块酸蜂蜡,锣内装上不见太阳的水,浸泡上9片生姜,交由约卡双手托住。老白腊泡手执黑扇念念有词,念诵到一定时候,将扇子往锣上一扣。待打开时,如果锣的中心酸蜂蜡上粘有一对贝壳,即表示贝神已经与主人结为一体。当下锣鼓齐鸣,庆贺主人成为白腊泡。老白腊泡立即用酸蜂蜡将这对贝壳对面沾拢,交给主人捧着请在场的人观看,看毕用红布包好,珍藏在“吐玛吐玛:基诺语,类似荷包一样的小包,专来来放贵重物品的。”里。父寨的老白腊泡、本寨的白腊泡和新成为白腊泡的人,一道绕着“转柱”跳舞,后面跟着手执刀、斧、锄的4个人,再后跟着5个人,各自抬着牛头、猪头、狗头、抱鸡抱鸭,最后一人背着酒菜,众人舞至竹楼外阳台上,吃完背箩中的东西,仪式就算完毕。第二天祭鼓后送走父寨的白腊泡,将鼓还回卓色家,主人就有了神赋的权力,可以替人看卦占卜,主持祭祀活动。如果说白腊泡扣扇子后再打开时不见有贝,或只有代表主人的一个贝,则表示贝神未与主人结为一体,主人就只能算个预备的白腊泡,仍不能独立主持祭祀活动。
因此,凡成为白腊泡的人,就要在家祭供“白腊泡内”白腊泡内:即基诺族巫师白腊泡供祭的贝神象征物,也就是放在特制的神龛中的贝壳,也可说就是贝神。并准备白腊泡的法衣法帽和剽。出门主持仪式时,由约卡扛着公剽在前开路,家人随其后。举行祭祀仪式的主人均需前来迎接。白腊泡做完仪式后,将所获报酬带回家,供奉在“白腊泡内”前,向其报告祭祀情况后,物品方可动用。但是不同的白腊泡,根据其所执有的贝壳的不同,分别代表不同贝神的意志,主持与该贝神有关的各种仪式,每隔9年,都要剽一次水牛,以表示对贝神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但是,贝壳在基诺族中,不同的支系有不尽相同的观念。在基诺山区的“阿细”、“阿哈”支系中,贝壳为白腊泡专有,是贝神的象征。而在勐旺区的“乌尤”支系中,贝壳仅是灵物的象征,为了避邪,在小孩出世前就要为其准备一顶小帽,上缀有一对贝壳、两片姜、两根小狗趾骨和一点铁器,待小孩出生后戴,戴至两岁时收起,结婚时取出,与对方的贝壳沾拢放入衣箱,又待生孩子前做帽子上的避邪物。丧葬时,老人一定要带走贝壳,否则认为过不了“干沟”(阴阳两界的分界处,有鬼把守,要将贝壳送给把守干沟的鬼),回不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司杰卓米。这些观念流传至今,但因现在基诺族中要找到贝壳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没有贝壳的人家就改用铜钱替代。但贝壳在他们的观念中,仍是用来避邪驱魔,保佑人畜兴旺繁衍的重要物件,这与其他民族中对于贝的认识是根本不同的,几乎没有货币的观念和审美方面的意义。在周围民族大都把贝作为货币和首饰的情况下,基诺族这种独特的观念,无疑是值得注意的。
众所周知,聚居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基诺山的基诺族,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大家庭正在崩溃的历史阶段,在他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因此,基诺人把贝壳视为神圣的东西,绝不是崇拜那呆板的物件,往往是对附会在那物件的超自然力量的崇拜。
人类最古老的一种生殖象征,就是一个简单的圆圈。中国有句成语“如环无端”,表示万有的无始无终,包罗万象。因此,圆便成了母亲、女人及“地母”的形象符号。那么,贝壳也可以说是代表实物形体的符号,爽直地说就是代表女性生殖器的符号。这一现象并非是基诺族所独有的,在历史上,人们常常把维纳斯和贝壳一起表现,解释说这暗示着她是从海洋中产生的,贝壳是同海相联系的。而维纳斯既是性爱女神,那么与贝壳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就不难理解为一种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之说。在罗马埃斯库拉皮由斯神殿里的一块还愿匾上,仙女们手拿贝壳,她们手拿的位置表明贝壳作为女性生殖器象征的意义。在罗马,人们进入神殿崇拜神灵之前,先用手指蘸圣水器里的“圣水”,接着亲吻手,把水向神洒去(飞吻),盛圣水的圣水器通常是贝壳的形状。
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谈到基督教时曾说:“所有异教的核心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崇拜自然。在所有异教中,自然的最深刻和最使人敬畏的属性是生育力。生育力和生成的神秘性是自然的最深刻的神秘性。”在很早以前,女人的生育能力就已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力量,受到赞美和崇拜。尽管在大多数宗教里,男性始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但在基诺族的宗教里,女性始祖是根本的神。这一点是与基诺族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虽然母系氏族制时代在基诺族中已成为历史,但是,在基诺族的风俗习惯和口碑传说中,仍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女性在世时是氏族长老,去世后是氏族的祖先——神。而且,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制约下,妇女所从事的采集和原始农业栽培是获得食物的主要来源,更兼妇女们在主持家务、养老育幼、制衣执炊、繁衍后代方面的能力,无可争议地构成了母系氏族时期妇女受崇拜的地位。加之原始时代人类生活的中心内容和根本目的就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大生产在原始观念中常常是具有同一性的。把贝崇拜与基诺族特定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联系起来,再与人类求生存和繁衍的目的联系起来,就可以得知贝崇拜实际上就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其深层涵义是人类自身的生产问题。
这种产生于母系氏族时期的贝崇拜意识,随着母系氏族解体、父系制的确立,必然会产生新的变化与发展,这种情况形成了基诺族的巫师白腊泡(基诺族的白腊泡均为男性)通过一系列神圣的仪式,与贝神结为一体,充当贝神的代言人的情况。这一点与基诺族的社会发展也是相适应。正因为贝壳被当作最神圣的女神长期受到膜拜,所以,基诺族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比较高,“母亲当家”、“妇女是家主”这类母系氏族制时代的传统不仅仅是一种流行在口头的成语,它在实际生活中还具有习惯法的效力。直至解放初期,基诺妇女在隆重的祭祖仪式“上新房”仪式中,仍以家主的身份首先登上新竹楼认家,并点燃火塘后,其他人方可上楼。在家庭离婚时不仅可以按习惯法带走自己规定带的财产,还可以带走全部孩子。在孩子生病时,也只有母亲才具有为生病孩子祭鬼招魂的权利。这些现象,在周围民族已进入封建社会或封建领主制社会的情况下,在贝壳已成为周围民族所喜爱的货币或首饰的时刻,不仅没有被融合,而且以其独有的风采保留下来。这固然与基诺族长期居住在偏僻闭塞的山区,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发展缓慢有关。但也可以说是基诺人对贝崇拜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