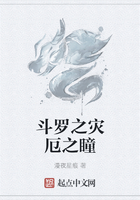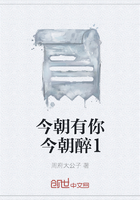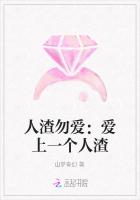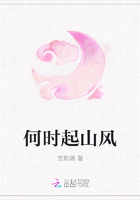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讲授中,应该着重于整个世界文学总体发展的文学路径的描述,就像绘制文学地图一样,在各民族文学总体特征的比较、概括中,注重不同的文学形态的类型划分和对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对文学作品表现内容和方式的制约。通过深入研究,尽量廓清世界文化发展总体线索。不仅做到东、西方文学并举,更重要的是以比较的方法,打通东、西方文学的共时性联系和差异,以宏观的视野,引发学生对人类文学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因此,需要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的分期,打破外国文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陈旧分类法,以崭新的理念和逻辑框架对外国文学知识元素进行重组和定位。在教学内容体系中,世界文学史分期不一定完全以社会形态和阶级属性线索作为标准,且宜粗不宜细。可以将东、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比较,把整个世界文学史参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17世纪~19世纪)和现代文学(20世纪文学)。对过去划分比较混乱的中古文学和近代文学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整理、分类、合并。将中古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划在16世纪末。以便将中古时期的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限下考察研究。将17世纪到19世纪东、西方文学统一合并为近代文学。这种划分,目的是为了更连贯地理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发展与文化、文学发展进程之间的联系,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下,考察东、西方文学的总体规律。这样的教学内容体系避免了对外国文学支离破碎的讲授,让学生形成宏观文化视野,并对世界文学的演进过程作规律性的把握。
除了对世界文学史分期进行调整外,对每一时期的东、西方文学现象也应作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例如古代文学时期,我们不一定为了证明教学体系的博大厚重,就一定要从几大文明古国所有文化现象说起,能不能直接从文学起源及最早的文学主要样式入手,以口头文学的主要样式:神话、诗歌、戏剧发展过程为线索,在文学样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东、西方文学都存在的典型样式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神话,我们可以对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和古希腊神话进行总体研究,既总结出各民族神话的共性,又寻求制约着不同体系的神话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同时从希伯来文化与巴比伦文化之间的血缘传承和变异中,比较巴比伦神话与希伯来神话相似的基因以及变异。而史诗和戏剧则同时对希腊史诗、戏剧和印度史诗、戏剧及其他民族早期史诗相比较,或以“平行研究”,或以“影响研究”来了解世界史诗文学存在的不同形态。这样的比较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说明东、西方文学之间,并非是截然划分、互不相干的文学形态,而一开始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处理史诗问题时,由于过去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体系都预设了古希腊史诗的标杆作用,一直以来,学者们费尽心机去阐释,中国为什么缺乏史诗性作品。其实,站在世界文学这一整体的角度,这个问题也可以倒过来问,为什么西方缺乏中国那样的抒情性短诗。在诗歌起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民族特性的不同,出现了哪些典型的诗歌形态。在这样视角的提问下,就可以认定古希腊的叙事性史诗和中国的抒情性短诗分属于的不同类型的诗歌形态,而且各自成为自己民族文学的源泉。这样,中国的《诗经》和荷马史诗,就无所谓优劣,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典范性。
这里涉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疆界的新问题,即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中国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和世界文学史的对象,是否应该进入该课程?如果要进入,应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讲授?笔者的看法是:从世界文学总体发展格局中,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多元存在和发展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在哪些方面具有典范性?如果涉及上述问题,中国文学现象就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如果与上述问题没有联系,则不必在世界文学的知识框架中涉及中国文学。不然就很可能将世界文学史讲成了东、西方比较文学。
另外,中古时期是世界格局变化最剧烈、最动荡的时期,也是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态变化最难以捉摸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将文艺复兴运动从中古时期分离出去,自成一体,其依据是以社会性质和阶级属性,来强调人文主义文学作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划时代意义,但这样却完全割裂了宗教文学与人文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将西方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滋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演化过程,分离成静态孤立的现象。这样便无法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讲清文学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密切关系,也割裂了一些文学类型之间的有机联系,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共同的基督教色彩。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信仰与理性、神性与人性之间此起彼落的矛盾张力。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的兴起,不应视为完全是与宗教文学的对立,而是基督教文学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人文主义文学对“人性”的大力张扬,实际上也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笼罩下展开的。从这一角度,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阐释《神曲》作为基督教文学的经典之作的价值意义,而不会有“落后的基督教因素和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矛盾对立”之迷惑。因此不宜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为不同质的文学,硬性划分出去。
一般的文学史还将中古东方文学延续至19世纪,给人的印象是东方文学辉煌一段时期后,就进入漫漫的落后时期。由于中古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在时间划分上的不一致,就无法在一个时空的横向比较中,把握其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和总体特征。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整个东方文学从14世纪到18世纪几乎完全缺席、失语,形成教学和研究的空白。因此,将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到16世纪之后,有利于在世界整体格局中把握其内在联系。
应当说,在中古时期,世界三大宗教先后确立、发展和扩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形成或者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政教分离的紧密关系。东、西方的主要地区以三大宗教为纽带,大致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因此,当时东、西方文学中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呈现出深厚的宗教色彩,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一。
同时,随着三大宗教的发展和扩张,在三大文化圈之间,形成剧烈的冲撞,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战争不断。基督教文化圈的扩张带来东、西方文学剧烈的震荡,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世界虽然多次进行十字军东征,以武力征服了东方,给东方人民巨大的灾难,但东方文化反过来给西方文化以极大的刺激。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东方因素。碰撞过程中的交融也就包含着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过程。不同文化圈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与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处于活跃状态。相同的文化圈内,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交融也同样如此。如在佛教文化圈内,虽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衰落,但它播散到亚洲各民族之后,与其他民族的本土文化融合,又产生变异。从这个角度认识当时的很多具体作品,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发掘《堂吉珂德》、《源氏物语》、《一千零一夜》、《西游记》这些作为世界经典着作的跨文化价值。因此,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具有先导性质,而且在彼此的渗透、融合中,促使西方文学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二。
17世纪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学中理性与情感因素,越出宗教藩篱,轮番主宰文坛,成为近代社会主导性趋势,也成为文学的主旋律。这一趋势在历经18世纪之后,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之后的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有一次大回旋。在此运动过程中,宗教的躯壳褪尽脱落了,但基督教信仰中“神秘”和“爱”却一直熔铸成西方文化之魂,成为文学表现的最高境界。
近代文学时期,可以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不以国别文学为主要线索,而从文化圈理论入手,找到这一阶段文学史构架的基本思路。文化圈的碰撞不仅是中古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近现代甚至当今时代的文化特征。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扩张,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头队伍的西学东渐形成强大的文化扩张态势。大量珍贵的文物和文献资料通过各种途径流到了西方,许多实用技术也被西方吸收运用。凭借殖民扩张的强势,西方文学确实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东方文学。但即便如此,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冲击与回应模式,“东学西渐”的状况仍大量存在。东方文学作为与西方文学形态迥异的独特类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文学在表现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深度方面,有东方文学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那么,东方文学在意蕴、哲思表现方面,在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方面与西方文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泰戈尔、纪伯伦、曹雪芹、川端康成等人的创作,从世界艺术水准和体现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而言,并不亚于托尔斯泰、乔依斯、爱略特等文学大师的创造价值。因此,在教学中,如何重点选择东、西文学的典型个案,将能够联结东、西方文学的重大文学现象和重要作家作为教学重点,是有效整合东、西方文学的关键。比如日本文学在西方文学和亚洲文学中发挥的“桥梁”作用,还有在传统和现代剧烈冲突中探索前进的阿拉伯地区文学。
总之,从建立真正的世界文学史的愿望出发,吸收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的分期,以史论的形式重新选择、组合有利于体现世界文学总体发展规律的知识,必然减少外国文学中支离破碎的知识的信息量,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给学生以宏观的文化视野,进而清晰地把握世界文学演进的规律。
主要参考文献
[1]蒋承勇.世界文学史研究中多角度观与整体思维.外国文学研究,1993(2):120
(陈俐,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语言素质能力与“现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
——压缩基础课课时,培养语言素质能力的思考
赖先刚
摘要:依据科学是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的观点,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素质能力的层级性。据此,本文讨论语言素质能力与语言课程教学的关系;提出为提高学生语言素质能力,“现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教改设想;说明课程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素质能力;层级性;“现代汉语”;系列课程;辩证关系。
1983年,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其《智力的结构》(Frames of Mind)一书中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其中言语-语言智力(linguistic Intelligence)指“包括用语言思维、用语言表达及洞察复杂内涵的能力”。本文所说的语言素质能力,与加德纳所指的言语-语言智力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涉及思维、表达、理解的问题,包括语言的运用能力、潜在的语感能力和语言研究能力。
在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如何提高学生母语的语言素质能力,仍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文首先讨论语言素质能力与语言课程教学的关系,然后提出为提高学生语言素质能力,“现代汉语”系列课程(包括基础课和后续选修课)建设的设想,最后说明课程建设的意义。
一、语言素质能力的层级性与语言课程教学
我们认为,语言素质能力是有层级性的。李雁冰在《课程评价论》一书中写道:“科学是内在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和工具价值(intrinsic values)的统一”。“内在价值”,即一事物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一事物对自身的有用性;“工具价值”,即一事物对别的事物而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事物对他事物的有用性。对于提高语言素质能力,语言课程的科学性也体现在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统一上。借助于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素质能力的层级性,可分为四个层级关系。
(一)语言的加工运用能力与语言课程教学
提高语言的运用加工能力,体现语言课程的工具价值。语言的加工运用能力包括书面语的表达和理解(说、写)和口语的表达和理解(听、读),即语言编码和解码的能力。加德纳教授对“言语-语言策略”的把握,也锁定在“听、说、读、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