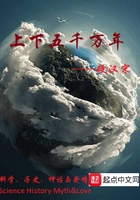3.《语丝》群体的思想转换
虽然一度共同服膺“闲话”之风,但是《语丝》群体的思想分歧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分歧是这些知识分子后来各自思想转换的基础。
鲁迅所提倡的Essay与“闲话”风是有特定背景的,即在沙漠里走来走去,找不到革命的方向时才作一些散漫的文字,这是一位彷徨者在知识分子作为文化革命的主力被时代边缘化后,在归属“革命”阵营或保持自身独立之间的犹豫。所以在《野草》里鲁迅充满了痛苦与绝望,但在绝望中,鲁迅依然要前行,他是不甘于黑暗里的寂寞的,鲁迅将自己定位于思想界之斗士,以笔为匕首和投枪,与黑暗世界作殊死搏斗,他把文学活动看做是服从思想界斗争需要的,推翻旧时代是鲁迅的第一选择,所以在《野草》里,他总是给自己一点希望,以求能够走出这“坟”,再次呐喊奋起。因为有了这样的选择,必然要和周作人、林语堂走上不同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继续以闲适幽默为文学寻找一个自由的可能性,与鲁迅有了不同的文学价值认同,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不管是周作人还是林语堂,作为自由知识者,他们都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一半是自愿,也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思想文艺倾向;一半是被迫,也就是这里要分析的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周、林着力创作闲适散文,与当时混乱的社会境况是有联系的。
周作人曾说过一段常为人引用的著名论断:“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他解释道:“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而到了“王纲解纽”的时代,“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周作人斯论颇具道理,因为当历代政权机制处于强盛时期,该政权统摄下的权威思想必然要控制整个社会意识,并不期然而然地赋予人们以共同的价值规范、行为准则。在此情形下,抒发个人情致的“言志”小品存在和发展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到了“王纲解纽”的时代,人们原先所处的大一统的社会结构逐渐松懈或瓦解,权威思想开始削弱并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于是,作为对历史和时代的一种感应,文学中抒写个人情趣的小品文自然也就有了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广阔天地。
1925年1月开始并持续一年之久的北京女师大事件;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市民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酿成了“五卅”惨案;1926年3月18日发生于北京的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200余示威群众死于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刀枪之下。同年暑期,林语堂南下到厦门大学任职,结束了在北京近三年不平凡的生活历程。当时,北京知识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南下,大批人到上海或广州。仅三个多月,在鲁迅辞去厦大教职之后,林语堂也不得已离开了厦大,来到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任秘书,六个月后又毅然辞去。1927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4月12日,风云突变,******为了“清共”,在上海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革命知识分子和群众惨遭屠杀。随后,广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也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8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实行“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汪精卫的背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周作人、林语堂和一切正直的人士所能感觉到的“中国新日子的曙光”突然消逝了。3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更加复杂多变。
1931年1月,国民党改组派宣布解散,******打垮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确立了其独裁政权。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人民掀起了支援抗战的热潮。1932年12月18日,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林语堂担任宣传主任。同盟致力于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活动,努力营救被国民党非法拘禁的进步人士。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就加强了文化围剿,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新出图书呈缴规程》等一系列条例,严密控制文化出版领域的不同见解与思想,稍有不慎,报刊杂志就被查封,有关人员就遭拘捕。
在这样的境况中,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就将《论语》的生存置于重要的地位。在林语堂所制定的《论语社同人戒条》中,也可见论语派的这种力图求生存的中性立场与态度:“一、不反革命。二、不破口骂人。三、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做有津贴的宣传,但可以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从这些戒条中,也都可见论语派的态度与策略。
1930年,周作人在《(草木虫鱼)小引》中说:“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笔祸。”这种“不想杀身以成仁”的态度,显然是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中的一种求生策略。林语堂经历了1927年大屠杀后,在震惊的同时也真切地意识到“头颅一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的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若再提倡激烈理论,岂不是又与另一个‘革命政府’以不便?”讥刺之中含有无赖,从此改变了腔调,由激烈而转为平和。
以上的论述中所呈现出的社会、文化状态无疑都为30年代小品文热和围绕“闲适”话语展开的小品文论争埋下了伏笔。
“闲适”理念的中外文化资源
闲适小品文在现代文学中****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半期,闲适小品文已经盛极一时,报纸副刊纷纷开辟专栏。最先从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起,提倡“以幽默为目标,而杂以于谐谑”、“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人们从林语堂的成功顿悟大众文化的巨大需求量以及闲适小品的广阔市场前景,上海滩上此类刊物骤然增加。据统计,1934年全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物三百余种,而且是所谓‘软性读物,——即纯文艺或半文艺的杂志;最近两个月创刊的那些’软性读物,则又几乎全是‘幽默’、‘闲适’与‘小品’的合股公司”。黄嘉育主编《西风》,谢兴尧主编《逸经》,海戈主编《谈风》,施蛰存主办《文饭小品》,此外还有《天地人》、《西北风》、《越风》等等,都与论语派小品文创作有关,为小品文创作提供了天地。
同时,废名、郁达夫、朱湘、丰子恺、俞平伯也都被卷入小品文创作中,创作出大批幽默风趣、冲淡悠然的散文小品,1934年因此被称为“小品文年”。
在这种“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的局面下,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不断撰文对小品文展开批评,还创办了《太白》、《新语林》、《芒种》等刊物来提倡创作更具有战斗性的杂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文人也撰文辩驳,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态度,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小品文的论争,恰恰是在这样的论争中,“小品文”为什么要“闲适”的理念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说明,有助于我们从中把握其内在的思路。
1.在传统中发现现代
周作人、林语堂二人一直在为“闲适”话语寻根,以支撑自己的理论构建。
论语派成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在更为“中国化”的意义上,自由可以理解为是某种形式的自在无为。这种自在无为,最主要的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论语派对个体自由的执著,部分也是植根于道家文化。
在《散文一集·导言》中,周作人提出:
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
周作人所称的“外援”,即英国的小品文;而“内应”——“历史的言志派的文艺运动之复兴”,指的是晚明小品文。晚明小品文代表作家张岱是绍兴人,周作人借重刊张岱的《陶庵梦忆》之机,在序言中指出:
现代散文与其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勿宁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明代是古文与理学全盛的时代,然而明代的小品文家却敢于大胆地反抗理学与礼法。从而造就了晚明抒情小品的灿烂,其历史功绩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现代人读晚明小品时,很难从中感受到现代的人追求解放的气息。
这当然是溢美之辞,但也看得出周作人的良苦用心。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表明文学的发展与一治一乱的中国历史相似。他不止一次地感叹:“我说如今很像明末。”“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事实上,论语派同仁认同晚明文人,原因之一就是晚明的乱世与现在很相似。既然是循环,那么过去的同样会出现在“现代”,而看似“现代”的东西,说不定也是“古已有之”。有研究者注意到,“论语派所采取的话语策略是强调封建与现代的对立而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这里的“封建”并非仅仅指过去的一个时间阶段,而是指一种价值判断,就像“现代”一词,既是时间概念也隐含着价值评判一样。周作人对历史人物、事件、人类生活现象的解读,使他得出“旧鬼”和“重来”的结论:过去的历史从来不因时间流逝而消失,而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活在现实之中。传统与现代之间并无一条乐观的分界线,而是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周作人因此一方面批评现实文化和社会中的种种封建复古(例如当左翼作家们指责小品文专门谈论一些幽默、闲适、趣味话题因而显得“小”时,论语派的精神领袖们却认为左翼文学的兴起表明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思维模式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从看似“古代”的事物中,找到了“现代”新事物的源头。这后一方面最著名的工作之一,就是众所周知的将现代散文的源头上溯到明末公安、竞陵一脉。
偏爱小品文,并将现代散文追溯到明末公安、竟陵,论语派同仁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并非将此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而是将它区分为两类:文学上是“载道”与“言志”二分,而其背后更深层的则是儒、道二分。前文已经提到,论语派同仁认同的是袁中郎一陶渊明一老庄一脉,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认同首先是情感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互补,论语派同仁对此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林语堂在很多地方都谈论过这点,并丝毫不掩饰他对道家的偏爱,以至于后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研究者都认为他属于“道家”。儒家占据着正统的地位,道家则处于边缘。一个文人往往在得志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自由知识者的论语派们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一半是被迫,一半也是自愿。这种自我边缘化或许有些无奈,其中也有着明哲保身的意图,但这行为本身便含有反抗“中心”的意味。周作人、林语堂们之所以发掘历史上的小品文,原因之一也是小品文与“文章”相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从来就是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小品文在他们眼里成为反体制、反一统、反功利主义文学的英雄,成了异端思想、叛徒精神的代名词”。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同样因畏惧“庙堂之高”而甘于身处“江湖之远”的晚明文人和陶渊明、庄子等自然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实际上,在对晚明小品文的鉴赏、把玩、模仿中,这些自由知识者们在不知不觉中即与那些作者们的心境达到了契合。
说论语派偏爱小品文,偏于道家,也就理所当然地涉及了论语派在文学上所强调的“闲适”。这个重要概念是植根于道家思想的。
论语派“闲适”话语的正式亮相,是在1934年《人间世》的发刊词中。其完整的表述是小品文创作应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以自我为中心”好理解,即是对个人主体性的执著。“以闲适为格调”则不太好理解。总体来说,“闲适”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指文体风格,一是指思想情致。前者暂且不论,就后者来说,“闲适”指的是创作主体的心闲意适。它是对一种超脱尘世喧嚣的古典境界的向往,追求个人自主,从而实现个人精神的高度自由。它也是安静平和、追求雅趣和风格的文人的表现。可以说的是,林氏的“闲适”实际上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一个作家只有在“闲适”状态下,才能维护自我人格的独立,才能保证自我精神的自由,才能不受任何外在于自我意志的权力话语的驱遣而“独抒性灵”。这也就是“在取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论语派同仁推崇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等,主要是推崇他们所达到的这种超然的境界。
将中国传统文化二分,并认同于道家文化,论语派同仁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中关于“个性自由”资源的努力发掘,这一行为表明,他们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出“现代性”因素。这同时也表明他们尽管向传统回归,但根本上还是认同于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当然,这里还存在着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面。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社会的出现、发展看成一个“祛魅”的过程。“祛魅”指的是世界图景和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建构,致使宗教性的世界图景崩塌,随之而起的是一个世俗化的文化和社会成型。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遵循着一种“启蒙的辩证法”,人对自由、解放的追求却使得人性受到物质文明的束缚,科学的理性主义换个角度看也是对人的感性生命的钳制,工具理性的盛行使得人成为现代社会的工具和仪器,从而处于机械化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论语派强调“闲适”、“性灵”,对道家文化资源的发掘,对超脱的向往,实际上也隐含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当林语堂出国后向外国人大谈中国文化(其实他所谈的主要是道家文化)时,其以道家文化来救治西方现代文化之不足的意图就更明显了。
“闲适”虽然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但对于论语派人来说,其直接的来源是晚明的公安、竟陵一派。众所周知的是,1932年2月,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了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在这次讲演中他首次重提了性灵文学,并把明末性灵文学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解放运动而与新文学联系起来。他把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格律”作为古代文学中反对复古主义、反对模仿、反对文以载道的“赋得体”,而能容纳真诚个性的文学观念,由此接通并等同于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八不主义”主张。他因此认为“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论语派的灵魂林语堂对“闲适、性灵”的阐发就是直接受周氏影响的:“周作人谈《中国文学的源流》-书推崇公安竟陵,以为现代散文直继公安之遗绪。此是个中人语,不容不知此中关系者瞎辩。”其后,他“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钞》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竞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由此才引发他“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般的兴奋。
周、林等人的这种对“闲适”的选择,一半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逼迫,一半也是出于主动的选择。这种主动选择即是在保全个性的旗帜下将生活艺术化,从而“得体地活着”。周作人曾经把中国古代文学史视为“载道”与“言志”的循环。“载道”文学是“赋得”文学,所谓“赋得”,即是被动地听从他人的旨意而作文;“言志”文学是“即兴”文学,所谓“即兴”,即是自己因感而发,毫无拘束地作文。“论语”时期的林语堂对“即兴”文学“我手写我口”的阐发更是不遗余力。
2.对西方文化的取舍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周作人认为新散文成功有两重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并认为“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
这段论述表明了周作人认为中国现代散文(小品文)的源流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相结合。周作人所称的“外援”,即英国的小品文。英国的小品文之影响有两个层面:在深层结构即思想意识层面上,“英国的小品文”吸引中国作家普遍关注的,首先是它那浓厚的个人色彩,比其他散文样式更自由、更直接、更充分的“自我表现”精神。这里,周作人所说的“英国的小品文”是指最早出现于法国、后在英国发展起来的“essay”,它通常被称作随笔,也译作美文、小品文、絮语散文或随笔散文等。这种外国随笔的内在特质是作家的“自我表现”。对此,它的创始人蒙田说得非常坦白:“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底平凡、纯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我底弱点和我底本来面目,在公共礼法所容许的范围内,都在这里尽情披尽。”显然,周作人、林语堂等作家原先所具有的“人本主义”思想与外国随笔“表现自我”的精神传统神交气合,于是外国随笔在他们那里找到了在中国生存、发展的机缘。从表层结构,即文体特征、语言思维模式等方面看,中国“闲适”散文作家对外国随笔艺术的借鉴几乎同样不容忽视。周作人欣赏的“如在江村小屋里”、“同友人谈闲话”(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的散文境界,林语堂喜爱的“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笑”、“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人谈心”(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的散文笔润,都明显受外国essay风的影响。
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对林语堂而言,西方自由主义文学尤其英美自由主义文学较多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的主体观。可以这样说,主要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促使林语堂确立了“闲适”话语自由独立的文学立场,坚持了对文学主体性的维护。
自由主义是贯穿西方社会几百年的一种主要社会思潮。因此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作家大多是自由主义作家。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从总体倾向上看始终充满了自由主义精神,其突出表现是对创作主体自由独立品格的强调,对个性自由的张扬,对“人”及人的生存境界的关注。这些观念对林语堂的文学观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闲适”话语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对自我表现的张扬,对创作个性的尊重,可以说都是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影响。林语堂在推行自己的“性灵”文学观时就曾将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引为同调。他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就是“性灵”的自由展现,因此他明确地将西方浪漫主义精神同“性灵”等同起来:“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的普通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也正如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
林语堂还认为,晚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说与西方表现派的文艺思想相一致,“真如异曲同工”。因此,他对西方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大加赞赏,对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之说极为倾倒,并提出如下见解:“除表现本性之成功,无所谓美,除表现之失败,无所谓恶。”林语堂引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和表现主义美学为同调,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表现主义美学都强调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这不仅与林语堂推崇的“性灵”说灵犀相通,或如林语堂所说是“异曲同工”,而且由于这种文学观念强调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作家主观情志的表现,从而和形形色色的片面要求文学发挥革弊兴利、改良社会、服务政治作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划清了界限,从而使文学回归“人”(主体)自身,回归“艺术”(本体)自身。这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一种文学语境下显然是一种有意识、有针对性的文学选择。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梁实秋在《现代中国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曾有很精确的概括,不妨引来作为林语堂“闲适”话语与西方文学关系的佐证:“全部影响之要紧处乃在外国文学观念之输入中国。换言之,我们自经和外国文学发生接触之后,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完全变了。我们本来的文学观可以用‘文以载道’四个字来包括无遗,现在的文学观念则是把文学当作艺术。”如果说,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更多地影响了林语堂“闲适”话语的艺术追求,那么,西方文化带给林语堂的却是“闲适”话语的核心内容——自由的精神。“闲适”话语追求的自由表达和林语堂终生坚持不变的自由主义立场,其中都有自由主义和表现主义对林语堂的影响。西方文化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兴起的一支强心剂,也是林语堂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西方文化精神促使林语堂产生了建立“闲适”话语、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而“闲适”话语使人在精神上超越苦难的现实人生,解脱世事烦恼,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的精神目标,这也正是西方宗教文化终极关怀的一种演化。
3.论争中的“闲适”
自然,这样的“闲适”卷入了论争,一场与左翼文坛的论争。
提倡“闲适”话语的一方,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集结在《骆驼草》、《论语》、《文艺茶话》、《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逸经》等刊物周围,人称论语派。而论争的另一方则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他们团结在《巴尔底山》、《涛声》、《太白》、《新语林》、《蟋火》、《芒种》、《杂文(质文)》等杂志周围,以“匕首、投枪”式的、生存的小品文为号召,反对“幽默”、“闲适”小品文,人称太白派。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提倡“闲适”的就是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公开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对明末公安派性灵文学的继承,而袁氏三兄弟的创作即为后者代表。从周作人开始,我们所熟悉的以对悠闲生活的渴望和对知识及文化的即兴化表述为风格标记的“闲适”散文就在整个新文学话语中居于重要位置。而在20世纪30年代对周说提出最有力支持的是林语堂。他说:“周作人先生提倡公安,吾从而和之,盖此种文字,不仅有现存风格足为模范,且能标举性灵,甚有实质,不如白话文学招牌之空泛。”由于林语堂的极力推崇,论语派刊物上又掀起了一股“袁中郎热”。“闲适”话语的首次正式亮相也是在1934年林语堂的《人世间》发刊词中,他指出小品文创作应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继而又在《论小品文的笔调》、《关于〈人间世〉》等文中多次阐释其内涵,认为小品文笔调就是“闲适笔调”、“个人笔调”、“闲谈体”、“娓语体”。
1934年4月,林语堂在其创办的《人间世》创刊号上的显著位置发表周作人《五秩自寿诗》两首,以此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人世与道家的出世之间的矛盾。诗中的“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成了论语派作家生活的理想,也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理想,从而抛出了论语派主张“闲适”小品文的主张。
林语堂小品文理论中的核心命题就是“文学是自我表现”,“文学是为人生的”。他说:文学只要是“抒写性灵”、“表现自我”,能够对人们的“人生有启迪”的意义,那么任何题材都可以成为文学表现的内容,即所谓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可谈猫鼠、鬼神、睡眠、饮食,也可畅泄哀情,摹绘人情,形容世故,札记琐屑,谈天说地;可描写席上文士、舞女、酒菜味道的闲适,也可描写“人生月不常圆,花不常开,好友不常逢”之类的感叹。同时,林语堂还主张小品文应该采用“娓语笔调”,使小品文读来有“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的理想效果。所谓“娓语笔调”,即“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但确有此种笔调,正实比正名要紧”。这种笔调就是指以一种轻松闲适、清新自然的文体来立志立言。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无所不谈;第二,亦庄亦谐;第三,轻松自然。因此他特别反对“板面孔”式的训话式笔调,认为小品文就是要“如至友对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且其来得轻松自然,发自天籁”。
以周、林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文学主张,受到以鲁迅为主的“左翼”阵营的反对与批评,而批评的焦点就是周、林等人对生活、文学所提倡的一种“闲适”态度。他们以《太白》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闲适小品的批判。鲁迅发表了《小品文的危机》、《论语一年》、《从讽刺到幽默》、《帮闲法发隐》、《小品文的生机》、《杂谈小品文》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评。1934年茅盾发表了《关于小品文》,1935年《太白》杂志发表了周木斋的《小品文杂说》、聂绪弩的《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洪为法的《我对于小品文的偏见》、徐懋庸的《金圣叹的极微论》和《大处人手》等文,都对论语派的闲适小品文创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左翼”作家们认为论语派的闲适文学脱离了社会的斗争,其实质是“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
林语堂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闲适”的重要性。在《论小品文的笔调》中,他认为小品文的笔调也就是“闲适笔调”,又说“谈话与小品文最雷同之点是在其格调之闲适,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示出来”,而且“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这是很明显的;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这也是一样明显的”。对林氏的闲适产生文学的论调,鲁迅大不赞同,他反驳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种不满,在林语堂向鲁迅邀约打油诗时,被毫不留情地展现出来。鲁迅回信说:“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
与此同时,施蛰存、康嗣群编辑发行了《文饭小品》。在《创刊释名》中,康嗣群解释:
这一二年来,小品文似乎在文坛上抬了头。因为抬了头,于是招了许多诽谤。有的说小品文是清谈,而清谈是足以亡国的。有的说小品文是小摆设,而小摆设是玩物丧志的东西。有的说小品文不是伟大的作品,而我们这个时代却需要伟大的作品。这种种的诽谤,其实都不是小品文本身招来的。而是“小品”这个名字招来的,倘若当初不把这种文字称为“小品”,而称之为散文或随笔,我想一定不至于受到这许多似是而非的攻击的。因为品不品倒没有关系,人们要的是“伟大”,当伟大狂盛之年,而有人来抬出“小品文”这个名称,又从而提倡之,这当然幽默得要使一些伟大的人物感到不自然了。
康嗣群对此的态度是:“小品也许是清谈,但不负亡国之责;也许是摆设,但你如果因此表态,与我无涉。”编者的态度决定了刊物的倾向,《文饭小品》虽然仅出了6期,但它不仅刊载了大量趣味闲适的小品,还积极参与了当时关于小品文的论争。在文学审美观上,属支持周、林的一方。
周作人晚年谈及当年倡导闲适一路散文的时候说:“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夹注: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
在“小品文”最兴盛又最受非议的30年代,“两条路”是不同的文学理想与人生观的标识。在“大品文”和“小品文”的争论中,在上海创刊的《论语》宣布:“在目下这一种时代,似乎春秋比论语更需要,它或许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之狂澜,跻国家于太平。不过我们这班人自知没有这一种的大力量,其实只好出出《论语》”。论语派作家首先为小品文正名,认为在正统文学观念中它无法占据一席之地是文学的功利心使然。
“说自己的话”是“言志”的前提,小品文既然以表现个人情思为己任,言志主体便决定了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问题;认定小品文的面目是智者、凡人、庸人的“人情物理”而非道德化、功利性的国家民族类的宏大叙事,便在理论上与鲁迅式杂文那种战士的品格区别开来,认定自己不过是过渡时代的人,也便有意疏离英雄姿态。从英雄和布道者的形象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和庸人,从救济苍生的精英心态回归于生活中的常人心态,与人生哲学调整有关的转换获得了现代社会俗世化进程的支撑。近代市民社会的壮大、传统士大夫阶层日益平民化、道德力的控制弱化、现世享乐主义的涌动,都支持着英雄心态的消解。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所说的“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并非卤莽之辞,英雄时代的大一统局面分崩瓦解后迎来了“旧常的散文世界”。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中,以广大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为对象的文艺发展倾向日益明确,闲适格调的散文以其近情、自然、讲求趣味吻合了现代人的心态与要求。于是,耳目之内、日用起居等个人的日常经验和情感被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人们承认个人琐碎的欲望、内心的细枝末节作为散文内容的合法地位,散文题材内容上的变化可说是与以人为本、以细节真实为底、以日常生活风俗为对象的现实主义潮流合拍的。
周作人为散文主体形象设计的是凡人、庸人形象,所谓凡人与庸人形象实际上是清平的明智者,这种智者非先知或圣人,也非唯科学或唯方法理论是尊的所谓通人,只是明白常理,通达人情,叙事抒情不悖于现代文明思想。与语丝时期拐弯抹角的攻击或连篇的反话相反,他用“庸人的闲谈”替代了及时的时事反应:“我们固然也要听野老的话桑麻,市侩的说行市,然而友朋间气味相投的闲话,上自生死,下至虫鱼神鬼,无可不谈……”闲话的主体一则要与高高在上和自以为是“给人家去戴红黑帽喝道”的权威霸道面目告别;二则保持自己独立思考的头脑,不作狂信之徒。撤离战壕,走下讲坛,成为田间树下或书斋里的智者,成为读者的友人而非导师,首先要摆脱焦躁心态,抵达恬淡之境。闲适正是摒除了狂热与偏执的清明理性的人生姿态,蜕去个人身上一圈英雄的救世主的神光。
卸下载道面具的小品文向闲适的个人笔调定位,为散文自身的发展机制所决定,近情亲切的文笔迎合了现代报纸杂志发展的需要。现代小品文提供的是“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的智者与友人的形象,与文章家韩愈式高头讲章的浩然之气、道学先生的冬烘气、秀才文士的酸腐气自然不同。当散文体式因为作家人生理想与美学理想的不同追求而有了多元发展的契机时,闲适小品文平淡自然近情的特点,既与左翼杂文对垒又与之互补。双方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文学传统中汲取了各自的语言资源依靠。周作人、林语堂将幽默闲适的宗祖从晚明公安派上溯至苏轼、陶渊明、庄周,寻找一条性灵文学的流脉,同样,鲁迅式杂文对社会人生的强烈关注意识,那种种超出“旧常”与“平淡”的风骨文字,则暗中接继了司马迁“不平则鸣”的反抗精神,鲁迅对魏晋文章中师心使气文字的偏爱,更欲在从魏晋六朝到晚明的小品中找寻出一条讽刺、攻击与破坏的路来,都将某种与闲适小品文雅致风格无缘的阳刚之气呈现出来,那种深刻的社会关怀,却同样建立在叛逆个性与自我表现之基础上。
而作为一个作家,林语堂当属自由主义之类。从创办《论语》开始,他始终打出不涉及党派政治的中间旗号。他所谓的不涉及并非不关心,不评论,而是“不拿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林语堂不是政治家,他对时局的批评,不过是从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正如简又文对他的评价:“语堂是一个真正的、忠实的,和热烈的爱国者。不过他不是一个政客,不是一个党员,也没有担任过政治工作……所以他爱国的立场并非某某党的,其爱国的方式也不是某某党的。语堂之爱国,是站在一介平民的立场,而施用一介书生,或一个学者的方式。”唯其如此,对于文学创作,林语堂首先遵循的是自己的文学理念。他认为文学最重要的是“真”,“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而艺术只要是真的,即使不呐喊,也是为人生。所以题材上,他无所谓“宇宙之大”还是“苍蝇之微”,关键是要抒自我之真情。虽然提倡闲适、自由的写作,但林语堂并不反对文学表现政治,“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国绝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他反对的只是以道学的面孔,借着文学的外衣来表现政治。他认为这种文学是“为饭碗”的假艺术。
对林语堂从《论语》到《人间世》、《宇宙风》主编风格的转变,研究者们历来众说纷纭。
林语堂自己的解释是:
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为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作家了。也许如某人曾说,人生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则将要闷死。这不过是人类心理学中一种寻常的现象罢:即是在十分危险中,我们树立自卫的机械作用,也就是滑口擅辩。这一路的滑口擅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自辩固然难以令人完全置信,但联系林语堂的行为,我们应该肯定他的表白是真诚的,他将自己的转变归属于一种自卫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林氏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任何一个时代,先驱先贤毕竟都是少数,更多人首先要满足的是生存需要。论语派杂志既避过政治锋芒,苟全性命于乱世,又能保留一点自己说话的园地,发发牢骚和闷气,无怪乎在当时闲适得以风行,杂志得以畅销了。
林语堂这类自由主义作家的双重心态,既想保性命之全,又不甘心对社会时事完全装聋作哑。他们品评时弊的热情和勇气与当局统治者的政治高压刚好成反比,统治者越趋专横,他们的勇气就越趋细微,渐至隐匿。但无论怎样隐匿,这种关心时事的特性在他们身上从未彻底消失过,这也是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区别于附庸文人的标志之一。
代表左翼文坛与林语堂论争的主要是鲁迅。无可否认,这场论争对林语堂来说多少是有些委屈。他在文中多次如是表白:“论语》提倡幽默,也不过提倡幽默而已,于众文学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谣,不脱期,为愿已足,最多希望于一大国中各种说官话之报外有一说实话之报而已,与救国何关?”的确,从最初在闲聊中决定办《论语》开始,林语堂的努力都只是围绕着自己的刊物,贯彻自身的文学宗旨,而幽默闲适作为文学风格之一种,无论由谁来提倡都属正常的文学建设,本不该受讨伐,但林语堂提倡的结果是:“个人笔调也错,小品文也错,幽默也错,谈古书也错,甚至谈人生也错,虽然个人笔调,小品文,幽默,古书,大家都在跟我错里错。”这怎么能让他不觉得委屈呢?全面地分析这场论争,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个人意气之见。林语堂赌气说过:“吾喜袁中郎,****不许我喜袁中郎,虽然未读袁中郎。因此下誓,****好卢拿卡斯基,吾亦不许****喜卢拿卡斯基,虽然吾亦未读卢拿卡斯基。”鲁迅规劝林语堂时,也不无误会之言,但鲁迅对林语堂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的闲适观,说明它在当时的危害性,而不是对林语堂本人的攻击,更不是对林语堂进行历史的评价。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有权利保持自己谈论政治的自由,但言论一旦作为文字公开发表,也必然要面临公众话语的指评,对林语堂个人来,提倡幽默、性灵、闲适固然是他“个性的自由”,但是对于文字的公共性而言,却不得不纳入社会空间进行认证。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机以及种种的独裁非正义都是整个时代不容回避的主题,一切“艺术本身”的问题同时也不得不呈现为“政治”的含义,在这个前提下,“闲适家”的个人趣味就不得不接受更广大的政治文化的拷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