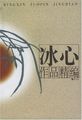远在他乡,思念的信鸽每每衔着记忆的花穗,飞回遥远的故土。那山,那水,那勤劳善良的家乡父老……不过,我思念得最多的却是家乡的谷子,那黄灿灿的谷米———小米,和那很会做小米稀饭的何二婶。
谷子是一种耐旱耐寒,生命力很强的作物。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谷子,幼苗时期常常是北方的干旱季节。这时禾苗只有一根头丝那样粗细的根,深深地扎入土里,吮吸大地那少得可怜的水分维持着生命。农民把这条根叫做谷子的“命根”。即使是这条命根已近枯萎,只要还和大地连在一起,谷苗就能顽强地活下来。一旦天降好雨,“命根”周围三两天之内便很快生长出许多条又粗又壮的根来———农民把这样的根叫“霸王根”———白刷刷地钻进土里。再过不了几天,奄奄一息的禾苗便会拔地而起,一片郁郁葱葱。
谷子把它的一身都无私地奉献给人类。谷草、谷糠,是上好的饲草、饲料,即使是烧成灰也能肥田壮地。至于谷米———人们称做小米,那价值可就大了,虽然不能像大米白面那样在宴会餐桌上讨得人们的青睐,但在农家的饭桌上却备受喜爱:一盘热腾腾的油馍,一碟香喷喷的肉炒山芋丝,几碗黄澄澄的小米稀饭,一家老少围坐一圈,农家之乐全在其中了。
小米稀饭,城里人管它叫小米粥,乡下人管它叫小米子米汤。提起小米子米汤,自然就想到了何二婶。何二婶一辈子没有生儿育女,可她却是我们村里人人尊敬的老娘婆———现今入时的称呼叫接生员。她一生说不清接生了多少婴儿,我便是她双手捧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何二婶还有一样绝活,就是做小米子米汤———这是乡下坐月子女人离不开的饭食。何二婶熬的小米子米汤不稀不稠,又精又香。别的年轻媳妇问她做小米子米汤的奥妙,她总是笑眯眯地说:“紧火米汤慢火肉,火烧紧点就行了。”她们便照着去做,虽然也不错,但终不及何二婶做的好吃。
要评说何二婶的功劳,当然要数对革命的贡献了。在战争年代,何二婶家是个老“堡垒户”。红军伤员在她家养伤,游击队员在她家打尖,何二婶总是像接待亲人一样,把家中最好的吃食———一碗碗小米子米汤端到战士们的手中。家乡流传着这样的信天游———
滚滚的(那个)米汤热腾腾的馍,
招待咱们的游击队(那个)好吃喝。
据村上的老年人说,这首信天游就是出自何二婶之口。何二婶还为战士做军鞋、补衣裳……有一次,三边游击队的一位小战士伤口化脓,在何二婶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何二婶自家吃苦苦菜、榆树叶,省下小米给小战士吃。她每天给小战士洗伤口、换药……小战士激动地说:“何二嫂(那时的何二嫂还是个年轻媳妇),你真是我们战士的亲人。”何二婶不高兴地说:“本来就是亲人,不是真的还能是啥?再不许说这样的见外话!”
人们常说中国的红色江山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此话一点也不假。陕甘宁边区像何二婶这样的老百姓千千万万呵,不正是他们支援着革命,才开创出了今天的新世界。
最感人的是何二婶在成绩面前像谷子一样谦虚。你看那金秋十月,一块块成熟的庄稼等待人们去收割:高粱把穗头高高地举起,玉米骄傲地昂首挺胸,糜穗像无数面小旗在微风中摇曳……唯有谷子把沉甸甸的穗头勾了下来,深深埋藏在谷叶中。农民们说:“好糜不见叶,好谷不见穗。”越是穗大粒满的谷子,越是看不到它们的穗头。革命胜利后,不少过去常在何二婶家中落脚的同志成了县里、省里的领导干部。同志们没有忘记何二婶,说她对革命有功,张罗着要在县上给她安排一份工作。可何二婶却笑着说:“你们把头提在手里打敌人、干革命,我干了个啥?再说,闹革命不就是图过个安生日子。如今革命成功了,家中分到了土地牲畜,就能一心一意种庄稼了。我若不在家种地,你们以后下乡来,咋能喝上我的小米子米汤?”
前几天,弟弟来信说:“自从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家乡年年都有好收成。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家家有余粮。尤其是谷子又丰收了,仅何二婶家的谷子就打了四五百斤。”家乡的人们富裕了,可家家还是每年都不忘要种一小块谷子,谁也没有忘掉要喝小米子米汤。
再过两个月就到春节了。今年的春节我要回家乡去过,去给何二婶拜年,再喝一次何二婶亲手做的小米子米汤。
作者简介 张树彬,男,汉族,1948年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宁夏盐池县人,中学高级教师,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诗歌学会会员,宁夏吴忠市作家协会理事。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及教学论文等多篇。与张树林合作撰著长篇传记文学《马鸿逵传》、长篇纪实文学《西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