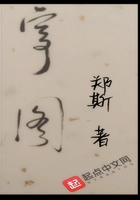巴黎左岸远眺提起“左岸”,可能就会提到这样一些气氛或背景:诗歌、哲学、贵族化、咖啡馆、艺术、清谈……当然,还有文化。
左岸:
巴黎人将塞纳河以北称为右岸,有许多的高级百货商店、精品店及饭店;而塞纳河以南称为左岸,这里有许多的学院及文化教育机构,在这里以年轻人居多,消费也较便宜。在法国,左岸则是一个特别“小资”的词。法国人一般爱把河岸分左右称呼,就像中国人爱把山坡分阴阳一样。而“巴黎的左岸”,则是一个让人容易浮想联翩、觉得是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广义上说,“巴黎左岸”指的是流经巴黎、把“艺术之都”一分为二的塞纳河以南的这部分;狭义上说,就是指靠近赛纳河南岸圣·米歇尔大街和圣·日耳曼大街交汇的方圆几公里的地方。
塞纳河由东向西呈“几”字形穿越巴黎,而巴黎城则是从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发展起来的。从公元14世纪起,西岱岛上的居民逐渐向河的两岸扩展。而自法王查理五世将王宫迁往右岸的浮日广场和卢浮宫等处后,巴黎的政治权力中心开始渐渐移向了右岸,商业经济随即也在右岸蓬勃发展了起来。左岸除了一些零星的居民外,主要建了三所大学:索邦大学(后更名为巴黎大学文学院)、三语大学(后更名为法兰西大学)、四国学院(后更名为法兰西学院)。由于当时学院的师生要求必须学会拉丁语,并用拉丁语写作、交谈,所以这一个区域也称“拉丁区”,这是左岸最早的区,也是一个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区域。
到了17世纪,路易十四迁居凡尔赛宫,左岸便成了从巴黎去凡尔赛宫的必经之路,这时的左岸进入了飞快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达官新贵、社会名流纷纷来此建造公馆,这样左岸便慢慢形成了一个以文化知识界为主流的中产阶级社区,与巴黎右岸由王宫府邸、商业大街组成的权力和经济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怪乎人们诙谐地称“右岸用钱,左岸用脑”。由于文化知识界聚集在左岸,于是各种书店、出版社、小剧场、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逐渐建立了起来。此后,围绕这种社交氛围的咖啡馆、啤酒馆也应运而生,这些都成了左岸知识文化人士重要的聚会场所。从紧靠赛纳河左岸的圣米歇尔大街开始,文化名人和先贤们光顾和聚会过的咖啡馆、酒吧就遍布于各个街区。
著名的花神咖啡馆三百多年来,左岸的咖啡不但加了糖,加了奶,而且还加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精华,加了一份像热咖啡一样温暖的文化情怀。“左岸”因此而成为一笔文化遗产、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一个时髦的代名词。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一不留神,你也许就会坐在海明威曾坐过的椅子上、萨特曾写作过的灯下、毕加索曾发过呆的窗口旁。在最古老的圣日耳曼教堂周围,有最早的“弗洛咖啡馆”(也称“花神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和边上的德玛格餐厅曾是著名的哲学家萨特和他的情人波伏娃几乎天天消磨时光的地方。现在咖啡馆的菜单上还印着萨特的语录:“自由之神经由花神之路……”。而附近的“里普啤酒馆”曾是安德烈·幻德与其《法兰西》杂志社撰稿作家们定期见面并探讨写作心得的地方,也曾是圣·罗兰经常涉足的地方。
在离大教堂不远处的蒙巴纳斯大街上,著名的“丁香咖啡馆”则又是一个重要的聚会中心。俄裔法国作家夏加尔、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美籍俄国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美国作家海明威、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等人在成名前都曾在这个所谓的“文学咖啡馆”里活动过。这群文学艺术家们围绕在号称“诗人王子”的保罗·福尔四周,每周二晚都在这里聚会。海明威就是在这里构思了《太阳照样升起》,至今,“丁香咖啡馆”还保存着一张“海明威之椅”,并保留着一道名为“海明威胡椒牛排”的招牌菜。
离此不远,是“双偶咖啡馆”。“双偶”,原是一场深受观众喜爱的滑稽戏,咖啡馆也因此取名“双偶咖啡馆”。萨特和波伏娃曾经常光顾这里,毕加索曾在此与朵拉·琦尔小姐一见钟情,莎士比亚书屋的女老板西尔薇亚·毕奇曾在这里认识了乔伊斯,经过她的竭力推荐,《尤利西斯》才得以面世。另外,附近还有“塞雷克特”、“劳特尔多”及“多姆”等咖啡馆。列宁在其流亡生涯中,就曾经常在“多姆咖啡馆”那有着明亮玻璃天花板下的座位上与托洛茨基构思和争论着俄国的革命。
奥赛美术馆宏大的内部展厅被称为“塞纳河边两大明珠瑰宝”之一的奥塞美术馆就坐落在左岸。馆内珍藏着19~20世纪著名画家莫奈、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一大批艺术珍品。此外,法国著名大画家德拉克罗瓦的画室和寓所也坐落在左岸,著名雕塑家布什尔在左岸落户,罗丹也将他毕业的作品,包括“思想者”、“地狱之门”、“加莱市民”等放在左岸的“罗丹美术馆”。而他所作的“穿睡衣的巴尔扎克”塑像就树立在“多姆咖啡馆”边。此外,这里还有雨果、乔治桑等名人塑像及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原塑像。
在左岸,还有着著名的先贤祠,这里安葬着对法国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们,包括卢梭、雨果、佐拉、伏尔泰、若海斯和居里夫妇等人。同时在左岸的蒙巴纳斯公墓,还安葬着萨特、莫泊桑、罗德、波特雷尔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很巧的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自成立起也落户于左岸。
先贤祠:
先贤祠,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它原是路易十五时期建成的圣·热内维耶瓦教堂,1791年改为埋葬“伟人”的墓地。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居里夫妇和大仲马等。至今,共有72位对法兰西做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其中仅有11位政治家。
德拉克罗瓦:
油画《自由引导人民》的作者。巴黎先贤祠如今,在右岸香榭丽舍大街及其周围街区高度繁华的今天,人们往往会在这光怪陆离之中似乎感到失去了什么。于是乎,人们就在塞纳河的左岸,在那文化与知识的先贤们曾经光顾的街道、公园、咖啡馆、美术馆以及旧居里寻找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一种充满着人文主义的东西,一种从历史遗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穿戴着右岸的名牌,品尝着左岸的咖啡”,人们会从这“品尝”中找回真正的精神慰藉。
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
让-保尔·萨特巴黎的蒙巴纳斯公墓的右侧有一座平凡的白色石墓。墓碑上没有装饰,没有雕刻,没有花圈,没有花坛,平凡得不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仅仅只有男女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可两个墓主人的名字会吓你一跳: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尔·萨特和《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是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他们又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各自著作等身,事业多姿多彩,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特立独行又成为永恒的经典。
西蒙娜·德·波伏娃他们俩以什么身份合葬?他们又不是夫妻。虽然他们相知相爱50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结婚。他们是情人?但“情人”经常是贬义词,而他们的爱情却很神圣,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
萨特年幼丧父、母亲改嫁,是个孤苦伶仃的少年,而西蒙娜则是在父母的宠爱中生长的规矩少女。两人在高等师范学校相遇,相见恨晚,两情相悦,从内心深处达成理解与默契。萨特提出:他们相爱,是真正的爱,但不要一夫一妻的模式,各人有自己的天地,有自己的交往。这就是说,男女相爱,但实行性开放,保留各自的性自由。这种观点颇合西蒙娜的心意,她接受他的原则。他们终身相爱,却并不从一而终。在以后的漫长人生中,萨特追求过很多女性,而西蒙娜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情外恋”。可这一切,正如他们相爱之初的约定一样,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爱情。
萨特去美国访问期间,结识并爱上了多情的多洛丽丝,以后他经常寻找机会去美国走一下;同样,西蒙娜去美国访问期间,也爱上了英俊的翻译阿格林,回国后她给阿格林写的情书,热烈得让人傻眼。但是当多洛丽丝要和萨特厮守一生时;当阿格林要和西蒙娜永不分开时,两人都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萨特和西蒙娜的爱情,精神的交流和交锋大于肉体的交融和交合。在这对哲人的感情生活里,有些事情对常人是不易理解的。1956年,萨特认识了19岁的女学生阿莱特,这个阿尔及利亚姑娘不久便成为萨特的情人。1965年,萨特把阿莱特收养为女儿,养父比养女大32岁。
萨特与波伏娃在一起萨特和西蒙娜可以双双出国访问,双双接受媒体采访,俨然是一对夫妻,但各人有家,有住房,各人著述,相互指正,相互切磋。在萨特逝世前,西蒙娜所有的书出版前都是经过萨特通读全稿的。他们是思想交融的情侣,不是举案齐眉的夫妻。婚姻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词汇。思想的结合,精神的交融,尊重彼此的人格主体,尊重彼此的人身独立,这才铸成了他们高于婚姻的爱情。
萨特病重期间,西蒙娜的一位女友向她提出问题,如何理解她与萨特的爱情以及《第二性》里的一句话:“一对幸福的男女是在爱情中认识自己,置天地和时间于不顾,他们自我满足,他们实现绝对。”波伏娃的回答是:“《第二性》的引文,并不直接波及萨特和我的问题。我从我们的爱情里获得了启发,而源自幸福爱情的绝对感,幸好是普天下都能实现的事情。两个深深相爱的人热爱生活,是无需任何别的理由的。纵然岁月流逝,真正的爱情始终能保持,会赋予生活全部的意义,全部存在的理由。”
1986年,波伏娃度过自己的78岁生日。她患了和萨特同样的疾病,因肺部炎症而导致肺水肿。波伏娃于4月14日去世,而萨特的忌日是4月15日。波伏娃提前一天走,也许反映了她迫不及待的心情,急着想和萨特会合。最后,人们打开萨特的墓穴,把她的遗体放在萨特的身旁,这一对没有结婚的终身情侣,死后才永远相守,永不分开。波伏娃对萨特而言,没有任何名分,但萨特身边惟一的位置,是属于她的,非她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