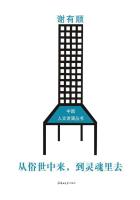上星期,乘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春风,单位组织我们去作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传统教育之旅。在延安,我们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在壶口瀑布,我们受到了民族传统教育;在山西洪洞,我们受到了历史传统教育。在短短的三天之内走访这样三个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大有深意的地方,自然只能说是走马观花,但是仅就一路上的见闻,也就感触颇多。黄色,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色。五千年文明史上,无论多么生动的场景图画,无不是在这个黄色的底色上展开的。从巴颜喀拉山北麓发源的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孕育了一个黄皮肤的人种,这个民族的祖先叫黄帝,就连奉天承运的大皇帝身上穿的,也是绣龙的黄袍!相信所有稍具历史常识的中国人内心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黄色情结,潜意识里都有那么一点对于黄色的敏感。但是这次传统教育之旅带给我的黄色冲击,却不仅仅来源于思想深处,它是更直接、更强烈的一种视觉冲击!回来已经多天,脑子里还是那一片让人晕眩的黄色,深浅不一、新旧不一、形式不一、性质不一的黄色啊!
黄土
旅游车出晋入陕,我首先看到了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说起来,山西地理部分也属黄土高原,但是到了晋中,已是高原和盆地、山地、丘陵的交界处了……所以,看到这满目黄土,我还是震惊了。除了土还是土,除了黄还是黄,简直让人觉得象被活埋了那样的感觉,喘不过气来……大自然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色彩的,是单色的,完全象一张年代久远的老照片。它辽阔,也狭隘;它雄浑,也单调;它冷漠,也深情……人们活着,住在黄色的窑洞里,耕作在黄色的大地上,死了,埋在深深的黄土里,变作黄色的腐殖质。谁也打不破这个黄,谁也改不了这个黄,谁也逃不脱这个黄!奇怪的是,这丰厚的黄土并不丰饶,这片大地之所以让人觉得窒息,不仅仅是因为它色彩上的单调,更多的是因为它缺乏活力,缺乏生命的征象。车行一天,几乎没有看到林网和绿色植被。路边的黄土落满了灰尘,已显出历史的陈旧,而山腰上被取过土的地方,露出的新鲜黄土黄得耀眼,煞象大地上一道疼痛的伤口。车窗外偶然晃过一两棵树,都光秃秃的似乎还睡在冬天的沉思里。弯曲丑陋的树干不着一叶,黑色歪扭的树枝象过了火似的痛苦的挣扎着直指无语的苍天……心,也象是在跟它一起挣扎。下雨吧!下雨吧!下雨吧!一路上我都读着它的语言,听着它痛苦的呼唤。
车过绥德,想起那句脍炙人口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不由得向车窗外细细打量起所有可见的男人来——让人失望的是,没有看到一个帅哥俊男。秦地的男子,都带着兵马俑的那种体貌特征,给人朴实、坚韧、愚笨的感觉。米脂的婆姨没见过,也许风流如常,而绥德的汉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全失英爽俊朗的风采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黄河
我还不止一次地看到了黄河,这条史上曾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河流。它是那样的平静,安祥,既没有倾注的气势,也没有喧嚣的波浪,春天的阳光下,它以一种比大地更为深沉的黄色静静地流淌着,细碎的波纹闪着鳞鳞黄光。人们说黄河是一石水,六斗泥,确乎不假,而泥土,也只有当它以这种形式存在和运动的时候,才能折射出阳光吧。第一眼看到这个样子的黄河,内心象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胸膛里涌起一股又辣又酸的味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吗?它为什么这么苍老?这么荒凉?这么孤独?这么贫穷?它背负了这个沉重的民族几千年,它有点筋疲力尽了……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它。它久久的在我们的车窗外,惊澜不起,默默伴随,有时,车随路转,我们离它而去,高原崎岖,在颠簸中昏昏欲睡的当儿它又悄悄的在车窗外出现了……“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上,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扳……”哦,母亲,这悲凉高亢的信天游是前人传下来的,那个时候的你,负得起儿女的舢板和巨轮,而现在,你的河道上,真的还能行船吗?都说母亲的力量源于爱,都说女性的力量在心里,你的力量,你的生气,在哪呢……一路上,我都在怀疑的自问。直到我看到了壶口。是的,这个答案在壶口,壶口,让我知道了什么是黄河!
黄瀑
在离壶口几里路的地方,我们已望见了白色的水雾,听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那隐隐的雷声。车行渐近,雷声也渐盈耳,终于变成了雷霆震怒!静女似的黄河,慈祥温柔的母亲,流到壶口这里,三百米之宽的河道骤缩为五十米之窄,又恰逢五十多米高的一个悬崖,于是滔滔泥流就在这里集束飞下,在石质的壶底摔得粉碎,溅起万丈白雾,发出雷霆万钧的吼声,之后,飞沫偕浪,击岸悬流,顺着刀削斧劈般狭窄的千米“龙槽”腾身东去。这就是黄河!这就是震怒的母亲瞬间爆发出的惊人的生命能量!我们走近壶口的时候正值清晨,旭日方升,大河上下,山为云遮,水为天盖,壶口上游水天一色,波平如镜,壶口下游黄浪奔腾,声若雷鸣。瀑激壶底冲击而起的水雾,在阳光中幻化出一道连天接地的巨虹,引发出游人阵阵的惊呼。离瀑布尚有二十米远,水雾已如细珠碎玉般迎面溅来,及走近,人人皆已头面尽湿,衣衫淋漓。站在瀑边遥想当年“亚洲第一飞人”柯受良和吉县农民朱朝晖驾车从兹飞越的情景,不由令人心摇胆颤,神为之夺。
离开壶口,我们又去了洪洞。有道是“要问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在这里免不了又是一番寻根问祖。游客甚多,好奇心大致雷同,象那种号称是国家姓氏研究所专制的姓氏起源考录一百元一份,真伪虽难辩,生意却很是红火,倒是洪武年间移民注册的所在,那棵让祖祖辈辈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大槐树前驻足者廖廖。如今的它已化作了安静的化石,它是那样的特别,石质的硬陋之中夹杂着丝丝木质的雅丽。它的子孙,从它的根部衍生出的二代槐也已死去,三代槐却依然风中卓立。看那枝条,婆裟中已露出几分柔软,几丝妩媚,想必不久即可鹅黄浅绿,一派春光了。槐树是一种高龄树种,人的寿命自然不能与它相比,但是生命的传递与繁衍却遵循着同一个不变的真理。作为树来说,树种不亡,此树永存,就人而言,后人点燃香火,则祖宗在天之灵可慰。站在这块尊贵的化石前,站在袅袅青烟中,我想这是每一个前来寻根的中国人都应该反思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