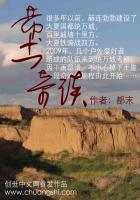嘎吧勒一时急道:“别说了,啥子勒,快快把你们的病人抬过来吧,我的兄弟保证救活他们性命的。”
中年汉子一时也顾不得自家心里的疑虑和困惑,狠下心趁机走前几步大叫着:“啥子勒,回来,都抬回来,咱们的人有救啦。”
这一下,刚才那一帮迎面而去的臣民听见自己的同伴一时大叫,略微停顿了一会,便慌忙抬着人往回走。一下子,一帮臣民三步并作两步就把人抬回到了嘎吧勒等人的面前了。
此时,无痕斜眼瞧了一下还在说话的嘎吧勒,便不推辞也搭话立即从马车上跳下来,奔到担架上躺着病人的面前,仔仔细细遂一检查病情,慢慢对照病理。然后蹲在一个肚子肿胀得特别厉害的病人面前,挽上长垂的手袖,从自己手腕里绑着布袋的小兜子里倏然拨出了一支5寸来长的银针,用火炀过消毒之后,对着那个病人肚脐上的三大穴位猛然扎了下去,然后在勃子之上的气涌穴又是一针,再翻转那病人的背后用力一拍,只听得“啊”然一声大叫,一股酸臭的黑水就从那病人的嘴里狂吐而出,顿时臭气熏天。
旁边围观的众人见此污秽发呕状,无不掩鼻而退,缓缓向后。无痕一时也是手忙脚乱,顾不得许多猛拉袖子掩鼻遮口而作,却叫不上一个帮手,任由担架上的病人一时狂泻猛呕。
扎木哈终于靠了过来,一边按住那狂呕的病人,一边憔虑地望向无痕,好像心里怀着十二分的愧疚一样,狠狠责怪自己没有及时过来帮上无痕的匆忙。
那作呕的病人终于停止了下来,扎木哈把病人挪过一边,然后喂上几口干净的水,就见那病人缓缓的开始活动了,精神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不断增加。
嘎吧勒即时在无痕的面前双手抱拳作揖,一副钦佩得不得了的样子,眼睛专注地望着无痕,似乎在说;兄弟,一切都靠你了。见识过眼前的这一幕,那一众臣民便把无痕围了个同心圆,眼里流露出十二分的敬仰。
无痕没有理会嘎吧勒这一套,略微回头看了一眼,叫过几个有力的护卫,走到其他的病人面前,从又依样画葫芦一般从新操作了刚才救人的针法和动作一遍。末了,自顾自地走到车架前净了净手和身上的污气,整理过衣服,再轻喷嗽过口,就靠着马车缓缓闭目休息了。
在场的所有人员都不敢去打扰已闭目闲暇的无痕,毕竟大家已见识过无痕的治病救人手法,想必也有理由相信目前的病人是确保无虞的。何况眼前治病救人的人真的是显得一脸倦容,疲惫之极。
大约半个时辰过去之后,无痕突然从倚着的车架站起走到嘎吧勒的跟前急切地说道:“二尊架,扎木哈,就刚才患病的臣民来看必是得了瘟疫之后的后遗症。这病说恶不恶,说难不难,只是像得了腹泻之症一样让人软绵无力,无期无尽。当然了,它没有瘟疫一样可以传染和交替感染的可能,只是某些除不尽的病菌在个人的体内作恶罢了,不必大惊小怪的。”
“哦,既然如此,无痕兄弟可有治病良方啊?”嘎邑勒一时显得无计可施地望向无痕的眼睛缓缓地说道。
“二尊架,法子倒是有的,但是还是要用到药草的,就不知尊架的意思如何了?”无痕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对着嘎吧勒说道。
“哎哟,我说无痕兄弟,你有什么法子就直截了当的大声说出来不就得了,还在这里兜什么圈子啊,咱们又不是外人,你怕什么呢?别忘记了要打要杀的话还有我扎木哈在啊。”扎木哈一时耐不住急性子直言说道。
“扎老三,就你能,什么事都急得像个泼猴似的,你以为治病救人就是简单的打打杀杀能解决得了的吗?你也不用脑子想想。就不能改改你的老毛病,学学人家无痕兄弟的沉稳和镇定吗?老是让人家看笑话似的。” 嘎吧勒转过头直眼盯上了扎木哈,没好气的说道:
“我说嘎老二,你也好不到那里去。我这是为民抢命急的,你那是故作清高装的。你以为你就这么能能糊弄我呀,我呸,呸,呸。。。。。。”扎木哈不服气地急速反驳道。
“二位尊架都别吵了,咱们这是商良办法,不是舞刀开枪上大架的,你俩就不能好好坐下来仔细研导一翻。”无痕有些气愤的说道。
嘎吧勒和扎木哈被无痕这样一道抢白,顿时脸红脖子胀的停顿了下来,双双抱拳向无痕礼拜道:“请无痕兄弟不啬赐教,只要是救民于水火,咱俩一定鼎力成全。”
“好啦,二位尊架也不用拉这么大的架势,咱们这就开药方去,时不我待了。”无痕说道。
忽然顿了一顿,接着又说道“方才我在车架小憩的当儿,就一直在思考除病去垢的问题。想来想去咱们狼烟驱瘟疫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可能是咱们没有做到弃恶除尽造成的吧。现在需要补救的良方就上来一道“七茶汤”,根据这“七茶汤”的药理和应对的病情,对眼下这后遗之症肯定是百好良药,药到病除了,就只等二位尊架发号施令啦。”
嘎吧勒一时听罢无痕公子的诉说,顿时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默默从怀里再次掏出血色的图腾交与身旁的扎木哈,挥了挥手沉声道:“去吧,都交与你了,好生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