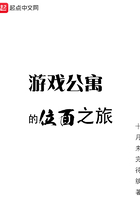“不……”
惨呼声中,石方猛然坐了起来。额上的冷汗如落雨般的直滚落下来,划过了眼眉,粘上了睫毛,主人却连动一下的意思也没有。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石方两眼泛出复杂至极的神色来。
已经好多天了,自打那天下了焚尸的命令,石方每晚都会被噩梦惊醒。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一具具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尸骸,时不时地,耳边还会响起那名可怜的妇人撕心裂肺般的嚎叫声。了无生息的小襁褓,与妇人那呆滞僵直的脸庞,交织着不停在石方脑海里闪现,最后凝聚成一束锋利的刀芒,狠狠地戳进石方的心窝。
石方早就知道祝家庄覆灭的事情,可在他的脑子里,这也仅仅就是一个消息,一个早已注定的结局。石方曾庆幸过自己好不容易摆脱了这样的宿命,却根本没想到,亲眼看见了,会产生那么大的冲击。
我错了吗?
同样的问题,石方已经自问了无数遍。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石方想过;在庄众伤亡惨重的时候,石方想过;在扈家庄的墓群前,石方想过;在下挥刀屠俘命令的时候,石方也想过。如今,目睹了祝家庄惨状的石方,更是每每的会在心里发出这样的疑问,只是,始终也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我错了吗?
石方再一次的问着自己。就在此时,玉兰披着外套,从外面推门进来了。
“哥哥又做噩梦了吗?”玉兰的脸上,一派藏不住的关心神色。确实,石方连日来一直被心结困扰,整个人憔悴了许多。
“噢,我没事,你自己安歇吧,别管我了。”石方低声的说着,神情像是好了一点。
“唉……”玉兰轻叹一声,也没别的办法,推门出去了。
屋里又恢复了一片宁静,可石方却一点的睡意也找不到了。翻来覆去的好半天,老石还是没办法宁心静气,干脆一骨碌爬了起来。随意的往肩上搭了一件外套,石方小心翼翼的推开了房门。也许,到外面透透气,是个不错的选择。
“庄主。”
也不知逛了多久,石方被一声呼唤惊醒了。定睛一看,自己竟然晃到关押俘虏的囚室来了。
“他们这几天有什么异常吗?”既然来了,石方也就顺便问了一句。
“回庄主,几日来,他们倒是安生了许多,也不像以前那样闹腾了,就是晚上睡得不怎么踏实,时不时地有人大呼小叫的。”
石方觉得奇怪,怎么跟自己的反应一样?
“全都这样?”石方不由得追问了一句。
“差不多吧,也就那个书生和寥寥几个人没什么反应。”看守挠了挠头皮,接着又指了指囚室:“这不,今天刚闹完,所有人都被闹醒了,估计这会儿还没睡呢。”
“打开囚室,我要进去看看。”石方还真就被勾起好奇心来了。
长长的过道,把屋里的空间分割成了两大块,石方让人在过道中间置了一把椅子,就此安坐了下来。这以前是座空置的库房,修得还算结实,窗户没开几扇,因而有些沉闷,不过,略微改建了一下,用来关人,倒也算得物尽其用。
石方横眼打量了一下两边的囚室,每边都另隔成了五六间小号,里面关押的诸人三三两两数目不等。不过有一点还是能看出来的,透过昏暗的火光,几乎所有人都偷偷的往自己这边瞅。
“已经好些天了,直到今天,我一闭上眼睛,祝家庄那幕惨绝人寰的画面仍不停的在我眼前闪现。说实话,对你们梁山的这些好汉,原本我还是有些敬重之心的,可亲眼目睹了你们做下的好事,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默坐了半晌,石方幽幽的开了口。与其说是说给囚犯们听的,不如说是有些自言自语的意味。不管怎么说,石方的话匣子一开,也就真的有点压抑不住了。
“江湖上都在传言,梁山好汉们如何如何的了得,更树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隐为领袖一方的龙头。我信了,真的信了,不怕笑话,我还曾经想过好好的与你们结交一番。身为江湖男儿,立马扬鞭、快意恩仇,自古就是我辈向往、追逐的目标。可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所有的景仰,都在霎那间破灭了。还真应了那句老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还不如不见!”
石方真的有点沮丧,幻想瞬间的破灭,没经历过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到那种巨大的失落感的。
“梁山的名头,响了也没几年,按说你等也都是从普通世民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可我真没想到,面对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你们手里的屠刀竟然挥得没有半点犹豫。那可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性命啊!你们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怎的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落草,可落了草以后,就能狠下心来去迫别的百姓了?你们被别人逼迫,所以你们也逼迫别人,这就是你们落草的意义?”
说着说着,石方的眼前又晃现出了那幕景象,不由得声音就是一滞。随着石方的停顿,屋里一下子没了声息,就连站在门口警戒的庄丁,也都闻言思量起来。没片刻的功夫,石方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对你们不太了解,也就前几天才知道,解氏兄弟小时候有过那么一档子悲惨身世。那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是天生的贼种?别人我不知道,吴军师你以前好像是教书先生吧,莫非你教人子弟的,都是些杀人掠财,放火屠庄之类的勾当?”
不知什么时候,囚室里响起了轻轻的呜咽声,随即,扩展成了一片。
“庄主所言,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庄主像是忘记我等的身份了。我等自打落草的那天起,再也不是普通的百姓了,贼寇这个名头,今生今日是再也抹不去了。什么是寇?什么是匪?有不杀人的寇匪吗?我们不杀人就可以摘了寇匪的名衔吗?”
石方冷眼一瞅,却是吴用坐在墙角发的声音。
“噢?那你们所树的替天行道的大旗又怎么解释呢?你们口口声声、一日不忘的义气二字又如何解释呢?”
也就在辩得吴用出不了声的当口,石方脑子里电光火石般的一闪,总算想到了问题的结症。这帮所谓的好汉豪杰们,不管以前是什么出生,自落草的那天起,就不自觉地为自己打上了寇匪的烙印。与其说杀戮、劫掠是他们的生存手段,还不如说是他们下意识的认可了这种血腥手段,觉得这样更符合自己寇匪的身份。这都******什么逻辑啊,石方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的推断,可又隐隐的觉得,自己的推断似乎也真的能成立。
“你们真是枉被称作一方的豪杰,江湖人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鬼使神差般,石方冲口诉叱起来。
“庄主休要欺人太甚,我等即落入你的手里,杀剐存留自由你摆布。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你这般言语相辱,我欧鹏却是不服!”
“不服?好,我就教教你们什么是服。”老石说着,又把头别向了吴用。
“寇匪应该用什么手段,我先不和你辩,先说说你们梁山的具体情况好了。就像前面我所说的,山上有不少人是被迫落草的,江湖有传闻,百姓也不会一点不知道,这说明什么?只要情况属实,百姓心里还是比较同情你们的。你们不事生产,四处劫掠,就像你们说的,这是寇匪的本分。先不说对不对,只要不太过分,大部分百姓还是宁愿花小钱买平安的。可你们呢?动不动就来个屠庄灭村,鸡犬不留,你说百姓的心还会站在你们这边吗?”
“你们不生产,还可以劫掠,百姓该怎么办呢?一次两次,问题不大,老是没完没了地给你们上贡,估计谁都不会乐意。早晚会和你们对上,就像我们扈家庄一样。打得过,自然就不必上贡,打不过,他们也可以逃。没人愿意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赚的钱财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们拿走。你不是要粮食吗?老子不种了,反正种了也吃不着;你不是要财物吗?老子不走你这条道成不成?大不了远一点,与其被你们劫掠了钱财去,绕道绝对划算许多。”
“再说说你们梁山的位置,好地方啊!八百里水泊,天然的屏障!你们能时不时地出来活动一番,官兵要想攻进去还真不怎么容易。所以呢?官兵不在的时候,你们就是老大,想打谁打谁,想灭谁灭谁。官兵一来,马上往窝里一退,还能逍遥自在的过日子。这是什么?典型的欺软怕硬!我也不来说这种行为丢不丢脸了,再问问你们,就算你们靠着水泊逍遥了一辈子,你们的儿孙后代呢?打算也让他们干你们的老本行?子子孙孙就那么干下去?永生永世的背个寇匪世家的名头?”
“实话对你们说,老子这次人手不足,犹能把你们打得灰头土脸的,要是老子手里人手充足呢?要是你们梁山周围的村寨听闻你们的血腥手段,感到害怕而联合起来了呢?别说打,硬圈就把你们圈死了。即便圈不死你们,官兵来的时候,打打下手,带个小路什么的,也能让你们忙活得找不到北。要粮没粮,要钱没钱,你们又能逍遥得了几时?”
“再说了,就你们那种欺软怕硬的作风,不是丢尽了我们江湖人的脸吗?顶着一方豪杰的名头,尽干些欺压百姓的勾当,我都替你们感到脸红。如今朝廷积弱,边关不靖,有本事带弟兄去那打出些名堂来,好歹也算为咱大宋挣个脸面,就算死了,也不枉在世上走了一遭!被人提及,也都是大拇哥一挑,赞一声:是个带种的!你们现在呢?别人会怎么瞧你们?别人不说,问老子的话,就一句:一帮贼寇!”
“庄主说得好轻巧,我等深受官府迫害,凭什么我等还要帮他们去打江山?”欧鹏听了老半天,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话头。
“蠢蛋!还真是个死脑筋。老子说过帮他赵宋皇帝打江山了吗?自己打下的江山,自己不会坐吗?”石方没好气地骂了一声。
这半天滔滔不绝的数落下来,石方心里轻松多了,一长身站了起来,再不看众人一眼,洒然去了。
屋里,火把仍旧噼啪的跳着火头,昏黄的光影下,留下了一屋或坐或站的人影……
(拉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