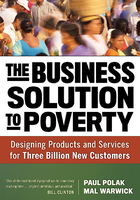大雪如同鹅毛般的纷飞乱舞,灯笼里的光线印在她黑色的面纱上,五官的影子却是黯然深沉的,她压低了声线的反问他:“今日长公主生辰,李封大人不在公主府祝寿,这么晚要赶去哪里?”
他去那里-----长公主在如此日子里,放着府内一众王孙贵胄不管,却跑去了梁上居,这种事他如何能知而不报。
李封问她:“你既然知道我是谁!那你为何要这么做,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她手中的灯笼缓缓放到脚边,一笑:“李大人,长公主在这样的日子里独自前往梁上居这件事对你就这么重要吗?重要的你冒着这么大的风雪都要去向皇上举报!”
“梁上居自建造之初就目的非常,一个好好的乐舞坊为何能笼络帝都人心。”
她叹息:“原来李大人是这样想的,怪不得颜枕戈会容不下你了。”
李封心中一滞,却像是想明白什么一样:“你-----果真是他派来的,看来我猜的没错,他开创梁上居接近帝都权臣贵胄,是有目的。”
她唇间一抹冷笑:“对于你,我早就想杀了,你时不时的在梁上居走来走去的,晃得我眼花惹得我心烦。”
李封眯眼看着她,这声音明明是个小姑娘的语气,可话语却比风雪还冷:“你到底是谁!”
俗话说,既然要让别人死,那就一定得让他死的明白一些,她唇角勾起笑意的缓缓取下自己的面纱,而面前的人顿时惊愕的看着她的面容,从一开始的浩然荡气变得慌乱不堪,他震惊的指着她:“你---是-----繆大将军之女,繆臻。”
她清美的面容淡笑了一下:“是的李大人,秋末的时候我与您还在书院里对过诗,你还夸过我呢!”
他瞳孔放大,很不敢相信的问:“你---为什么?”
她将手里带血的匕首收回,从容淡定的说:“或许是我该问李大人,帝都的乐舞坊这么多,你为何偏偏盯着梁上居不放。”
“若非他目的不明,我何至于每日盯着他。”
“目的不纯,李大人是说他与死去的季相爷有关系吗?”
“季忠------你到底知道什么----你----”还未等他说话,她便伸手将他压制在桥边,脚踩在他的胸口上让他半个身体都悬在了河面上,此时风雪吹拂,她衣袂飘诀轻声而笑:“我知道什么?那我就告诉李大人吧!五年前其实是你们一步步设计害死的季相爷的吧!什么诬告平冤这些戏码,你们利用谭松诬告,让皇帝诛了季相府一族。”
李封顿时惊呼:“你竟然知道这些。”他瞳孔放大,激动的大喊:“你不是繆臻,你和相府那些人都是六王余孽,是乱党”
她轻声冷笑:“我们确实与六王有关,不过,我们不是余孽,是侥幸在当年活下来的人。”
李封大骇:“原来你们这些年都潜伏在帝都谋划逆反之事,你们这些乱党。”
李封的话一说完,她便收起面上的笑意,眼中冷冽的伸手在他脖子上用力捏紧,语气狠烈:“当年皇帝为了登基残杀六王,还装作仁义圣贤的模样,季相爷当年就是知道了这个真相才被你们所杀,所以到底谁才是乱党!”
李封挣扎着怒言:“若不是皇上,哪里能有如今的太平盛世。”
繆臻听了,目光甚寒的握了握拳头,一字一句的告诉他:“一个没有真相的太平盛世吗?既然你到现在还不明是非,那就只能送你去问问阎王,为一己之私杀尽父兄的人面兽心,有什么资格论功绩。”
“你------------”
她伸手摸到他胸口上的鼓起处,快速的从他怀中拿出一封信来,繆臻寒笑了一下,手指快速点尽他的大穴,再反身一脚将他踢入冰冷的河中,她速度极快,在李封还未来得及说一句遗言的时候,他已然在河中动弹不得的淹没。
看着河中的人影一点点的沉下去,站在桥上的人一身黑衣在夜风大雪中飞舞凌乱,她冷笑:“余孽乱党?-----你敢在我面前说这些就注定必死无疑。”
她看着如此完美简单的完成了事情,唇角勾起笑意的转身离开,能够在两种身份下活得游刃有余的人从来就不是个善人,而她,也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好人。
十五年前---------------------
晋国昌惠元月初三。
这是历史里昌惠年间所记载的最后一日:这一日,大雪纷飞,寒冷彻骨-----
帝都血染风雨满城,若是要形容一下当时的惨况,那只能是血流成河,哀嚎不绝。
相比如今高坐王位的皇帝,当年那一场阴谋他可谓是成绩斐然,在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惨无人寰的时候,竟然还能受人爱戴。
真是可笑,可笑之极!
----------------------------
就当公主府派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出去找寻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四处寻找的长公主此刻正静静的坐在梁上居里,压根儿就没有回去的打算。
梁上居的琴坊里,长公主正独自端庄的坐在雕花桃木桌前而她的目光,始终只看着前方纱幔围绕的琴阁里,对面琴架上的正端坐在古木琴边,手指抚在琴弦之上,修长的指尖正在熟练的勾出每一个悠扬的琴调,这人,正是梁上居的主人---颜枕戈。
长公主沉浸在声乐之中,而颜枕戈在那明亮的烛光里,一身暗红长袍,长若云丝的黑发松松的挽在身后,如美玉雕刻的面容在烛光中明透清晰,他的眼眸随着自己的指尖而转,似潋滟波光,唇角微微扬起的淡笑却有着撩人风情般的魅惑。
一曲音止,他缓缓收手,看向对面还沉浸乐声中的人,轻笑的唤她:“长公主殿下。”
司马成婉一时回过神来,看着他问:“你方才所弹是什么曲子,我怎么从未听过。”
颜枕戈挑眉而笑:“是繆大小姐前日给的贺寿词,我让纪叔将它编成曲子,以恭贺长公主生辰笑乐,芳龄永继。”
长公主听后,美眸微转,眉间更添了几分温情,对他笑道:“臻丫头写的贺寿词吗?”
“繆小姐文采敏捷,知道长公主近日肯定要来,所以特意写的。”
长公主不可置否的噙笑:“那贺寿词我可以看看吗?”
颜枕戈点头,便朝着右侧喊了声:“七洺,将东西拿过来。”
他的话音落后,内阁里有人应了声,很快就有一个面目容秀的少年上来,从怀里拿出贺寿词放在桌前后行礼磕头:“七洺参见长公主,这是繆小姐的贺寿词。”
长公主缓缓将寿词放入衣袖问道:“现在什么时辰了。”
庄七洺在一旁忙回答:“回长公主,此时已快亥时了
司马成婉听后,眼中泛起幽幽黯然:“我该回去了。”
颜枕戈站起,身姿恭敬的行了一个礼,再抬起头来时,那张灼灼其华如秋水轻娆的面容保持着笑意,眼中又全是关切之意的说:“公主殿下,屋外寒冷,让婢女们小心伺候些,勿着了凉。”
梁上居送走了长公主,七洺便连忙吩咐关上了大门,而此刻重新回到琴阁里坐下的颜枕戈有些疲惫的用手指揉了揉自己的额角。
庄七洺走过去问:“主子要休息了吗?”
“休息什么,不是还早吗?”颜枕戈又抬头问:“锦绣还没回来吗?”
庄七洺看了看开着的窗户外的大雪飘摇,摇头:“-----还没。”
还未回来------颜枕戈沉著了一会抬头问:“我煮的姜汤呢?”
庄七洺回答:“因为今晚太冷了,现在还在厨房里温着呢。”
面前坐着的人有些叹息的站起身来,手指拢进袖中朝着自己主室走去,边走边说:“今晚风雪是大了些,不过风雪再大,也冷却不了整个帝都的炙热啊。”
庄七洺跟在身后,试探性的问:“我可以去接应一下小绣儿吗?”
颜枕戈听后不由一笑,他继续走着:“要是去接应的话她指不定会生气的,刀光血影的事她可比你见的多了,等会记得端姜汤来就好。”
七洺依旧担心:“----可是绣儿---。”
颜枕戈见他如此模样,便问他:“究竟她是你主子还是我是?”
七洺看着颜枕戈的目光越来越犀利时,连忙说:“你是我们两个的主子,我们都只会听你的。”
“这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