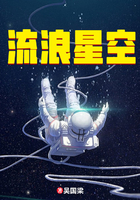一个人为了感情,可以不顾旧人死活,凶猛到何种程度,有时甚至令局外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存受了威胁。
爱意之浓,凶猛与固执之深,手段之酷烈与卑鄙,所有曾经或者正在偷情的人一定与我有同样深刻的体验。《失乐园》弥漫着末日行将来到的气氛,黑木瞳与役所广司让观者不寒而栗。
偷情的人是婚姻制度的恐怖分子,是日常生活的定时炸弹。在等奖学金的日子里,我百无聊赖,内心空前极端,头脑空前清醒与灵活,多愁善感,见到一切都会勾起愁思。落泪,满口谎言,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平衡内心的极端,我外表上比不偷情阶段更笑容可掬,更友善,更彬彬有礼,除了背叛了的那个人。
我每天给H写信,这个行动已经成了晚期癌症,继续膨胀是它惟一的去向。我还发明了一个更可怕的行动,每天夜里给H打国际长途电话。我们住在留学生公寓,两对夫妻共享一个大客厅、一个设施齐全的厨房、一个洗手间,还有各自的卧室。每天深夜两点多,北京时间下午两点多,偷情女主角出场了。我眼神贼亮,蹑手蹑脚地把电话线拖出卧室,拖到过道中间。两个卧室门是并排的。美国的房门都是木头做的,很不隔音。隔壁一对毕业于国内两所菜鸟学校,来到美国已经三年多,处处如鱼得水,知道到哪里看便宜的最新电影,到哪个Mall的哪个角落挑拣便宜货,充分享受无理由退货的好处。他们买了变质的牛肉,切到一半发现那些肉不对劲,捧着一大堆碎肉,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小时去退货。
我把耳朵凑近那扇木门,死一般的沉寂。这一对都是高头大马,男的四肢修长,脸很瘦,肚腩微微突出,这是汉堡王、麦当劳和每天开车害的。女的接近一米七,红彤彤的大圆脸蛋,刚刚买了一双BCBG的平底凉鞋,白色,两头翘,走起来像开着两条小白船。她爱不释手,回家脱下鞋后把两条小白船放在一个高高的地方。
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李静。李静是个F2,这是美国移民局给陪读签证的代号。不少F2不久就转成了F1,这是学生签证的代号。李静当F2已经当了9年。她在苏北老家没有读完初中,15岁开始工作,在榨菜厂切榨菜。18岁上李静来到常州做保姆,那家人家认她做干女儿,找关系让她到一家医院开救护车。20岁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许业。许业中专毕业,1988年经人担保来美国留学。李静下班后继续开车接送医院里的病人,赚了外快换成4000美元给许业寄去。
1992年,李静带着2岁的儿子飞来美国。两个星期后,许业开车把她送到一家餐馆门口,李静开始洗盘子。她一句英语不会说,只能洗盘子,洗盘子不用说话。洗盘子每个月几百美元,做waiter或者waitress可赚到两三千美元。再过了两个星期,李静开始试做waitress。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女子,没说过一句英语,为了赚钱给丈夫读书,克服了任何顾虑,直接为客人们服务。开始很难,凭着她的刻苦、谦卑和好学,李静很快学会了餐厅的所有常用语。做Waitress收入很高,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到几千美金,哪怕丈夫一分钱奖学金拿不到,仅凭李静在餐厅的打工收入,一家人在美国也能很好地生活了。
李静长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大圆苹果脸。“有一个老美,经常来吃饭,给小费给得特别多。有时什么都不吃,就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悄悄地走掉,桌上留下小费。有一天,他又来了,手里拿着一束玫瑰花。我告诉他我已经有家庭了,对不起,先生。他很难过,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李静告诉我,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现在想想,那时候真傻啊,一心为着家庭。”
许业博士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有外遇,那是1995年的事情。对方是个女F1,已经有了丈夫。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州立大学的留学生们几乎都知道这件事。李静受到严重的伤害,“我把一生的眼泪都哭干了。”许业对李静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生的最爱。”李静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要死要活追她的男人。当年李静是个漂亮姑娘,有一份收入很好的工作,养父母很疼爱她,她不时往苏北老家寄笔钱,有时利用长假期回去探望亲生父母。有个在常州当兵的军人很喜欢她,希望跟她结婚。李静觉得,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希望找个读书人。养父不喜欢许业,说:“你跟他没有什么好处的。”许业追到李静工作的医院,在那里等她。他对李静说:“你是我世上第一个谈得来的人。”许业出国留学后,写信给李静说:“我背着个米袋子四处漂泊,等米吃完的那一天,我也就完蛋了。”许业开始时没有奖学金,他边学习边进餐馆打工,每天只睡3个小时。李静心疼丈夫,把攒下的钱全部给许业汇去,自己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穿。
许业博士毕业来到实验室做博士后,一家三口迁来长岛。“长岛物价好贵呀。”李静对我说,“在田纳西,500美金就可以租到上下两层楼的house了,这里800美金才租一个卧室带一个客厅的公寓。”实验室空着一幢大房子,窗户外边是海,实验室主任、德高望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住在隔壁。实验室允许许业搬进去住一阵子,但他必须立刻找房子,找到就得搬出来,毕竟这幢房子太豪华了,位置太好了,他住在这里不太合适。
李静打开房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这个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年的女子,仍然穿着一件棉毛衫和一件老式的裤子,棉毛衫上印着“常州国棉一厂”。李静有点显老,有点胖。他们有一个11岁的儿子,像只大熊猫,胖得动作迟缓,憨态可掬。和我熟悉了之后,李静告诉我,许业首先来到长岛,她和儿子留在田纳西,又呆了两个星期,等儿子学期结束。李静和儿子来到长岛后,在卫生间里发现了女人留下的一根头绳。许业叫她分担一半的房租,回到家,热菜热饭要立刻端上桌子。打了这么多年的工后,来到长岛,她想休息一阵子。她一直为自己没有上完学感到遗憾,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读一个护士资格证书。取得护士资格证书后,她可以在医院里当护士,取得正式的身份。护士的薪水远远低于她在餐馆里打工的收入,但护士是正式工作,在餐馆打工是“黑工”,从法律上说,一旦发现,应该立刻被遣返的。不打工李静立刻失去了任何收入。不仅分担一半房租,每周进城一次,到法拉盛买菜,轮流付款。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稍有不如意之处,立刻破口大骂。“‘我对你一点胃口都没有。’许业经常这样侮辱我。”李静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他们在婚姻里安安稳稳地呆着,他们真有勇气。
我如今在一家杂志做小编辑,上班时间我坐在一台丑陋的显示器前,敲打出我的一日三餐、房租、水电、衣服。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将来不再有偷情行为。
对与H偷情惟一可以告慰的是,我痛痛快快地离了婚,微总算逃脱了我的魔掌。离开美国后,我打过两次越洋长途电话给李静,她打过一次我的手机。她说,你还是到美国来吧,你在国内肯定不容易,看你寄过来的照片,你明显地老了。
她问我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我犹豫了一下说没有。其实我是有的,我们住在一起,以体温和血液互相温暖,相互知根知底,窝里斗的时候刀刀见血。
我们以嫖客和婊子互相称呼。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对李静撒了个弥天大谎,我有了男朋友还不敢向她承认。偷情者就是偷情者,难道我还想保持形象?我还有形象要保持吗?在心底里,我依然不敢正视我的偷情,我愧对列位偷情老手。我是个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