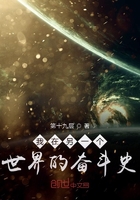待到十一月中旬,四处是雪花飘飘,一路上耽搁了不少时辰,好不容易,终于看见了京城的大门。虽短短几月但人早已归心似箭,看到京城那一刻是他几乎落下泪来。皇帝归宫后,自是有百般要事要处理,他守在殿外,看漫天飘扬的大雪,想不到才过几月,竟是如此地恋乡。“大人,皇上有事找您。”一名侍卫前来通报,“知道了。”他走进御书房,皇上正在批阅奏折,“臣参见皇上。”“起来。”“嗻。”“容若,”皇上拿着一本折子冲他晃了晃,“朕不在的这几月里,政务都是由那四个大臣代理,当然,那里也有你的阿玛,只不过朕没想到,如今这党争已变得如此激烈,你瞧瞧,朕才走几月,这互相弹劾的折子就堆了这么一摞,朕选那四个人不过是以他们平日里意见不同,期待他们遇事可以互补不足慎重考虑,现在好了,这些人一个个的变本加厉,只想着你争我斗没一个是为我大清为我大清百姓从心底效力的!”他待皇上怒气消了才道,“皇上息怒,毕竟事情还大有挽回的余地,臣有一个想法。”“讲。”“皇上显然已经分清了大臣们的党派,现在朝中索额图是一派,臣的阿玛是一派,还有些小派,剩下的就是墙头草了,索额图和臣的阿玛势力都不小,臣想,皇上可以这样,皇上先故意重视其中的一派,对另一方忽视,”“嗯?”“皇上重视其中的一方,最好是多采纳那一方的意见,再找些借口提拔那派的中心,让朝臣以为皇上明确了立场,久而久之,不受重视一派里必出墙头草,等到差不多了,皇上再将此举反过来做,这样一来,两派里都会产生不可信的人,势力自然就小了。”“所以你是说,要朕利用大臣之间的信任?”他微点了点头。皇上眉头一皱,“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啊。”“皇上,朝局本来就是这样,每个人之间都要留些空隙,这样他们才能以为,与其随和他人,倒不如将自己的意见直接呈给皇上,每个人的意见大多都不会相同,意见多了,才好辨明,才有最好的。”皇帝叹了口气,闭目想了一会儿,又睁开眼睛,“好吧,朕会考虑试试,不过容若,”忽然又转向他,“你是不是,至今心里还在埋怨当初朕没有给你一个前朝官职而是把你留在身边当了一个御前侍卫?”他猛地一抬头,随后神情恢复平淡,“臣怨过,不过臣懂皇上的用心。”“那就好。”皇帝微微一笑。
待他飞也似地奔回家时,未到家门口就看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外面飘着雪,她披着披风,盈盈地站在府门前。“淑月!”他翻身下马,卢氏亦按奈不住心中的激动迎了上去,又小跑了几步,吓得身后的丫头们差点尖叫起来。“莫跑!”他一把扶住妻子,两人的目光相对了,卢氏静静地望着他,目如秋水,终于忍不住,几滴泪滑过脸颊。“淑月,我回来了。”两人目目相对,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过了半晌,卢氏才缓缓道,“公子路上辛苦了,快进去吧。”夫妻二人团圆片刻,忽然听外面有人来访,他听说是顾梁汾,便立刻叫人带他去书房等候,看向卢氏,她微笑着点点头。
“容若。”“梁兄。”二人促膝交谈好久,塞上的事情也不太想说了,就故意聊聊闲话。“梁兄这几月可好?”“好。”梁汾笑道,“只是你不在京城,这但凡清闲的日子里,也就寂寞了许多。”他笑了笑,“梁兄乃风雅之人,怎会愁没有事情做?”“不错,虽常与些旧友题诗作画,每次都会想到,若是他在的话,定能压倒群才。”“他?梁兄说的可是吴先生么?”梁汾叹了口气,“如今已是寒冬,不知他在那边过得是如何,不知是否暖饱无忧,宁古塔非寻常之地,岂能不让人挂心?”他微皱了皱眉,半晌,缓缓道,“容若考虑过了,虽无太多把握,但容若愿帮兄台,去请求阿玛。”“此话当真?”“君子无戏言。”
晚膳时分,因他久出而归,父亲命大摆家宴,顾梁汾乃他好友,自然也受到了邀请。父亲坐在中央,母亲与卢氏坐在一处,他与好友坐在一处。宴过半晌,父亲斟了一杯酒,“顾先生乃我府上常客,又与犬子交好,今日家宴,应由老夫敬先生一杯,以表欢迎。”“不敢当。”顾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父亲已饮数杯,显然是有些醉意了,言行举止亦不似方才那般生硬拘束,有几处还与这边的谈话附和着,还笑出了声。他见时机差不多了,与顾使了个眼色。“阿玛,”他道,“顾先生一向擅长吟诗作赋,阿玛不如让先生作几句增添下气氛如何?”父亲眼睛一闪,“好,好啊,只是不知先生,是否愿意啊?”顾站起身,“在下愿意献丑,只是不知以何题材,今日大人难得一家团聚,实在令人高兴,只是在下,有一好友,多年在外不得与家人团聚,归返故乡,如今已二十有三年,在下对他,甚是怀念,方才见大人一家和睦,不免想到了他,不知可否做一首怀念旧友的诗词?”“好啊,先生博学多才,作什么都好。”他停了片刻,缓缓道,“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籍,母贫家老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博人应见惯,总输他,翻云覆雨手,冰郁雪,周旋久。”话语刚落,鸦雀无声,明珠显然是被震惊到了,静静地听着,只听他又道,“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知如今还有。只绝望,苦寒难受,廿载包骨承一诺,置此札,君怀袖。”明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擦去眼角的泪痕,过了半晌,饮下一杯酒。“不知先生所指的,是何许人也?”顾梁汾抬袖拱手道,“此乃在下数十年来的旧友,如今被流放在严寒之地的吴兆骞。”“吴……什么,吴兆骞?当年因科举作弊案被流放在宁古塔的罪人吴汉槎?”明珠一惊顿时将手中的酒杯打落在桌上。“正是!只不过在下想纠正的是,此人并非罪人,他是遭小人陷害的!如今,已被流放二十多年,作为亲友在下却欲助无力,欲与之宽慰却见面不得,而今在下有万幸能与大人的长公子结交,若大人有惜贤才之心,还望大人伸以援手相助!”明珠诧异地半张着嘴,未答话,只见顾梁汾已跪到了眼前。明珠叹了口气,“先生的心情老夫理解,只是若要翻此案恐怕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阿玛。”他也站了起来,“儿子相信,阿玛定有另外的解决办法。”“你说什么?”“儿子知道,以阿玛的权力,解救一个已被流放多年的前朝犯人不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你是要让你的阿玛去背这个黑锅么!”“阿玛!”他也几步上来跪到了父亲眼前,“吴先生乃贤才也,南闱科举案已事隔多年,没有人会想再翻起这些陈年旧事,若是如此被冤之人就要一生在那极苦之地饱受饥寒,含恨而终,儿子想不求翻案,只是使些门路将他解救出来即可,阿玛是朝中重臣,相比起朝中大事这不过是一件小事,儿子知道阿玛是有办法的,况阿玛素来欣赏贤才,若此人真有才学让他留在阿玛身边作作参考也好,阿玛,儿子求您了。”明珠脸上渐渐地流出一种高深莫测的神情,转动着手里的酒杯,静静沉思。良久,缓缓道,“好,此事老夫答应,只不过从今以后,”看向他,“阿玛对你的所有嘱咐你都要言听计从,你,能做到么?”他眉头微微一皱,半晌,“儿子答应阿玛。”“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