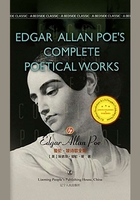我和三爷相知相交,是高中毕业回村以后。那时,我已没有更高的理想,只想做个优秀的庄稼人,干活很卖力气。三爷很赞赏,向公社推荐让我做大队主任,给他当副手。从此我们就常在一起开会、干活、喝酒,处理各种矛盾纠纷。那时的干部,很多精力都花在处理纠纷上,因为人和人的关系太紧张。三千多人的村子,十个生产队,按下葫芦瓢起来,天天都有纠纷,有时一天数起,我和三爷几乎是马不停蹄。老实说,三爷的好多做法都不上路子,但我又不能不佩服他周旋和化解事情的能力。三爷处理问题威风八面,但他有一条原则,就是不害人、和为贵。他像一位仁慈而又威严的帝王,保护着他的子孙和臣民。
一九七一年初,县里调我去通讯组搞新闻报道。开始我不愿去,我已醉心于乡村事业,想为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出一把力。那时的思想是非常单纯的,并没有多想今后的发展前途。一天晚上,三爷叫我去他家喝酒。桌上摆四样小菜,两双筷子,一壶酒。开始,他一直不说话,只和我喝闷酒。三壶酒喝光,三爷额上沁出汗来。他一直不看我,这时抬起头说:“你走吧。我本来想叫你接班的……还是走吧!在外头啥时都别忘了,咱是平民百姓出身。”后来,我到县里工作了。几年后三爷也退了下来。三爷是个强者,可在他任职期间,村子依然贫穷。有几年,他非常忧郁,常常自责。大伙都劝他,这不能全怪你,你已经尽了全力。是的,他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三爷是一代人的缩影。后来我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祖先的坟》,发表后居然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其间多是三爷同时代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他们说感谢我对那一代人的理解。我一直认为,对于前人,我们尽可以去总结他,但没理由轻薄他。我们也会成为祖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同样等待着后人的评判。
作品中的主人翁死了,真实的三爷依然活着。他知道我把他写进了小说,并且是死了。三爷毫不介意:“我死过一回,就不会再死了。”他时常在他的杂货店里向人说起我,说本夫在省里当材料员,我早看出他会写材料。年轻人纠正他说是作家,可他坚持说我是材料员。
三爷从土改当干部几十年,已不惯于蜗居家中。他在十字路口开一爿杂货店,一人独居。往来行人经过此处,总爱歇歇脚和他说几句话。他们知道这家杂货店的店主曾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三爷到底老了。刮风下雨的天气,杂货店就显得格外冷清,偶有行人也是脚步匆匆,顾不上看一眼他的杂货店。三爷走出柜台,蹒跚着倚住破门板,望着十字路口的斜雨,那时便显得茫然而呆滞。
算起来,三爷该七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