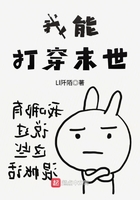“妈腿的,这又讨军饷啊?”孙二娘又厌腻又抵触的瞥视下木偶般的大兵,蚊子回头的叮下成士权,警告地说:“成士权,殷会长那事儿,那都是只听轱辘把响不知井在哪的空穴来风,你别跟着臭哄哄的牛屁后,掰膀的瞎嗡嗡起哄,臭屎坨上再穿稀啦?”
“孙二娘你也别这么说,无风、轻风、微风、小风、大风、狂风、飓风、黑旋风、龙卷风,白毛风,不管啥风,是你篙嘴吹出来的吗,那是得有风眼点才刮起来的?”小转轴子拿操袖抹下冻得红草莓的鼻子,抽抽着说:“殷大叔跟俺爹说起来是世交,俺当小辈儿的不该说,这沤屎坑里捅出这大马蜂窝,你不想说,那也蜇得你跟着哼哼呀?殷大叔一向板板的,坐怀不乱的样子,俺都不敢想他会那样龌龊?大德子那哥们,要真要是殷大叔私生子,那哪来的盛子倒插门呀,这不脱裤子放屁费那二遍事儿吗?”
“我说小转轴子你啊,比你爹还能转轴?”小抠儿跺跺的跺着冻木的两脚,仰眼的看着小转轴子,“你说的咋个意思呀,转来绕去的,你团溜面呢你?你是想烙饼还是要蒸饽饽呀?你就说‘殷大舅是亲爹’,还是殷大舅就是他舅,不就得了?我的脑子也冻萝卜开奓了,爹就爹,舅就舅,管咱屁事儿呀?啊,不对呀?你还是说,吉老三倒插门,吉老大就是个外甥,那还是啊,瞅这弯弯绕,绕的啊?孙二娘,这里头皮袄套棉袄还带坎肩儿,你听懂了没有啊?”
“哈哈……”小转轴子一后脖溜子撸掉小抠儿的破獭皮帽子,“你这臭小子,驴嘴里吐不出狗牙,你不咬人呐?”
“殷会长是个正直的商人,摊上这烂眼边儿的事儿,这得分风和雨来说?”穿蓝长棉袍,围围脖儿,当代教书先生穿戴的一个二十八九的人,侃侃地说:“这些年了,谁说过殷会长在男女之事上半句的不是了?那是孙二娘这样贞节烈女的偶像!那为啥?那是殷会长是个纯爷们,干净得洁身如玉。再说吉大少爷都娶妻生子了,又通过个个儿的奋斗,开了咱镇上狗撵鸭子顶呱呱的大商铺,引领着咱商界将来的走向,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国家昌盛的脊梁!这个时候,这贼喊捉贼的不居心叵测吗?那目的是什么,咱泱泱大国是个礼义之邦,武崇尚关羽忠义皆兄弟,文崇尚孔孟之道,尊奉孔子的伦理道德,民又多信奉佛、道、儒教,净化灵魂,讲究洁身自好,这魑(chí)魅魍(wǎng)魉(liǎng)的阴鬼小人,拿人们眼里最厌恶谁糟蹋伦理和佛的圣洁,来玷污殷会长的人格,污辱诽谤,用心何其毒也!这是龌龊小人,报君子磊落之仇。这就是说,殷会长走的正道,这是雨。反之呢,事情如童谣所说,人们混水摸鱼的相信了,那殷会长就会遭人们的唾弃,身败名裂!城中失火,殃及鱼池,咱的尊敬的可爱的吉大少爷吉大掌柜会咋样儿呢?脚臭,臭在鞋里。腋臭,臭在衣里。人臭,臭在名誉上。吉大少爷就会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这就是风。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把雨刮下来,那小人就是不拿枪不拿笔,杀人不用刀,刀不血刃,狡猾的用嘴臭,喷杀人也!嘴皮子是刀,舌头是利剑,人们就愿嚼那臭味臭旁人,个个儿嚼着香的臭豆腐。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不管童谣说的是真是假,沧桑流逝,历史烙痕,抚今追昔,也都是一曲带有奈人寻味动听的而又透着心酸苦涩眼泪的罗曼帝克。”
“啪啪”几人的鼓掌声,好灵和霭灵跟一些男女同学挤过来,“李老师,你讲课呢这是啊?”那个叫李老师的哈哈说,路见不平即席而感,“你信俺爹会有那事儿吗?烂嘴丫子!”李老师说:“好灵、蔼灵同学,对绯闻,就像身上的虱子抖是抖不净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昏者见昏,浊者见浊,往殷会长身上刷屎的人,见不了大天,也就是虱子打喷嚏不伤筋骨,你不要跟着凑热闹,别往心里去?那事儿准备的咋样儿啦?”好灵眼神往身后一甩,“关心国事的同学都来了!”
“殷会长出来了!”
“你看崔镇长和那李杜副官也出来了。”
“兵临城下,刀摁脖子,谁也没辙,任人宰割吧!”
“各位同仁,李杜将军非常偏爱咱富庶的黑龙镇啊,亲派特使督饷。”殷明喜板着冰块似的脸,一字一顿地说:“关里军事鏖(áo)战,缺兵少饷,大帅为天下黎民百姓虑,扩军购械,肯请咱商家慷慨解囊,违者军法论处。经多次和特使磋商,崔镇长的抬爱,咱商户各家共负饷捐十万大洋的一半,五万。俺知道咱各商家都不宽绰,这是扒皮抽筋,国事兵大,讳莫如深,本会长无奈又无助,只有遵嘱而行。德增盛大东家吉德没在家,俺装一回大屁眼子,带个头,殷氏皮货行和德增盛商号,共负一万块大洋,其余由各家商铺按纳税多少分摊。”
“‘殷大舅,是亲爹’,你不用装噔,啥做了作不了主的,哪有儿子不听老子的?”
“‘莲花庵,尼姑妈’,你不用装蒜,你往老姑子窟窿里捐了多少****钱,别大癞蛤蟆戴水獭帽,就呱呱装人了?”
“有没这事儿呀?”
“吉老大是你和老姑子生的吗?”
“千里嗅,你埋汰佛家弟子的圣洁,该遭天谴?”
“千里嗅,你还要脸不,缺大德了,姑子你也敢玩?”
“殷大舅,別不好意思,天大奇闻,堂堂的大会长,跟姑子玩邪门,说说呗!”
“谁造谣,有种站出来!”
人群中良莠不齐,瞪眼完一伙儿人混在人群中,不时向殷明喜发难,引来猎奇人们的一片骚动。
“这没啥,有谁没向莲花庵捐赠过呢?积德行善,也是积功德,俺年年捐!”二掌柜一早拿那匿名纸条找到殷明喜,也吓吓得他脑子一片空白,毛细孔都嘎嘎炸响,出了一头的冷汗。冷静下来和二掌柜一商量,从兰会长先前学的邓猴子亲口所说,一致认为是邓猴子瞄着点儿啥须子杵咕的。搅浑水的人,跑不了瞪眼完、麻坑一伙儿坏小子所为。这一明一暗,一口对百口,哪去找公堂对案分辩的地儿呀?无损大雅,只有缄口不语,不辩自明,静观其变,不攻自破!有个难点,也最缠手,文静扛得住,吉德、殷张氏和孩子们呢?二掌柜献一策,只有疏导,谣言而已!这工劲儿大庭广众之下有人发难,殷明喜缄口不语是不行了,只有高调又幽默地回应,“有谁对童谣感兴趣,请俺到你家热炕头上,炒两小菜,不用山珍海味,不挑?焯萝卜片蘸大酱、再来一碟炒盐豆,烫上一壶小酒,不用茅台,咱烧锅的老山炮就行,冲啊,解嘎儿,俺答疑解惑的慢慢拉!这觉得还不过瘾,那就请上文静师太,一边敲木鱼一边念逍遥经,悠哉妙哉不?俺是俗人,会会佛家弟子,也叫大伙儿开开眼,俺是咋幽会姑子的?”
殷明喜话落铮铮有声,幽默没有引来哄笑,而是有人感动得含着苦涩的泪。
“反对内战!”
“打倒军阀!”
“……”
好灵和蔼灵的学生们,适时手举五色小旗,高呼起了口号。
“同学们,静一静,打倒军阀俺也赞成!这倒省得俺这些商家再掏腰包了。省下来的钱,建学堂修街道,多做些善事多好呢?可俺得识时务啊,不拿捐,眼前这些军爷这身军服就得脱了,和咱老百姓一样了,那这块人杰地灵的地界又交给谁呢?世上有吃草的,就有吃肉的,弱肉强食啊同学们?俺是商会会长,首先俺也是个商人,俺非常体量大家伙的难处,俺和特使商量,军饷也是军需,实在拿不出大洋的,也可拿你铺子的货品,按市价顶大洋。”
“这入秋蘑菇採一茬咕咚又冒一茬的,我们这些开大街棚小吃铺儿的,糊口都没有糨子,拿啥顶啊?”
孙二娘质问又诉苦的带头吵吵,嗡嗡咉咉一片,引来很多人的附和。
“你不闲着一个老寡妇身子吗,捐给军爷,比啥不强,准叫你老贞节烈女沟满壕平,还糊啥糨子啊?”
“你松松口,你不用卖大灶,给俺开个小灶,你那份捐银,俺替你拿了!”
“谁?谁没长嘴,找抽啊?”孙二娘踮翘脚的在皮帽子上左右前后踅摸着,“你妈还闲着呢,捐给老跑腿子了都?”
“反对内战!”
“打倒军阀!”
“……”
马六子调来一队警察,没有放肆,只喝斥的阻止学生们的正义行为。
“各位老少爷们,同学们,当前,奉军正在换防,镇上兵力不足,大伙儿要做好防范,胡子随时都会来侵扰。”崔武一派官吏的样子,“这饷捐,各商家二十天內交齐。上头催的很紧,我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啊,拜托了!鸟无头不能飞,殷会长和吉大东家带了头,两个柜上也不是有钱花不了,饷捐拿了五分之一,面打箩里转,他两家多捐了,大伙儿就少捐了。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顾全大局的作法,值得赞赏!我不以一个镇长的名义,以一个外人,多说一句。对有人造谣,恶意中伤殷会长,我嗤之以鼻!大伙儿呢,这埋汰人的事儿,也别脏了个个儿的嘴?不传谣,不信谣,谣言还有市场了吗?咱不管造谣的人出于什么目的,人身攻击,都是不可取的。我个人捺摸,殷会长是光明磊落的。我们要相信殷会长,事情会水落石出的。”
殷明喜这时拉过二掌柜耳语几句,二掌柜消失在人群中。
“对孙二娘这样欠税的小吃铺、烤地瓜、蘸糖葫芦等微利商贩,这次免捐。”殷明喜明确表态又不失风趣一句,“谁想打孙二娘的主意,俺送大红包祝贺!”
“公正啊!”
“谁赶紧把孙二娘抱回家呀?”
孙二娘对殷明喜拿她开涮,又好气又好笑,红着脸骂骂的挤出唔嚎的起哄人群。
“谢谢父老乡亲了!”李杜将军特使先抱掌作揖,后高喊:“敬礼!”
牛二眼尖,在人群中发现了七巧猫,七巧猫也看见了牛二。牛二刚想凑过去,七巧猫向牛二招招手,就不见了。
牛二觉得诧异,就从散开的人群里,挤到刚送走崔武和李杜将军的特使,要回屋的殷明喜跟前,低语告诉殷明喜,“七巧猫来镇上了!”殷明喜听了,脸上浮上了一层疑云,“这是摁下葫芦要起瓢,黄鼠狼要拜年啊?”
“哎哎牛二!” 牛二听完殷明喜吩咐他不要声张,看殷明喜走进了商会会馆,听有人喊他,就见程小二在杂乱拥挤人群中推来搡去扒拉来扒拉去的,好不容易来到牛二跟前,“这咋二掌柜当了大掌柜,你当了二掌柜,还忙了起来了,这个不好找?”
“啊小二回来了!”牛二看着咧怀穿着羊皮大氅,一身雪末的程小二,“顺利吗道上?”
“牛掌柜,一言难尽!”程小二搂上牛二走着,“別说了,差点儿没回来,还怕见不着你们了呢?还算好,吃饭的家伙还长在脖子上,回来了。冬至他们等着你卸货呢,快看看去。你和冬至交割清了,咱好回家在炕头上好好烙烙,身板儿硬撅撅的,赶上棒起来的‘老二哥’了,这个累呀?”
两人连跑带颠的回到德增盛,来到后院,牛二一边跟冬至、二娃和小乐一帮小兄弟们拥来搡去打招呼嬉闹,一边叫伙计和学徒的卸货,该进库的进库上架,客商急等提货的,就当场批发点钱付货,一切井然有序。
“牛掌柜真成了行家里手,有大买卖家的样子了。”冬至看牛二娴熟地扒拉算盘算着账,夸赞地说:“咱这帮土豹子地里刨豆包的,也能当二掌柜了?”
“这得感谢咱德哥呀!没他,咱哥几个现在还猫冬呢,炕头爬炕梢,抓虱子挤虮子的呢?”牛二头不抬的拿石膏块儿往黑木板上记着账,“哎冬至,双棒呢?咋没见,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牛掌柜,忘告诉你啦,双棒儿出事儿了!”牛二停下手,疑虑而又焦急地瞅着神兮兮的小乐,“出啥事儿了?快说,咱尿都要急出来了?”
小乐看牛二越发急,越慢吞吞的吊牛二的胃口,有点儿火上房与己无关的样子,“牛掌柜,双棒儿在****山,掉进一个娘们的大坑里了?我们哥几个,就冬至,咋救也救不出来,看来只有你出面,非你不可了?”牛二急急的又犯疑地问:“又不老实,逛了?你们也是,不看着点儿,再不多给‘暗门子’俩钱儿不就结了?这撂在****山,****山?哪地界,我咋没印象呢?”
二娃从一辆大胶轮车上,往下搬卸一个个大麻包棉花,笑说:“哎小乐,別逗咱牛掌柜了?双棒儿啊,这回出门我们几个看得紧,没打着尖,想钻灶坑了,没找着灶坑门,这一道想春花想的,熬不住了,在路过咱圩子岔道时,就两人骑一匹马,回家找春花出火去了。这节骨眼儿,早趴在春花****山上快活呢,哈哈……”牛二没有笑,噘嘴地说:“你们这几个小光棍儿呀,开玩笑开大了?我好悬没把苦胆吓破了,咱们可再不能出啥事儿了,经不起了?你们出门这些日子,可出些了大事儿,一喜一赝。喜的是,老王八犊子邓猴子因杀人霸女带上大脚链子了!”
“啊,有这大好事儿,太叫人解嘎渣儿了?”
“这猴子一贯撅尾巴竿儿当庙旗,招摇撞骗,摁人头,老欺负不上香的。”
“……”
“邓猴子的二老婆叫彩秀的,听说跟了马六子;那个三老婆,叫凤儿,也听说在回李家圩子的半道上叫金螳螂劫上山,给穿山甲当了压寨夫人了;只有大老婆大傻还守着那个两个鳖甲儿子跟那个狗窝,造得家破人散,枭雄变狗熊,害人终以害己而终。可不知哪个王八犊子戳咕的,咱德哥和殷大舅这赝吃的餍哪?可叫你们想都想不到,太阴损了!这咱德哥到他老丈人家不啥事儿还没回来,回来后还不知咋样呢?”哥几个围过来,“牛二哥,家里出啥大事儿了,我们几个啥也不知道,你说,三个臭皮匠还赛不过一诸葛亮吗?”牛二皱眉沁头的难于启齿,“唉,是德哥的事儿,也是殷大舅的事儿。有人满大街满镇子的造谣,说德哥是殷大舅和莲花庵文静师太生的私生子,这不是糟烬人吗?”
“啊,有这事儿?”哥几个大惊失色,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说:“谁造的谣啊?”
“要知道谁造的谣就好了?”牛二看伙计们干活也低头耷拉耳的,愁苦地说:“嗨,现在谁哪有空追查这事儿呀,殷大舅叫二掌柜到姜家圩子去截德哥去了。想先透透风,怕德哥冷不丁听了,受不了?”
“这咱也不能干瞪眼瞅着不管啊?”冬至说:“我琢磨呀,邓猴子一向跟殷大舅势不两立的作对,谷友子连着谷子,咱德哥也是邓猴子眼中钉肉中刺,如今最恨德哥的只有邓猴子的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