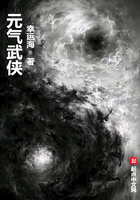可到了第五天的夜里,那人又不声不响的送了一个窝头过来。她声音低沉,仿佛害怕被人发现一般,将窝头颤抖着塞到她的手里,有些急切地说道:“公主,都到了这个地方,您侥幸不死,就是天意。想想皇后娘娘,她定然不愿看着您这般命丧于此的。求您听奴婢一句吧,多少吃些东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柔嘉听了来人这话,有些吃力的睁开眼。她已经连续多日不曾进过一滴水米了,只是仗着年轻还勉强有些生气而已。此时便是用力睁开眼,终究也看不清楚眼前的人是谁。
昏暗的夜色里,只瞧见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窸窸窣窣的,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诡异。
柔嘉问道:“你是谁?怎知我的身份?我……”
“公主,奴婢只是昔日秦宫一个卑贱的宫人罢了,便是说了名字,您也想不起来的。只要公主能受了奴婢这份心意,也就不枉奴婢这般担了风险为您送水送粮了……”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可是,可是……我真的不想活下去了。活着太难,太难太难……”柔嘉的声音干涩无力,既轻又飘,仿佛下一刻就要湮灭于自己的哽咽声中一般。
“公主,奴婢从前在宫中时也曾因为一时糊涂犯下了错,被罚了三十刑杖。当时挨打的时候,也以为自己必定是活不下去了。可后来皇后娘娘仁慈,她派了医女来给受罚的奴婢们上药,并且留下一句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若父母还在,身为儿女又岂能不恪守孝道?如此这般死了,又对得起谁?奴婢这才想明白,生死不过是自己一念之间,但活着,却远远比死去要难千倍万倍。父母生养我们一遭,这份恩情我们无以为报,唯有好好活着,才是最大的孝道。”
柔嘉听完这番话,心中百味杂陈。她自是知道,当初母后之所以在最终时刻改变了主意,不过还是因为舍不得她死在这般的花季年华罢了。而父皇,战死沙场的父皇,他留下的那道令后妃殉节的旨意中,也无独有偶地将自己放在了最后……
想起十几年来,父母对自己无微不至地尊宠与呵护,温热的泪水再度氤氲在模糊的眼眶中,柔嘉吃力地咬着牙,控制自己不发出更大 的声音来惊醒那些睡熟的人。
淌了一会泪之后才开口道:“那……你相信我母后她……失贞变节的传言吗?”
在来中京的路上,便是最最低等的宫人,也听到了关于凌后成为东晋大将军宠妾的传言。这些传言一刀刀的凌迟着柔嘉的心,以至于后来她每日里除了吃饭喝水之外,几乎都不曾张嘴说过话。
“奴婢不信……皇后娘娘在奴婢心目中,永远都是那个仁慈端庄的一国之母。公主,您身为她的女儿,更不应该相信这样的谣言的。”
“是啊,都是谣言,都是谣言……我自是一个字都不信的。”
柔嘉说着,有些吃力地摸索着想要爬起来。但惜于她此时身体虚弱,黑暗中只一把抓住了那宫人的手,柔嘉有些急切地说道:“是啊,我也一个字都不信,母后她不会那样的,母后她……”
她的话堪堪说完,便听得门外院子里有人大声咆哮道:“又是哪个贱人去厨房偷了咱们值夜的人的夜宵?这夜宵的馒头都是有定数的,一夜夜的都来偷几个,这不是要翻了天了么?”
那人说着,嘴里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去。柔嘉和那宫人却是都听得心中一阵骤然的发紧,待听到那脚步声远去,柔嘉再看时,自己手里抓住的那个手腕早就没了。
手里的 窝头被她紧紧地攥出汗意来,一只装着大半碗水的小瓷碗,里头的清涟渐渐点亮了她黯淡的眼眸。
那一次,柔嘉终是缓缓地坐了起身。她费力地啃下了那个窝头,然后,慢慢地喝完了那碗已经凉了的开水。
终究是年轻的身体,在生死边缘挣扎了一段时日之后,她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了。
自那以后,便是再苦再累的活,她也咬着牙挨了下去。
自那以后,便是再难再苦的时刻,她都记着那宫人对自己说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不信自己的母后已经失贞变节,更何况母后若是还活在这世间,她又岂能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半夜里,她便在一阵热一阵凉的高热中,哆哆嗦嗦的挨了过去。
说来也怪,这半夜烧的人云里雾里,到了早上,那身上的热却渐渐散了下去。柔嘉模模糊糊里听得窗外的鸡鸣声,正在梦中,忽觉得身上一凉,紧接着两个脸颊火辣生疼,胸口也沉得喘不过气来。
惊愕中睁开眼,只听那人正尖声叫道:“下作东西!晨起的鼓声都敲了两遍了,你还能偷懒挺尸,真是个不知死活的。还不快给我爬起来!”
柔嘉忙醒过神,只见站在自己面前的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长着一张圆长脸,柳叶眉眼,一张嘴便露出满口贝牙,只是其眉眼虽然生得齐整,那贝齿门前的一颗却缺了。
柔嘉总感觉这样看起来实在是有些说不出的怪异,因不知她是谁,因此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词,唯有瞪大双眼瞧着,耳畔还有些昨夜烧过之后的嗡嗡声响。
“看什么看!”那女孩子话音未落,劈手已甩过来一记耳光,又重又狠,打得柔嘉两眼一阵发黑。
长这么大也没被人这般没头没脑的折辱过,且看她的装束,也定是这苦役司里的受罚之人。真正是想要把自己当作柿子来捏了么?
想着之前在浣衣房时那些惯常懂得逢迎孙婆子的宫人的种种卑劣行径,柔嘉心中便有些怒气生了出来。她咬着嘴唇抽出手,慌乱中没有章法的便照那人面门就抓了下去。
只是才道半空中,两个腕子便早已被握住了,狠狠推回来抵住她喉咙处。
“想还手?我呸!也不瞧瞧自己这副寒酸的怂样?实话告诉你,我姑姑是王府里的管事,这苦役司里,从来就没人敢跟我叫板!”
女孩嘴里骂着,反手将柔嘉推到地上。她身手利索,且力气也很大,这一推之下,毫无与人交手经验的柔嘉便被重重的推到了地上,嘭的一声,正正脸面朝地。
“怎样?知道姑奶奶我厉害了吧?识相的就赶紧起来,给姑奶奶我磕几个响头,我也就饶了你这一遭……”
听得那人还兀自洋洋自得,柔嘉跌坐在地上,有些狼狈地捂着疼痛的前额,下一刻,却忽然站起身来,不由分说地朝她站着的方向撞了过去。
这下子只听得“咚”的一声闷响,柔嘉过后便就势扑倒在之前睡觉的通铺上面。她才刚用自己的头和她迎面狠狠地撞 了一下,此时两人都齐齐倒在床上,觉得眼前一阵昏花,耳畔的嗡嗡声愈发的百转千回。
“你作死啊你!居然敢撞我?你……你简直就是不想活了!”
那女孩想是也撞得不轻,原本迎面扣着柔嘉的手一松,身子就向后仰倒。倒是柔嘉趁势一骨碌站起来,顾不得额上伤口疼痛,也不知哪里来的狠,抱住那人的头死力“咚、咚”又是两下撞过去。
那女孩被撞的稳不住,一个倒栽踪摔下床,碰倒了旁边的桌椅板凳,轰隆隆粉尘四起连声巨响。
听得这样的响动,外头才有一个婆子忙跑过来,见屋里一片混乱,跺着脚道:“唉哟!你们两个这是要作死哟!搞得一铺狼烟狗灰的,你们这是要拆房子啊!”
说着,又冲那女孩道:“云儿!我叫你过来喊她起来上工,怎么就打起来了?”
那云儿见状连忙哭道:“我是来喊她的呀,可她耍赖,睡着不起来。我一着急拉了她两下,她就疯了一样又打又撞。”
看了看柔嘉又急又怒的样子,那个老婆子到底有些不相信,转头问柔嘉:“你打她了?”
柔嘉垂下头,瘪嘴道:“我是动手了,不过是她先动的手。”
那婆子咬着牙根哼了一声,走上去伸出鸡爪子攒了劲,便突突赏了一人一个爆栗。
柔嘉被这一下子敲的疼得捂着头,地上的云儿也愈发哭天抢地。
老婆子一脸嫌弃地吼道:“嚎什么,就知道嚎。大清早的,想让马姑姑听见吗?”
云儿连忙蒙住嘴,看来极是畏惧的样子。那婆子便又道:“不省心的东西,两个都给我出来!”一面摔了门帘,自顾自转身走了。
两人出来之后就被这里掌事的马姑姑一顿好训,指派完了其他人的活计,也许是时日尚早,王府里许多处的马桶都尚未送来,便打发二人去墙角处受罚立规矩。
说是受罚,就是两人各自端着一个大铜盆。铜盆里装了才刚沸腾的滚水,腾腾的热气不住往两人脸上蒸。那铜盆本就沉重,加了滚水之后更是烫得拿不稳。
两人又都怕水泼出来烫着,但马姑姑的话在这一处便是圣旨,不能不遵,因此只能咬牙端着,才端了一会,两人便都是觉得自己手肘贴着铜盆的地方,像被烫熟了一般的难受。
尤其是柔嘉,昨晚被押解到这里来时,脚上连双鞋子都不曾穿上,走了那么远的路,一脚的血泡,此时站久了,只觉得火烧火燎似的灼痛。站了两刻钟,已经有些软软的眩晕。
那孙婆子打着扇子坐在门旁吃茶,椅前靠了根扁毛竹家法棍。但见两人之中有谁略弯一弯身子屈屈膝盖,她抄起家法棍狠狠的就是一下,只抽得人咬牙咧嘴。
盆里的水凉了,立刻又换上热的。这酷刑也不知道要挨到什么时候,云儿抽抽搭搭不住地哭,柔嘉却咬住下唇,将所有的力气都运到手肘上去,全力抵挡臂上的酸乏感。
直站到太阳爬起来老高,旁边的云儿终于“咕咚”一声,连人带水盆一块摔在了地上,再也起不来。
孙婆子这才慢悠悠的起身,拿手里的竹棍在云儿身上拣要害处戳了戳,这才转头问柔嘉:“装死也没用!死了才轻省呢!我来问你们,可是知道错了吗?”
那云儿倒在地上直哼哼,也巴不得这一刻,大声哭喊:“是,云儿知道错了,云儿再也不敢了!”
孙婆子嗯了一下,见旁边柔嘉默不作声,又来问她:“你呢?”
柔嘉整个背都被汗水打湿了,声音自然有些颤:“是她先打人,我不过还手罢了。”
孙婆子白她一眼:“谁跟你论理对错了?在这个院儿里,我说谁有错,谁就有错。”说着向旁边的一个婆子打了一个眼色。
那婆子过来,接去了云儿掉在地上的铜盆。云儿满脸汗水夹着泪水,也不敢去擦,乖乖走到孙婆子跟前。
孙婆子斜了她一眼,道:“再有下一次,看不抽出你的筋来!去,滚去河边把才刚送来的马桶都刷干净了,不刷完不许吃饭。”云儿一叠声应是,连忙出去了。
孙婆子这才回头看着柔嘉,又问:“你想好了吗?”
柔嘉咬紧牙关,仍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只咬着那一句:“我没错。”
说着,到底眼眶里泪光氤氲。
这回孙婆子着实恼了,正待发作,偏有人要取库房里的东西,拿着册子来向她拿钥匙。
打发了这一起,又有几个婆子抬了竹篓去柴房挑火炭,也来请她的示下。
孙婆子不胜其烦,忙的得分身无术之际,只得对旁边的一个婆子道:“她若认错就来回我。不然,就让她端到死为止。”
说罢,一面领着几个婆子去柴房不提。
后院的人声像盆里的滚水,从雾气蒸腾到云烟不兴。灶间里柔嘉仍倔强苦撑,奈何手里的铜盆做不得假,只是越来越沉。
那盆里的水此时已经温了,几个婆子自顾不暇,哪还记得来给她换水?除却急匆匆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余光里便只见到一个烧火的婆子勾着腰在收拾着灶间的柴火,厨房里安静得能听到灶膛下的噼啪声。
到了后来,日头越发地晒。柔嘉实在端不住了,这才屏住气,慢慢弯曲手臂将铜盆放低。
这烧火的婆子勾着腰,将手里一捆稻草扔进灶膛,起来揭开笼屉看了看,反手舀了半瓢水,沿着锅边慢慢掺进去,一面有心无心的道:“我说你这丫头实在也是个傻的,这等时候,说句软话又能怎么样?像你这么没头没脑的傻犟着,在这里往后还有大把的罪等着受呢。”
柔嘉被她这么一说,顿时觉得有些说不出的尴尬,未得思虑间,便蹲下身又用力去端铜盆。可松下来的手臂早回不到原位,她只觉得身子一歪就摔下去。
铜盆砸在地上哐啷啷直转,里头的水便就势流了一地,慌乱之间柔嘉连忙扑过去按住。这一扑用尽了全力,她再想撑坐起来,全身上下竟如同抽走了骨头一样瘫软。
真正是无力,周身连一丝力气都用不上来了。
那烧火婆子三两步走上来,一把拉起她按到旁边的凳上坐了。背转身在灶旁摸了两下,丢给她一碗鸡肉粥。
柔嘉捧着碗双手直打战,连粗瓷的调羹都拿不起来。那婆子不由一叹:“为争一口气吃这些苦,还不如多吃几口饭长二两肉,瞧你这一身瘦的,唉,也不知道你娘是怎么教你的。”
说着,竟然走过来夺过调羹,一勺勺舀了里头的粥,慢慢喂她。
柔嘉一听她提起娘,眼眶里憋了好久的泪水终于决堤而出。她抽抽搭搭的本能的张着嘴,吃下去的粥却似堵在了喉咙里,一点也咽不下去。
婆子瞧着,牵起粗布围裙给她揩了揩,低声道:“傻姑娘,这里是王府的苦役司,什么粗活累活都要干。进来的人都要过这关,过去了也就好了。你的记着一句话,柔能克刚。从今往后要学着长点眼色,不要硬来。知道吗?”
柔嘉还想说什么,还是忍住了,只略略点一点头,忽然想起来问:“先前那是谁?”
烧火婆子只当她问的是云儿,便答道:“她是这里的粗做丫头,叫云儿。说起来,她也可怜。原是王府前面院子里的家生子,爹娘都是王府的老奴了。只这么一个女儿,自然是十分爱着的。小时候据说看着挺水灵,可心眼也大,长着长着,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便总想着去爬王爷的床。也不想想这王府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王妃又是那样的出身,眼底容不下沙子的人,哪里能容着她这样的一份野心?后来也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事,据说是连门牙都被人打落了,全身上下没一处好的地方,血淋淋的就给发落到这里来了。估计是知道自己往后没什么出息了,总喜欢犯嫌惹事。她最最喜欢欺负的,就是你们这些新进来的人。不过也没关系,我老婆子看你也不像是要在这里长待的样子。今后她再说什么做什么,你只不要理她就是了。”
柔嘉听完觉得有些难以置信,却又摇头,咽下一口粥道:“都是一般的可怜人,她怎么这么的往死里相逼?何苦来着?”
这婆子才嗤笑道:“这你还不懂?这世上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性子,高处的有高处的明争暗斗,低处的有低处的自相残杀。只有心里头觉得自在的人,不管到了哪才有自己的自在地。说白了,云儿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啥指望了,这才想着往死里践踏人。这丫头啊,也真正是个糊涂没福气的啊。”
那婆子一面烧着火,一面侧目见她吃完了粥,便收了碗下去,又跑到门口看看孙婆子是不是快回来了。
柔嘉吃完粥之后,便自觉浑身的力气都渐渐回来了。她心里含着感激,便坐在灶前,手里一下一下地学着往里头送着柴火。
火光红艳,照的她一张小脸彤红。干柴在灶里噼里啪啦地燃烧着,只听她嘴里自言自语道:“心自在,才有大自在?母后,这是不是您从前常对我说的那句禅语,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
火光红彤彤的映着柔嘉瘦削苍白的脸,捡拾柴火的双手粗糙不已,她蹲在一地柴火间,浑身上下衣衫褴褛,脸上有几处还带着被掌掴的伤痕。
唯有那两汪黑水晶似的眸子,最深处似乎有什么在苏醒一般的绽放。
这烧火的婆子姓卢,管着苦役司里十几号人的厨房烧煮,手下还有两个打下手的厨娘,柔嘉此后就叫她卢妈妈。卢妈妈待柔嘉极为亲和,只是经此一事之后,云儿和柔嘉结下了深厚的梁子。
孙婆子跟着马姑姑管着苦役司的所有人,白日里忙得跟陀螺似的连轴转,倒也没空天天盯着两丫头立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