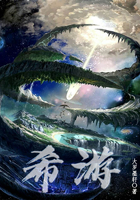睿王脸色微沉,指了站在最前面的喜鹊:“快点滚过去!”
被点名的喜鹊一脸哭相,咬了咬牙,拎着灯笼往前走去,好在那些鬼火闪烁得不久,不待她走近就渐渐消失了。她弯腰在草丛里翻了翻,哆嗦道:“这……这儿有一只猫,居然趴着不动。”
睿王拔剑冷冷地道:“捉过来!”
喜鹊将灯笼放在一旁,哆哆嗦嗦地伸出手,要去捉那猫,谁知道那猫虽然看着老实不动,等人一摸,立即就拼命地挣扎抓挠起来!
“哎哟!是活的?”因为摸着那猫儿是温热的,心下反倒不那么怕了,拼着被抓伤,死命地抱了过来,“捉住了!”
“阿沅待着别动,”睿王说道。然后上前,他正准备一看究竟,不料那猫儿拼命挣扎了几下,居然真的不动了。
“啊!”喜鹊吓得失手扔了死猫。
慕容沅蹲下身去,不敢贸然用手沾染死猫,捡了一根树枝轻轻地拨了拨,然后道:“哥哥,这猫儿的后腿被人折断了。”
喜鹊瞪大了眼睛:“难怪、难怪它方才趴着不动。”
睿王眼睛里闪过一道冷光,哐的一声,将佩剑插回剑鞘,今儿的这出戏,分明是一起人为的装鬼捣乱!
妹妹预料得不错,只要走夜路,有心人就会蹦出来作怪。假如今天不是自己陪着妹妹,而是她自己领着宫人回去,众人惊慌失措之际,肯定不会仔细去看猫儿,而是赶紧领着妹妹避开回去。万一妹妹因此吓病,背后的人得了便宜,还不会被人拿住把柄,真是好生狡猾!
“阿沅,别怕。”睿王习惯性地揉了揉她的头发,静静站在月光下,将妹妹护在身边,静静等着早已安排好的人,神色无比宁静。
过了片刻,两个小太监押着一个扭动的宫女过来。
“启禀睿王殿下,奴才等人奉命在路口暗处等候,看见这个宫女鬼鬼祟祟地往墙根儿处放了一包东西。按照殿下的吩咐,将她悄悄抓住了,等到这边有动静再赶过来。”
慕容沅看清来人,不由得大吃一惊:“你……不就是白天发纸笔的芹香吗?”
芹香低头咬着嘴唇,不吱声了。
“回去再审问。”睿王牵着妹妹的手,上了肩舆,此处黑漆漆的,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不安全,一路疾行回了泛秀宫。
泛秀宫的大门轰的一声缓缓关闭,主殿内,灯火通明恍若白昼。玉贵妃见一双儿女平安回来,神色微缓,却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睿王朝下喝道:“说!今儿的事,是谁指使你做的手脚?”
有宫人上前抽出芹香嘴里的帕子,她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抬头四顾,像是找寻什么似的,脸上露出一片恐惧的神色,显然已经害怕到了极点。
睿王冷笑道:“怎的?还盼着你的主子来救你呢。”
芹香并不回答,只是缓缓垂下了眼帘。
玉贵妃瞧她似是绝望,又似下定什么决心,不由得喊道:“快,抓住她!”
其实两边一直都有小太监抓住芹香胳膊的,但她情知挣不脱,居然猛地把头朝地面狠狠撞去,下一瞬便是血光飞溅!
“啊——”宫人们不由得一声惊呼。
小太监慌忙上前探鼻息,颤声道:“没、没气儿了。”
“没气儿了?!”睿王闻言气恼不已,眼看就要查出背后的凶手,结果就这么断了线,气得上前狠狠踢了一脚!还不解气,回头又在桌子上重重一砸,弄出一片丁零哐当的茶碗声响。
玉贵妃看着地上的一片血污,嫌恶地皱了皱眉:“快拖下去。”
“等等。”慕容沅走到兄长身边,拉住他,踮起脚耳语了几句,“没法子,且试一试吧。”
睿王犹豫了下,缓缓道:“好。”
第二天,慕容沅先去凤栖宫请安。见到了打扮得清爽可人的周宛宛,梳了小小堕马髻,鹅黄色的窄袖衫,翠绿裙子,很衬她那纤细娇弱的气韵,好似一株清灵灵的黄色水仙。
慕容沅心下不由得暗笑,不好意思继续装病了吧。
到了小班的宫殿,一切如常,就是分发笔墨纸砚的时候,昨儿的宫女换了一个,姜胭脂诧异问道:“咦,怎么换人了?”
慕容沅接话道:“昨儿那个作死的奴才,在纸上面捣乱,故意弄个猫爪儿印吓唬宛宛,已经被查出关到慎刑司去了。”
姜胭脂诧异道:“还有这样的事?”
周宛宛急忙问道:“那查出来是谁指使的没有?!”面色恼怒,“原来是有人装神弄鬼,吓我一跳。”
慕容沅冷眼看着她,吓没吓着你不知道,借机演戏你却搞了不少,只是不想和小丫头拌嘴,冷冷地一笑:“等着吧,还在严刑审问着呢。”
一上午都是风平浪静的,总算熬到晌午了。
因为小班是没有下午的课程,中午放学就散课。姜胭脂想起自己昨天嘴快,有些后悔,想要缓和一下冷淡气氛,上前问道:“宛宛,听说你昨儿不舒服?好些没有?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凤栖宫?”
周宛宛一脸骄矜:“不用了,等下太子殿下会来接我的。”
不过很快,她就骄傲不起来了。靖惠太子的确过来接她,却没急着走,而是先朝慕容沅表达歉意:“昨儿父皇突然叫我过去,临时让出宫半点事,回来的时候宫门已经落匙了。”
“没关系。”慕容沅乐呵呵道,“昨儿晚上父皇过来看我了。”
靖惠太子微微一笑,笑容和煦好似三月里的春风,他从怀里摸了一个平安符出来,递给妹妹:“我路过护国寺的时候,给你求的。”
慕容沅甜甜道:“谢谢太子哥哥。”
而旁边,周宛宛气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昨天看到猫爪子印受惊吓的人是自己,摔倒的也是自己,为什么要给她求平安符?可是眼前二人不仅身份尊贵,还都是长辈,一个是自己的嫡亲舅舅,一个是隔了肚皮的小姨,根本不能上去和他们理论。心里一腔委屈,忍不住又盈了一眶晶莹泪水。
“周小姐小小年纪,别是得了见风流泪的毛病吧?”睿王身着宝蓝色的团纹四爪龙袍,一脸寒气走了过来。
周宛宛顿时不哭了,气得嘴歪。
睿王根本不理会她,只是朝靖惠太子行礼:“太子殿下,我看周小姐身子不适,还是快些带她回凤栖宫去吧。”心下懊恼,明明自己离妹妹更近,怎么太子每次都跑在自己前面?再说凤栖宫和泛秀宫关系很好吗?整天缠着也好意思!
而另一边,周宛宛又是咬牙,又是跺脚,上前拉住靖惠太子的衣袖:“舅舅,我们回去!省得看人家的鼻子眼睛的!”
靖惠太子神色有几分无奈,几分不悦,但是没有驳回她:“好。”看了看一脸不悦的睿王,自己也觉得有点没意思,叹气领着人去了。
慕容沅抬头胡乱看了一圈,今儿没有见着姬暮年,不过想想也对,他只是太子的伴读,又不是太子的奴才,散了学,自然就回姬家去了。
睿王过来招呼妹妹:“怎么还在发呆?”
慕容沅不敢说自己在想姬暮年,低了头,被哥哥习惯性地揉了揉,然后恍恍惚惚上了肩舆。刚到泛秀宫门口,就有小太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急急禀道:“捉住了!有人真的想要谋害芹香。”
“走!”睿王目光一亮,扯着妹妹下了肩舆,“进去看看!”
昨儿芹香撞地破头而死,慕容沅不愿意让线索就这么断了,于是交代哥哥,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清点一遍,记了下来看好。然后对外只说芹香未死,正关押在慎刑司审问,如此一来,假如幕后的人按捺不住的话,多半就会找机会杀人灭口!
果然抓住了!就连慕容沅都有几分兴奋,进门问道:“到底是什么人?”
大殿内,玉贵妃仪态万千端坐其中。
下面一群宫人,当中捆着一个中年嬷嬷,慎刑司的人上来禀道:“这位陈嬷嬷,在景阳宫葛嫔娘娘手下做事。今儿上午,她偷偷摸摸去了慎刑司,试图贿赂别人,然后给芹香送一碗茶,里面有毒。”
那陈嬷嬷肯定想不到,芹香早就已经死了,这不过是一个早就布置好的局,专门等着她来跳呢。慎刑司的小太监收了银子,一转脸,就让人把她抓了送过来,并且提前灌了东西,浑身软绵绵地用不上劲儿,免得她自寻短见。
“快说!是谁指使你的?”慎刑司的人上前一记窝心脚。
陈嬷嬷疼得咬牙哆嗦:“奴婢说了,是奴婢之前跟芹香有些过节,听说她犯了事儿,所以赶着过去落井下石……”
“放屁!”睿王一向涵养不错,这会儿气得爆了粗口,去里面找了一条马鞭出来,狠狠一顿抽打,“芹香犯了事,慎刑司早晚都要处置,用得着你去落井下石?你就不怕被人发现惹上麻烦?!”
陈嬷嬷脸上青一道、紫一道的,疼得脸上的肉直跳,还是坚持哆嗦道:“是奴婢太、太恨芹香了……太心急了。”
竟是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
睿王正在气恼,忽地传来一声响亮通传:“皇上驾到!”
殿内的人都站了起来迎接圣驾,慕容沅没那么多讲究,上前先搂住了武帝的胳膊,陪着他到大殿正中坐下。然后指了陈嬷嬷,气呼呼道:“就是她!背地里和芹香一起装神弄鬼的,在墙根儿藏猫儿吓我!”
“知道了。”武帝朝小女儿点了点头,安抚了几句,然后朝下问道,“这奴才是哪个宫里的?”
“回皇上,是景阳宫葛嫔娘娘手下的宫人。”
武帝又问:“可问出什么来了?”
“没有。”睿王气恼道,“这狗奴才嘴硬得很,说什么都不肯松口,一口咬定是她和芹香的私怨。”怕父亲不清楚,解释道,“芹香就是昨儿放猫的宫女,这个狗奴才的同伙!”
“缪逊啊。”武帝沉吟了一下,“你带着人,和慎刑司的人走一趟吧。”
“是。”缪逊领命而去。
大殿里的人一窝蜂地离开,顿时安静下来。
武帝的神态颇为淡定,像是并不为那些污糟事儿着急,朝慕容沅笑问:“这两天去学堂可还习惯?”让她退后了两步,打量道,“看起来,我们阿沅是越发懂事了。”
慕容沅笑眯眯拍马屁:“都是父皇教导的好。”
“哈哈。”武帝闻言大悦,虽然明知道是有意讨好的话,可是小女儿长得粉雕玉琢,乖巧机灵,脆生生地说出来就是那么讨喜。拉了她在身边坐下,说起家长里短,又问起睿王的学业,全然是没有皇帝架子的慈父一般。
泛秀宫内气氛温馨柔和,慎刑司那边却是一片阴冷和惨叫,那陈嬷嬷还真是一块硬骨头,咬牙、咬牙、再咬牙,直到第三种刑具上身的时候,才惨叫道:“我说,我什么都说……”
缪逊得了供词,脸色仍旧一片乌云不散,飞快地找到皇帝,竟然先要求玉贵妃母子几个回避,然后才悄声道:“皇上,陈嬷嬷招了,说是……这一切都是皇后娘娘指使她的。”
武帝的脸色瞬间阴沉下去,伸手抓起供词:“起驾,回金銮殿!”
玉贵妃领着儿女们追了出来,不解问道:“皇上怎么走了?”看了看他手里紧握的供词,“陈嬷嬷怎么说的?到底是谁?”
“不必问了。”武帝皱眉道,“这件事,朕自会妥善处置。”
慕容沅心下猜测,必定是陈嬷嬷的供词十分棘手,以至于不能随便公开。不知道里面牵扯到了什么人,叫父皇如此紧张,竟然不许母亲再问,于是识趣地闭了嘴。
忽然之间,嗅到一股风雨欲来山河倾的气味儿。
武帝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大老婆、小老婆,儿子、女儿们全部叫来,开一个开堂审判会,神色肃杀道:“缪逊你来说。”
“是。”缪逊声音清晰,说道,“昨儿在学堂的时候,宫女芹香负责分发文房四宝,她发给周小姐的纸上面,有猫儿的爪子印,当时三公主也是在场的,从头到尾见到了这件事。”
慕容沅脆声道:“有人知道我怕猫儿,想吓我,不过没有吓到。”
众人听了,各自的脸色都有点丰富。
缪逊又道:“虽然没有吓到三公主,但却吓到了周小姐,受了惊吓,还专门请了太医过去。三公主听到消息过去看望,一直陪到天黑,等周小姐醒来才离开凤栖宫。”
慕容沅一脸惆怅之色:“只有确认了宛宛没事,我才放心哪。”
众人的脸色越发五彩斑斓起来。
尤其是郗皇后的脸色,变化微妙、十分玄奥,什么确认了宛宛没事才放心?!小丫头满嘴胡说八道,昨天分明就是故意赖在那儿不走,折磨宛宛,憋得她脸色通红好不可怜,不知道是谁教的损招儿!心下暗暗咽了一大口恶气。
缪逊接着道:“本来若只是有人捣个乱子,就这么了了。偏生有些人不肯善罢甘休,存了黑心,居然在三公主晚上回去的路上,又放了一只弄伤的猫儿,鬼哭狼嚎地继续吓她。”
“哼!”武帝接话道,“幸亏老六反应机敏,不但护住了妹妹,还把暗地捣鬼的芹香给抓住了。”话锋一转,并不提芹香当时已死的事,“可是芹香去了慎刑司以后,却有人要杀她灭口!”
整个事件的起始经过已经明了,众人各自一番思量。
靖惠太子抢先怒道:“是谁这么坏?阿沅年纪那么小,居然几次三番地想要吓坏她?”他问,“父皇,可抓到了那个杀人灭口的黑手?问一问,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的!”
武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皇后在长子早夭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身孕,葛嫔等人也没有生下儿子,不得已……二房才从三房过继了一个儿子。后来又过了十几年,河间王都已经十八岁了,已经娶妻生子,皇后才又生下靖惠太子。
因为生得晚,不容易,这个儿子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完完全全就是后宅妇人养出来的公子哥。往好了听,可以说是仁厚和善,实际上,性子十分绵软,丝毫没有杀伐决断的气魄。
每每想到此处,自己都忍不住一阵惋惜懊悔。
“父皇。”靖惠太子等了一会儿,又问,“那人到底是谁?”
武帝眼里闪过一丝失望,自己的沉默,难道不是已经说明和皇后有关吗?这个天真的儿子,还在傻乎乎地一直追问。指了指陈嬷嬷,叹气道:“你自己问吧。”
靖惠太子终于察觉出有点不对劲,可是众目睽睽之下,已经问了两遍,总不能就此打住,只得朝陈嬷嬷问道:“是谁指使你的?”
陈嬷嬷还是那一套说辞,哭哭啼啼的:“是皇后娘娘收买了奴婢,让奴婢去慎刑司贿赂宫人,然后好杀了芹香灭口。”
“你胡说!”靖惠太子闻言大怒,但他养得金贵,骂人的脏话是不会的,只是气得发抖,“不许造谣!攀诬中宫皇后乃是死罪!”
陈嬷嬷哭道:“奴婢不敢撒谎。”
郗皇后冷冷地看向她,质问道:“你这狗奴才,本宫何曾指使过你做什么?你红口白牙地攀诬,有何凭证?!”继而看向葛嫔,“本宫没有记错的话,她是你景阳宫的奴才吧。”
“皇后娘娘这是什么意思?”葛嫔一脸震惊之色,“她是我景阳宫的奴才不错,但是……嫔妾可没有指使她做过什么!难道皇后娘娘的意思,是嫔妾唆使了什么?”
豫王四平八稳地坐着,淡淡接话:“若是陈嬷嬷没有被严刑逼供,不说清楚的话,人人都知道她是景阳宫的人,可就都以为是景阳宫做的手脚了。”
靖惠太子脸色不好看。
“二皇兄你的意思,是有人借机陷害景阳宫?”陈嬷嬷又招供,说是皇后娘娘指使的,“是说母后,故意陷害你们?!”
豫王今年三十多岁了,加上性子本就稳重,眼见兄弟已经炸了毛,说话声音还是不徐不疾的。
“太子殿下,我可没有那样说,只不过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抬头看向皇帝,“父皇,慎刑司是什么地方,谁敢派人去杀人灭口?这件事分明是有人栽赃陷害,一定要彻底查清楚!”
慕容沅在旁边听得有点晕,到底是皇后要陷害葛嫔,还是葛嫔在陷害皇后,真真假假,一时有点辨不清。
葛嫔淌眼抹泪的,可怜巴巴地看向皇后,哭诉道:“皇后娘娘,嫔妾一直敬你、尊你,豫王一向孝顺你,此事断然与我们母子无关,一定……一定是被人陷害的。”说着,故意瞥了玉贵妃一眼,“贵妃娘娘,你说会是谁呢?”
睿王眼尖瞧见了,冷笑道:“葛母妃不必含沙射影、看来看去的,不就是想说泛秀宫在捣鬼,故意挑唆景阳宫和凤栖宫吗?”他年纪不大,口角却是十分清晰伶俐,“葛母妃也未免把我们想得太龌龊了!阿沅是我的亲妹妹,是母妃的亲生女儿,岂能拿她来做诱饵?!”他怒声道,“做得出这样龌龊事的人,天地不容、猪狗不如!”
这便是发咒赌誓了。
虞美人小声道:“是啊,贵妃娘娘怎么会去害三公主呢。”
葛嫔一声冷笑:“难讲啊,贵妃娘娘固然不会害自己的女儿,别的有心人未必不会,闹得皇后娘娘、本宫和贵妃娘娘争执,正好捡一个大便宜呢。”
虞美人顿时脸色一白:“葛嫔娘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葛嫔讥讽道:“你自己慢慢体会咯。”意思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是靖惠太子、豫王、睿王都牵扯进来,落了不是,可不就剩下代王一枝独秀了嘛。
虞美人不承想自己帮衬说一句话,就惹出这么大的麻烦,顿时急得哭了,朝着皇帝垂泪道:“皇上,你要相信臣妾!”又急急看向玉贵妃,“嫔妾没有,嫔妾断然不敢算计贵妃娘娘和三公主的,嫔妾没有……”
还别说,经过葛嫔这么一冷一热的讥讽,就连慕容沅瞧着虞美人,的确也有那么几分可疑的样子,毕竟她也是有皇子的后妃啊。大殿内众人却是七嘴八舌的,纷纷为自己辩解,一个个都是无辜的、清白的,都在隐隐指责别人,只有傅婕妤,因为膝下没有皇子没人指责。
武帝朝她问道:“婕妤可有什么话要说?”
傅婕妤神色淡定道:“仅凭一个奴才的供词,做不得准,谁也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到底是受了何人指使。”平静地回视皇帝,“依臣妾看,这件事谁最受益,谁的嫌疑就最大。”
谁最受益,谁的嫌疑就最大。
慕容沅在心里点了点头,这话说得不错。
郗皇后当即道:“我乃母仪天下的中宫皇后,承明又是太子,有什么理由跟慕容沅过不去?除了落不是,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葛嫔接话道:“不管这事儿是谁做的,终归不过是害死了一个奴才,惊吓了三公主,并非什么大罪过,我们景阳宫也是捞不到好处的,只能白白惹一身臊罢了。”
玉贵妃神色凛冽,只有一句:“谋害亲生骨肉的人,天诛地灭!”
剩下虞美人好不可怜,惶惶哭道:“天地良心,我这个人是笨笨的,七皇子为人也老实,年纪又小,就算这件事能落出什么好处,也轮不到我们啊。”
慕容沅听她们一个个说得委婉,简单总结了下。
皇后的意思,老娘是中宫皇后,儿子是太子,已经贵不可言、贵不可攀,岂会为了一点小事坏了自己的名声?葛嫔则是说,反正这么一点破事儿,也不可能废皇后、废太子,景阳宫才不做没好处的傻事呢。
玉贵妃就不用总结了。
至于虞美人,别看平时木呆呆的样子,说话也挺讲究,奴家姿色平常不得宠,儿子年幼争不过哥哥,母子两个都根基不稳,哪里敢去陷害别人?再加上一把热泪,模样说不尽的楚楚可怜。
“好了。”武帝抬手一挥,让全场肃静下来,继而道,“起初这个奴才就招供,是她自己和芹香有私怨,所以才杀人害命。”声音一顿,“依朕看,全都是这个奴才胡言乱语,借机攀诬他人试图脱罪!”
皇帝的风向怎么突然变了?众人都是一愣。
武帝一身明黄色的五爪龙袍,身量高大,端坐如钟,哪怕已经年过半百,说起话来仍旧中气十足,断然道:“来人!将这胡言乱语引乱宫闱的奴才,拖出去直接打死!”
陈嬷嬷顿时脸色一变:“不,不……”
眼看都要乱起来了,为什么……为什么突然变了,当初那人说好会在大牢里面救自己,找个尸体替换的。现如今皇帝要当场打死,哪里还能作假?自己的小命岂不是玩完了?虽然早就知道实情风险很大,但是……总归还是抱着一线希望。
“怎么……你还有话说?”武帝问道。
陈嬷嬷怔了怔,最终却是一片沉默。说与不说,眼下都是难逃一死。不说的话,那人还能安置照顾一下自己的嗣子,罢了……她一咬牙、一狠心,把眼睛缓缓闭上,只求后继有人大富大贵吧。
武帝便不再多问,挥了挥手。
陈嬷嬷被人带到了金銮殿台阶之下,在广场中间,刑具很快抬了上来,啪的一声,廷杖狠狠落下!一声、一声,又一声,缪逊奉皇命出来监刑,悠悠喝了一句:“往死里打。”
“啪啪啪——”
闷响之声不绝于耳。
一下下的,仿佛正好和大殿内众人的心跳合上,震得人心颤动,而陈嬷嬷很快一片血肉模糊,凄厉地惨叫了几声,最终断了气。
“除了阿沅,其余的人都回吧。”武帝那金振玉聩的声音里,透着一缕隐隐的疲惫,但却不容置疑,“走吧,别再惹朕心烦。”最后呵斥了众人一句,“谁要是敢在后宫里兴风作浪,外面就是下场!”
郗皇后、葛嫔、虞美人的脸色都不好看,傅婕妤一贯置身事外,玉贵妃则是从头到尾保持她的高傲,齐齐行礼告退。
豫王迟疑了下,也道:“父皇保重身体,儿臣告退。”
代王早就跟着虞美人走了,睿王也跟玉贵妃走了。最后剩下的,是还没有缓过神来的靖惠太子,脸色微微发白:“父皇,这件案子就这样了?都还没有……”
“怎么,你还嫌不够?”武帝反问,喝道,“你还嫌没把后宫搅乱?!”
“不是。”靖惠太子赶忙辩解,“儿臣的意思,除了乱子,总得把幕后黑手揪出来才行啊。”有几分不解,几分抱怨,“怎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断了案……”
“放肆!”武帝闻言大怒,“你是说朕糊涂了!”
“儿臣不敢。”靖惠太子慌忙跪了下去,“父皇息怒,儿臣只是替母后的清白名声着想,替慕容沅的安危着想,若是不把幕后黑手揪出来,岂不是给那人继续猖狂的机会?只怕还会更得意呢。”
“哼!”武帝冷笑,“那你打算如何揪出来?是再严刑逼供一回,让那奴才继续攀诬皇后,或者另外攀诬一个人?弄得后宫翻云覆雨的才好,对不对?亏你还是做储君的,一点远见也无!”
靖惠太子不敢分辩,只能道:“儿臣驽钝,还请父皇教导。”
武帝本来没打算留下太子的,此刻被气着了,让人关了门,站起身来在大殿内来回踱步,怒声骂道:“你是太子,是储君,是大燕江山未来的皇帝,不懂得顾全大局,只知道争一时之气,叫朕怎么放心把江山托付给你?!”
这话有些重了,靖惠太子抬起头,脸色更白:“父皇……”
“朕来问你。”武帝微微倾身,“皇后现在是不是好好的?阿沅现在是不是好好的?”声音微顿,继续问道,“如果朕不打死那个嘴硬的混账,任凭她惑乱人心,惹得六宫之人互相猜忌不休,又会不会再闹出点别的事来?本来风平浪静的日子,忽地变得混乱不休,难道那就是你希望看到的结果?”
“不!”靖惠太子摇头道,“可是……”
“可是你想查出真正的幕后黑手,对不对?”武帝一声冷哼,“那种奴才横竖都知道自己要死,嘴又硬、皮又厚,你拿什么让她说出真相?她凭什么替你牺牲性命?那幕后黑手,必定一早就许了她足够丰厚的条件,让她至死不松口,所以你就算把她打烂了,也听不到你想要的真相!”
“那要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武帝不只是冷笑,更是讥讽,“你一个储君,连这种蠢问题都好意思问出口?!师傅都是怎么教你的?”回头看向小女儿,“阿沅,你知不知道要怎么办?”
慕容沅稚声稚气道:“阿沅不是很懂,但是我想,父皇既然下令打死陈嬷嬷,就一定是早想好怎么办了。”既顾及了靖惠太子,又不着痕迹给皇帝拍了一通马屁。
“看见没有?”武帝指着靖惠太子,“你妹妹都比你通透一些!”其实倒也未必如此,只不过皇帝一向偏心小女儿,加上此刻对太子十分失望,不免说出一些气话,“别再问朕为什么了!自己滚回去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再来回朕!”
靖惠太子被骂得狗血淋头,脸色苍白,“是,儿臣告退。”
大殿内只剩下武帝和慕容沅父女两个,慕容沅见父皇怒气难消,赶忙续了一杯茶,脆脆声道:“父皇消消气,太子哥哥多想一想就明白了。”
“蠢货!这样的太子……”武帝有着满腹牢骚,却不便跟小女儿唠叨,继而缓和了神色,笑道,“还是朕的阿沅听话乖巧,最让父皇舒心。”
慕容沅听了这话觉得熨帖,父皇一向都是最喜欢自己,最疼爱自己的。
武帝忽然问道:“阿沅,你觉得谁最可能是坏人?”
怎么又来考自己了?慕容沅搓了搓肉乎乎的小手,小胳膊藕节似的,趴在桌子上托住腮帮子:“我觉得呀,未必就是皇宫里的人呢。”
武帝顿时眼睛一亮,本来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女儿这么有见地,带着吃惊和好奇,追问道:“哦?那你觉得是什么人?”
现在靖惠太子走了,慕容沅存心讨好父亲,加上自己年幼,说错了,父亲也不会怪罪,当即叽里呱啦道:“我觉得傅婕妤的话很有道理,谁最受益,谁的嫌疑就最大!”细细分析起来,“陈嬷嬷指证母后,凤栖宫肯定难脱嫌疑;而她又是景阳宫的人,闹出来葛母妃也难以择干净;母后和葛母妃争执不休,不免就会怀疑有人渔翁得利,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我的母妃啦。”
“如此三宫相争,弄得几败俱伤的时候,大家可能突然发现,原来捡了便宜的是虞母妃和七皇兄。如此一来,谁都不会放过他们母子的,到时候三方怒气一起发作,只怕叫人难以消受呢。”
“但是仔细想想,就算闹出一些矛盾来,皇后还是皇后,太子还是太子,我的母妃、哥哥,二皇兄豫王、葛母妃,也都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怎样,虞母妃又能落到什么好处呢?得到的,不过是难以平息的众人怒火。”
慕容沅总结了一下:“这个时候,后宫里面大家斗得跟乌眼鸡似的,岂不是便宜了外面的人?而那个人……”抬头看向父亲,没有叫自己停住的意思,鼓起勇气道,“毕竟从明面上来说,实际上,河间王才是父皇的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