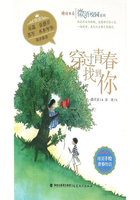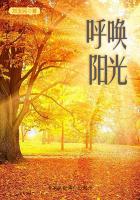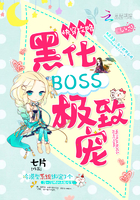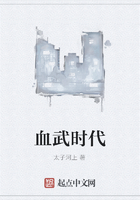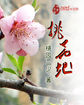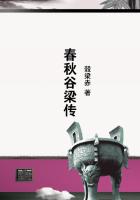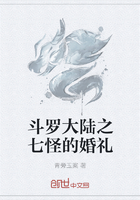罗红与我们同行的中国税务报的邵总编是朋友,他邀请我们一起登飞机空中拍摄。因为我们采访计划的下一站是到纳库鲁湖去看火烈鸟,只好与这位非凡的摄影家告别了,我们相约在北京他的摄影展上见面。
再次穿过稀树草原,我们向昨天刚刚相识的老朋友——满身条纹的斑马、大眼睛的瞪羚、头顶利器的角马和脖子高过树林的长颈鹿告别。对我们的高声呼喊,它们颇不在意。只有那倒卧在草丛中的狮子抬起头来厌烦地望了我们一眼,然后又趴下去静养。如卡伦所说,它们要午睡了,“在家族的簇拥下心满意足地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静静地卧在金合欢树投下的柔和、泉水般清凉的绿荫里”。
我们向北走出草原后,开始爬上2000米高的肯尼亚高原。高原的景色要比草原丰富许多,有成片的树林和草地,间或还有连片的农田,上面铺着金灿灿的燕麦和立着的已经成熟的玉米,边上还有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我们还看见了连片的村落,绿树环抱的房舍,一家连着一家沿街的店铺。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栅栏围成院子的小学校,穿着整齐校服的卷发的男孩子和光头的女孩子走进校门。仔细看黑人很漂亮,都是双眼皮大眼睛厚嘴唇,皮肤细腻光亮,特别小黑孩子更可爱,我们非常想摸一摸他们毛茸茸的头。不知他们是不是马赛人的后代,政府鼓励他们定居务农,放弃“磨难主义生活方式”(马赛人也被称为磨难人,他们孤独地住在丛林中,关在土寨子里学习部落的风俗,锻炼体力、勇气和耐力),而接受正规的教育。我们看见路边走过的许多穿西装的男人和穿连衣裙的妇女,但愿他们都是新一代的马赛人。我发现,肯尼亚人特别愿意行走,无论是男是女,都是长腿细腰,走起来步伐很大,特别快,很轻松的样子,不管乡村城市到处都是疾走的人,怪不得这个国家出现那么多田径的世界冠军,因为整个国家就是一个人人参加的田径训练场。
我们有幸进入了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大裂谷省省会纳库鲁城。城市并不大,街道也不宽,沿街排列着二三层的小楼,涂着鲜艳的颜色。非洲人对鲜丽的色彩很偏爱,无论衣着还是建筑都是浓妆艳抹。繁华的商市熙熙攘攘,清雅的街心小公园的长椅上挤满了老人。街道也很拥挤,更多的是非机动车,连拉脚的都是后座宽大的自行车。导游小邓告诉我们,那自行车是中国的永久牌,这个城市还引进了一家中国的自行车厂,专门生产符合非洲人需要的永久牌自行车。在东欧国家访问时,我曾看到过一家建在保加利亚的中国的电视机厂,在肯尼亚又看到了自行车厂,“中国制造”真是无处不在了。
出城南行,我们闻到了扑面而来的鲜湿气息,因为已经走进了由草地、沼泽、树林和山地组成的200平方公里的纳库鲁湖国家公园了,其核心部位是52平方公里水面的纳库鲁湖。这里气候温和,湖水宁静,植被丰茂,栖息着400多种、数百万只珍禽,被世人称为“鸟类的乐园”“水禽展览会”“世界上最大的鸟类避难所”和“鸟类学家的天堂”。每年有大批的学者来这里考察研究,爱鸟者更是纷至沓来,他们要观看如云霞般飘浮在湖面上的鸟群和火烈鸟群突然飞起那遮天蔽日的胜景。
可惜蒙蒙的细雨让湖面上一片苍茫,湖畔的泥泞让我们无法走近美女纳库鲁的身边。我们登上湖畔的一块高地,只见湖边的树林影影绰绰,湖面上虚无缥缈。依稀听到了火烈鸟呀呀的鸣叫,它们招唤远方的来客快些走近它们的身旁。
我们祈祷,明天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
纳库鲁湖和火烈鸟
我们的旅行是够浪漫的,前一天晚上住在马赛马拉的树林宾馆里,昨晚住在纳库鲁的花园别墅里。这房子由六角形的木制尖顶和石块砌成的墙组成,古朴而清凉。一栋又一栋的石屋由树篱围起,那树上开着红色、紫色、黄色和白色的小花,那花的形状有点像中国南方的三角梅。房前屋后立着遮阴的热带树木,身高叶阔,枝头站着啼叫的鸟儿,羽毛闪着彩色的光泽。整个别墅区用带刺的蒺藜和外面阻隔,但散漫在草地上的动物清晰可见。
老天很成全我们,天上挂着一丝丝游云,太阳灿烂但并不耀眼。昨夜的雨让有点泛黄的草地格外青翠。路边亭亭玉立的树像披挂了钻石一样闪闪放光。静如处子的纳库鲁湖上飘浮着淡淡的面纱,如烟如絮,透出阵阵诱人的朦胧美。
我们的旅游车沿着曲折的小路向湖边走去,又看到了马赛马拉的那些老朋友,野牛、角马、斑马等,它们表现得要比马赛马拉的同类热情,但我们并没有把镜头和热情投向它们,我们的心里只有火烈鸟。当晨雾散去的时候,车停在了湖畔,我们踏着细软的白沙,向湖水靠近。我们看见了那浮在湖沿的一片片红云,那就是拥挤在一起的火烈鸟了。这种又名大红颧的候鸟,最喜欢集群,平常总是几万只鸟聚集在一处湖面和沼泽里,这是一个庞大的鸟的家族部落,它们相依为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离不开谁。在这个纳库鲁湖就生活了200万只,占全世界火烈鸟的三分之一。经鸟类专家考察,这个火山湖盐碱度比较高,特别适宜火烈鸟主食的浮游生物生长。这里自然成了它们美食的天堂、生活的乐园。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肯尼亚人从来不伤害鸟类,他们没有捕鸟吃鸟的恶习。当然湖区也没有建设污染湖水的工厂。水草丰美,邻里和睦,鸟儿谁还愿意离开。
鸟类是森林和草原的保卫者,是它们抑制了对植物有破坏作用的生物的生长。可惜因为农药和许多化学药剂的使用和人类的贪婪,让鸟类正面临灭绝的灾难。如果有一天蓝天上没有鸽子飞翔,树林里没有鸟儿歌唱,那么人类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我们的老祖先孔子早就提出“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的保护鸟类的思想,可是我们有些不肖子孙以玩鸟吃鸟为快,他们大概就是被西方人耻笑的丑陋的中国人吧?
看着我们慢慢地向它们走近,火烈鸟并不在意,它们和同伴擦肩搭背,低头叨食着水中的小鱼小虾小蛤蜊,发出叽叽嘎嘎的笑声。最先惊起的是那一群鹈鹕,这是一种像天鹅一样的大鸟,白胖的身子,兜形的大嘴,里面可以装一条半大的鱼。宽大的翅膀拍打水面,身体腾空而起,然后像滑翔机一样在湖面上盘旋,接着一只跟着一只地向远离我们的湖面飞去。兄长们的转移让火烈鸟警醒,那一望无际的鸟们都停止了低头找食,全部伸直脖子望着我们这个方向。好像经过精心的排练,几万只鸟唰的一下,头都朝一个方向,动作神奇地统一,如接受检阅的士兵。这时,我们看清大约几百米外的火烈鸟,红翅膀、白身子和黑色的尖嘴。导游提醒看得发呆的我们赶快拍照,于是长枪短炮一起对准湖水中凝视我们的鸟群,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我们先照湖和鸟,然后再以鸟为背景照我们自己。先后十分钟的时间,那鸟还是静静地注视着我们,那亮晶晶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这群忘形的人类,它们好像在尽一种群众演员的义务。
也许看我们忙活得差不多了,火烈鸟突然腾飞起来,几万只鸟同时掠起,我们头上好像升起一片红色的霓虹,它遮住了天际。它们在我们的头上呼啦啦地漫过,然后向湖的那一边飞旋而去。火烈鸟在完成了接待我们这帮中国人的任务之后,去和那群远飞的鹈鹕鸟会合了。这是我所看到的鸟群的最神奇和壮丽的表演,此景也许只为纳库鲁湖独有。
望着远飞的火烈鸟,我们站在湖畔久久不愿离去。小邓说,快走吧,在回内罗毕的路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内瓦沙湖,那里不仅能看到火烈鸟,还能看到河马。我们又打起精神,登车北上了。
内瓦沙湖没有纳库鲁湖那么大,可它被青山环绕和绿树拥抱,更显得神秘。我们要看清它的美丽容颜,只好乘船而入了。正好有几位驾船的黑人朋友在岸边等客,他们为我们穿上红色的救生衣,又把船摇向湖心。我们的游船又惊起了一群群鹈鹕和火烈鸟,这一次更近距离地观察了它们的飞行表演,那鹈鹕飞离水面时用黄色的脚蹼拍打水面,像水陆两用飞机那样在水上滑翔,然后渐渐跃出水面。这回我们看清了那火烈鸟嫣红的翅膀、黑色的后背、雪白的腹部和黄色的脚掌,而嘴喙漆黑而尖利。我们还与成双成对的鸳鸯相遇,非洲的同类和中国的一样,它们亲昵相依,并不避人。难道它们不怕凶残的河马袭击吗?
我们让同船的人民日报的记者李丽问驾船的黑人,她初通英语,可一时想不起“河马”这个单词。她只好说了个“河”,又说了个“马”,那个黑人朋友笑着点头,然后把船摇向湖心处,他指着远处漂浮的几块黑黢黢的木头,发出“马马”的声音。我们仔细一看,上面立着几只小鸟正在朽木上叼啄,那是鸟,怎么是马呢?当船划近时,我们才看清,那朽木就是浮在水面上的河马头,它们半睁着眼睛,正窥视着水面的动静。
河马是非洲独有的一种大型杂食性哺乳动物,它的体重一般都有三四吨,仅次于大象。但它的嘴大为动物之最,长而阔,甚至可以装下一个人。它的下犬齿最长达一米,如象牙一样珍贵,因此长期被猎杀,原来尼罗河中河马最多,现在已经灭绝,只在中非的湖河中还幸存一部分。别看河马体重腿短,但它的奔跑速度连短跑运动员也赶不上,时速可达30公里。河马因为皮肤怕晒,长期潜伏在水里,只露半边脸,它的鼻孔、眼睛、耳朵都在脸的上部,几乎在一个平面,嗅、视、听兼呼吸,什么也不耽误。如果说狮子和豹子是草原和山林里的霸主,那么河马和鳄鱼就是水中的霸主了。别看河马长得丑陋憨厚,可一旦发怒,能把水里的船拱翻,那血盆的大口,让岸上再勇猛的动物也惧怕几分。它发火时能一口把粗大的尼罗鳄咬成两截。河马一般不伤害另类,只有母河马为保护小河马具有领域攻击性。每年非洲都有数十人因接近它们的领地而被攻击丧命。其实河马平日是很胆小的,它们昼伏夜出,到岸上觅食,走进菜地,听到人们的吆喝,掉头就跑,而且再也不敢到这片地里来。另外,河马最怕蚊虫叮咬,因此,它把各种食虫鸟奉为头上宾,并长期共存关系良好。你没见那些小鸟正在河马的头上蹦跳吗?因为有了它们的守护,蚊虫再不敢来纷扰。
在我们向潜伏在水中的河马群靠近时,湖畔树丛中的长颈鹿都伸着它们长长的脖子向我们这边张望。真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难道它们愿意看到船翻人亡的惨剧吗!有经验的黑人船手慢慢地把我们的船向远离河马的方向划去,河马们合上了微张的眼睛,它们头上的食虫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我们下船上车,要在天黑前赶回内罗毕。我更着急,一个哈尔滨的小伙子正在新江苏饭店等我见面。
我的老乡与戴安娜
郭青和我一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没想到在遥远的非洲还能见到家乡人,让同行的伙伴们都很羡慕。他向大家打着招呼,说晚上他请我们吃饭。
郭青是个典型的哈尔滨小伙子,高大英俊,热情爽朗。他大学时读的是建筑专业,一毕业就在哈尔滨办了建筑设计公司,搞得十分红火。手里有了点钱了,又想向海外发展,欧美和日本去的中国人太多了,他想到了非洲。一年前,他来到肯尼亚的内罗毕,立刻喜欢上了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当时来这里的华人不多,但干什么都能挣钱,有来自温州的两口子,做了几年豆腐,现在又有房又有车了。一位姓王的医生建议他办中餐馆,来肯尼亚干事业和旅游的华人越来越多,但能吃家乡饭的地方太少了,另外肯尼亚人对中餐也特别喜欢。可小郭毕竟上过大学,他不甘心当个餐厅的小老板。内罗毕毕竟是联合环境署所在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是他经常听到的话题。肯尼亚虽然自然生态很好,又以野生动物的乐园闻名全世界,但这个国家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老百姓生活所用燃料就是木材。结果这个本来森林资源丰厚的国家,现在的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5%了。(看来马赛马拉的稀树草原几百年前也可能森林密布,就像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似的。是人类过分的采伐,让那里沙化了。)身在肯尼亚的联合国环境署不能容忍肯尼亚再毁林取热了,他们要求这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要尽快恢复到13%!
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关系一个非洲贫穷国家的国计民生,从总统到每一个国民都为此着急。“远来的和尚”——中国的一位哈尔滨年轻人郭青为他们念了一道新经:用制糖废弃的甘蔗渣烧炭,用这种炭取代木炭,解决全国民用燃料问题。肯尼亚盛产甘蔗,又是制糖大国,可用的甘蔗渣很多,这不失为一个最佳方案。另外,根据联合国关于气象变化的“东京大会协议”规定,大企业超额排放二氧化碳是要交补偿金的。而少伐一棵树就可以多吸收若干立方米的二氧化碳,那样就可以获得多排二氧化碳的补偿金。如果肯尼亚再不用木材烧炭而用废弃的甘蔗渣烧炭,不仅对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大有益处,而且也可以得到减排补偿,这是一个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好项目。郭青经过一番认真的调研和论证,形成了这个甘蔗渣烧炭的项目建议书,已上报肯尼亚政府,如果他们同意再报联合国环境署。对此郭青很有信心,如果这个项目批下来,或者在肯尼亚自办甘蔗炭厂,或者把这个项目有偿转让给别的企业。当然,办事效率不高和程序的烦琐,让他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但他深信功到自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