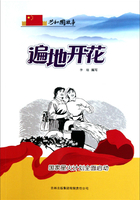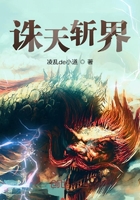——肯尼亚纪行
孟买—内罗毕—马赛马拉
离开闷热喧嚣的印度孟买,我们向炎热的赤道之下的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飞去。时间是2006年10月31日的0点30分。孟买是个不夜城,午夜时分,满城还是灯光璀璨,人声嘈杂。机场更是拥挤不堪,广场塞满了各种车辆,候机大厅里躺满了衣不遮体的人。孟买当局的领导人曾对来访问的上海客人说:“你们干得不错,将来有可能赶上我们!”印度人总愿意在中国人面前装大,可眼前这个乱糟糟的孟买国际机场和上海的浦东机场相比,实在让我们沮丧。不过孟买让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是不少,如敢与好莱坞抗衡的影城宝莱坞、富丽堂皇的七星级的泰姬宾馆、世界最大的贫民窟、臭气熏天的千人洗衣场……最后给我们留下美好印象的是,机场的工作人员很殷勤很客气,一位老员工一直把我们送到登机口,还跟着位女员工帮我们提行李。就服务行业来看,中国的硬件强,印度的软件好。有人说,印度人是被英国的殖民主义调教出来的。歪打正着的是,英语在印度很普及,这成为更多人走向世界的条件。
我们乘坐的是肯尼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将飞越浩瀚的印度洋,在东海岸登上非洲大陆。夜色如墨,舷窗外只有星光闪烁。我在地图上寻找肯尼亚的位置。它像一片锥形的叶子镶嵌在东非洲的海边,北靠埃塞俄比亚,西临乌干达,脚下就是坦桑尼亚。东非大裂谷纵贯南北,正好与头上的赤道相交,在肯尼亚形成了一个大十字架。因此受到上帝的关爱,他的恩泽让这58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阳光灿烂,雨水丰盈,河流密布,湖泊众多,森林成片,花开四季。更重要的是他让这里成了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这一秘密最早被达尔文发现了,1871年他在《人类起源》一书中预言:“人类始祖的化石将在非洲出现。”60年后,果然在肯尼亚发掘出250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因此,世界人类学界公认,非洲的肯尼亚就是“人类的摇篮”。
中国记协这次安排我们这帮老记大老远地跑到非洲,怕不是来访古寻根的吧?其实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硬邦邦的古人类头盖骨,而是欢蹦乱跳的动物。我们都知道肯尼亚是名享遐迩的“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不仅生长着火烈鸟、丹顶鹤、秃鹫、巨喙等奇禽,也生活着狮子、猎豹、河马、犀牛等猛兽,还有大象、羚羊、斑马等性情温顺的热带动物。听说我要去肯尼亚,在北京上中学的侄女贾天鸽还专门给我找了一盘记录非洲动物的VCD让我看。那动物自由生活的场景陪着我在这一万多米的高空入梦。
在我正坐着吉普车追赶草原上成群的角马时,突然被同伴叫醒,内罗毕到了。一阵凉爽的晨风让我从睡眼惺忪中清醒。没想到赤道之下的内罗毕一片清凉,全无孟买的酷热。这里地处1700米的高原,再加上森林覆盖和花草繁茂,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7.7度。马赛语“内罗毕”的意思就是“冰凉的水”,烈日炎炎如火烧的赤道之下,能感受一份清凉,内罗毕真是一个令人舒适惬意的城市。无怪乎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和人类居住中心都设在这个城市。
进了内罗毕城如同进了一座公园,给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树的高大和花的繁盛。那树未经修剪地立在道路两旁,枝干粗大,枝头上开着一串串的花朵,那花是紫罗兰色,连成一片,如同整个城市都飘浮在紫云的祥气之中。这感觉如同我在广州看到满城高大的如火把般的木棉树,在罗马看到家乡只能栽在花盆里的满街盛开着粉红色花朵的柳桃树。后来才知道那树花叫肯山蓝,可能是这个国家独有的。内罗毕的建筑都掩映在树荫之中,隐藏在花园里,哥特式的尖顶和墙面的花饰显示着它们的欧式风格。
内罗毕素有“东非小巴黎”和“阳光下的绿城”的美誉,我看后一个称号更名副其实。毕城无处不飞花,旧花将落新花开。那如花雨般纷纷落下的花瓣在肯山蓝树下铺上紫色的地毯,而旁边的绿篱内姹紫嫣红花团锦簇。和所有现代城市一样,内罗毕也是车水马龙,交通拥堵,从机场进城我们费了一个多小时。满眼的葱郁让我们消解了浑身的疲惫,而新江苏饭店的稀粥和小笼包子,让我们有了到家的感觉。在这个世界上有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就有中国饭店。以食为天的华人最善于经营餐饮。在内罗毕华人餐馆十多家,新江苏是家大店,大红门上宫灯高悬,楼上楼下雕梁画栋,墙上挂着国画和书法条幅。
大陆来的店主热情有加,中国驻肯尼亚使馆的文化参赞也来陪餐。边吃边寒暄。餐后,我们就上路了,我们的心思在下一站——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那里被称为“海明威的故乡”。1933年到1934年美国作家海明威在那里居住,并写下了《非洲的绿色群山》一书,生动地描写了那里鲜为人知的自然景观和土著人的生活,而那可爱的野生动物成了他书中的主人公。因为这本书的传播,让马赛人和这片野生动物的天堂为世人瞩目,各国的探险家、摄影家和动物爱好者蜂拥而至。而那部就在这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动物世界》更让马赛马拉风靡全世界。善于造势的肯尼亚人又声称这里就是海明威的故乡,就更让寰球的文学爱好者们趋之若鹜了。
神奇的马赛马拉在内罗毕西南方向300公里的苍茫草原上。路途漫漫,公路很差。以旅游为主业的肯尼亚为什么不把通往主要景区的公路修好?也许他们有意让你感受原生态的粗犷之美,因为当年海明威来时,连这样的路还没有呢!这回在国内经常以香车美女为伴的老总和名记们要吃苦了。还好,这帮住总统套房和乡间野店都安然的家伙们,在“万礅公里”的颠簸中还是笑语喧天的。不一会儿,我们便被东非大裂谷的壮丽景色吸引了。万里沟壑,横穿东非大地,壁立数百丈,沟底宽百里,这是地壳发怒的痕迹。地壳深处沸腾的岩浆引发了火山的爆发,凝固后便形成了谷上的高原、台地和锥形火山群,终年积雪的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就是它们永生的纪念碑。而谷地广阔的平原和一串串宁静的湖泊便是上天馈赠给人类和动物的家园。
与内罗毕的一派葱郁完全不同,我们奔跑在满眼秋黄的山地上,树不多,树上的叶子黄绿相间,那树多为针叶槐和仙人掌。地面上荒草萋萋,碎石遍地,有点像新疆戈壁滩的景色。这就是肯尼亚的稀树草原,是马赛人和众多动物的栖息地。
透过车窗,我看到了在荒原上孤独地走过的马赛男人,他们披着红底黑条的“束卡”,那是由两条布组成,一条围在腰间遮羞,一条搭在肩上,可遮挡风沙,也可擦汗。他们的手上都拿着一根像孙悟空金箍棒一样的木棍,那是他们赶牛的工具也是防身的武器。成年的马赛男子头上有精心编制的小辫儿,而女人是剃光头的,脖子套着金属的项圈,耳朵上悬挂饰物,被拉得很长。她们穿着像套头长袍式的“坎噶”。导游小邓指点着让我们看远处树林边上的马赛人的村落,那是由带刺的灌木围成的一个很大的圆形的篱笆。圈内靠篱笆建了一圈土房,中间为养牲畜的院子。这一座土围子住着四到八户马赛人家。他们过着由部落首领掌管的游牧生活。
马赛人是一个可尊敬的民族,他们放牧但不狩猎,他们只吃自己养的牛,喜欢喝牛血,但从来不吃野味,连鱼都不吃。他们相信万物是有灵的,不可侵犯。而牛是上天赏赐给他们的。他们甚至不耕种,因为那样会把大地弄脏。我们有些奇怪,到马赛马拉参观游览的人都坐在有金属栅栏保护的车上,马赛人却经常一个人走在野兽出没的山林里,为什么一点也害怕?小邓说,动物们都知道,那穿红袍的棕黑色皮肤的人是它们的朋友,已经几百年了,它们没有伤害朋友。人类和其他生灵互不伤害,相依为命,这正是马赛马拉能成为野生动物天堂的原因。为此我们应该向马赛人致敬!一位访问此地的白人作家诗云:
高贵的,
我发现
总是土著,
而无聊者
——移民。
经过大半天的奔波,我们一行终于在一片高大浓密的树林中的宾馆安营扎寨了。然后我们满身披挂地被装进吉普车的笼子里,向无际荒原驰去,不知是让我们去参观动物,还是让动物来参观我们。我们要比动物热情得多,举起长枪短炮,透过栅栏把镜头对准成群结队的野牛和角马,还有悠然走过的大象……动物很冷淡,看着我们的汽车,它们不跑也不躲,想干什么还干什么,憨傻的斑马连头也不抬地吃草,精灵的瞪羚,亮晶晶的小眼睛望着我们原地不动。只有树林中的长颈鹿伸着脖子远远地向我们张望。最可气的是那几只狒狒,竟停在我们的车前,望着我们又蹦又跳,难见的一次表演,当我们都对准镜头的时候,它们撒了一泡尿后扬长而去了。老记者们哭笑不得。
丹麦有位叫卡伦的女作家对此地野生动物的记述要比我生动,而她的描写被我们见证了。她和她写的书《走出非洲》,我在后面还会说到。她在书中是这样写的:
一个罕见的、株茎高大、长着斑斑巨大花朵的花族在缓缓地向前移动。 黄灿灿的苍穹下,一群野牛从晨雾中走来,摩肩接踵,一头挨着一头,这些黝黑、庞大、钢铁般的动物猛烈、水平地晃动着犄角,好像它们不是由远而近,而是正在你眼前被创造出来,待到完成,又立即跑开了。我还目睹过一群大象穿越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的情景。森林里,明媚的阳光透过茂密的匍匐植物斑斑点点地洒下来,大象悠然地迈着步子,仿佛它们在世界的尽头有什么约会似的。……我还不止一次地目睹长颈鹿成群结队地从旷野上经过。它们有着一种奇特、无与伦比的素雅美。它们好像不是一群动物,而是一个花族——
真是大开眼界,《动物世界》里的许多场面在我们的眼前重演了。小邓说,如果你们七月份再来,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野牛角马大迁徙的壮观场面,奔跑着的动物群如大河涌流般奔腾咆哮,整个草原上浓烟滚滚。每年大约有4万只斑马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高原迁徙而来,紧接着约80万只角马和其他蹄类动物也拥入马赛马拉草原。这里平时生存有50万只野生动物,大迁徙时能达到140万只。在领略了角马、野牛、大象、斑马、长颈鹿的神采之后,我们有些不满足,怎么没看到最凶猛的狮子和豹子呢?小邓说,它们都躲藏在草丛中睡觉呢。他马上用对讲机联系,然后他让司机掉转车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说那个方向发现了狮子。大约在几公里的路边真躺了一只狮子,它懒洋洋地眯缝着眼睛,就是不起来。有一个游人向它扔了个汽水瓶,正好打在它的身上,它忽地站起来,头上的毛都挓挲起来,然后向车上望去,好像在问:“这是谁干的?这么不懂规矩!”车上的游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那狮子又慢腾腾地走进草丛,我们仔细一看,那里卧着好几头狮子,都是那样慵懒的样子。导游对我们说,在这个动物世界里,越温顺的动物越活跃,越凶狠的动物越懒散。不过谁要侵犯了它们的领地,它们是一点也不客气的。有一个日本游客一时内急,下车后到树下方便,这时一只蹲在树上的豹子,突然蹿下,把那人后背抓得皮开肉绽,要不是抢救及时,真的没命了。很可惜,那一天,我们没有看到弱肉强食的场面。不过肯定要比哈尔滨东北虎园的老虎抓鸡惊险得多。那些野性退化的老虎演员,要送到马赛马拉草原,不是饿死也得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在玫瑰色的晚霞中,大象排着长队向天边走去,那镀着金边的剪影富有诗意。暮归的老记们疲惫的脸上也写满笑意。一下车,我们发现有几只狒狒竟在宾馆门口向我们招手,一时分不清是不是在我们的车前露丑的那几位。在这个花园宾馆里,狒狒、驼鸟、珍珠鸡是我们的“三陪”。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邂逅罗红
一夜沉睡在东非稀树草原深处的马拉辛格(狮子)宾馆,虽然狒狒叫春的声音有些凄厉,但并没影响困倦至极的我们酣然入梦。早上林子里百鸟合唱,几乎和叫早的马赛打更人一起把我们唤醒。这个山林里的别墅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更不能上网,这种脱离现代信息社会的生活,让我们进入最好的休闲状态。在这片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观日出日落,闻花香鸟鸣,倒头就睡,吃嘛嘛香,这是患现代城市病人的最好疗养院。
昨晚的一次美丽的邂逅,还让我们兴奋。曾经16次到非洲采风的摄影家罗红也住在这个宾馆里,我在北京侄女家看到的关于肯尼亚野生动物的摄影图像,就是罗红的作品,是侄女在“好利来”食品店得到的赠品,而罗红正是这家全国最大的烘焙食品连锁店的老板。这位1967年出生的四川雅安的小伙子的经历特别传奇。他17岁外出打工,在照相馆学徒,他挣得第一笔钱就买了一台理光牌相机,从此爱上摄影,并自己开了影楼。为了给母亲过生日,他跑遍全城没有买到称心的蛋糕,从此他下决心自己办一个像样的蛋糕店,经过十年的打拼,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蛋糕大王”,他在全国各大城市有一百多家“好利来”连锁店。他把挣来的钱更多地投入到他热爱的摄影事业上来,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又来到了非洲,更迷上了肯尼亚。中国驻肯尼亚的郭大使回国述职,在地铁站的展窗里看到了罗红在肯尼亚拍摄的野生动物的作品,大为惊喜。在他的安排下,罗红今年的6月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署举办了非洲保护野生动物的展览。这是中国摄影家第一次在联合国搞影展,反响强烈。这回罗红又一次来到马赛马拉,是为了给北京的展览再增加些作品。他以每天2600美元的价格租了一架直升机,要拍摄成群的动物在旱季的荒原上奔跑而烟尘滚滚的场面。
我们坐在宾馆的咖啡厅和罗红闲谈,披着红袍子的马赛人给我们表演,他们用手中的棍子点着地板,有节奏地哼唱,不断变换着队形,旋动着手中的棒子。那形式像武术又像歌舞的表演。表演者都是油黑的壮汉,没有一个女子。但我在罗红的画册中看到许多马赛女人的形象,都是袒胸露乳的,目光是那样清澈自然。罗红是走进她们的部落和村寨为她们摄影的,因为他是她们可信的朋友。表演时,罗红不时地和他们用马赛语打着招呼。
闲谈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罗红是这样狂热地热爱大自然、热爱原生态生活,更热爱野生动物。他立志用毕生的精力,为山川立照,为动物写实,旨在呼唤人类保护自然、爱护动物,因为大自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因为动物和人类血脉相连、唇齿相依。为此他可以洒尽千金,无怨无悔,这是他的挚爱,更是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