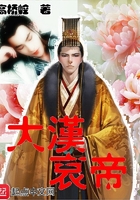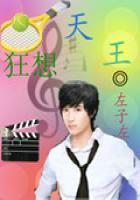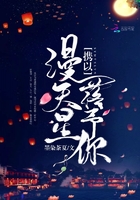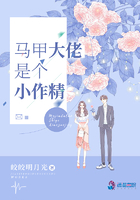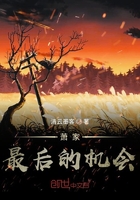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汉代农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先进的生产工具得到应用,修建了一批水利工程,粮食的产量有较大增长。商业贸易在汉代动荡起伏,总体趋向繁荣。商业和农业的关系错综复杂,汉代确立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影响及于千年。
■重农抑商
自战国时代起,关于农商关系的争论就已经开始。基于社会现实,诸子百家似取得一定的共识,就是重视农业,提倡“以农为本”;但对于工商业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建立在主观认知的基础之上,很多学者以为工商业的发展,不仅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也会造成社会风气的奢靡与堕落;而诸多工商业者四处流动,也大大威胁社会秩序的安定,不利于统一管理。法家一派便是此说的持有者。汉初沿袭秦朝已有的以重农抑商为主旨的经济理论。几位皇帝接连提倡“重农”,贬斥从事“末技”、“末业”的商人,如高祖禁止商人子穿丝织衣物,禁止其为官等。著名政论家贾谊、晁错也屡屡进言,认为农业为政务之本,应迫使“末技游食之民”从事农业生产。武帝时期,桑弘羊主持经济改革,体现的则是农商并重的思想。
“盐铁论会议”上,桑弘羊主张以农为本,但又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坚持盐铁官营。“贤良文学”派则与之针锋相对,主张农本商末,视盐铁官营为“崇末抑本”,倡利背义。此后历代对农、商关系的论争,基本上不出盐铁论会议所辩论的范围;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如“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由此确立其正统地位。
■农业成就
农业是支撑汉朝社会经济的基础,而“以农为本”国策的确立,更稳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经济体系。在汉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农业取得长足进步。汉朝农民掌握丰富的耕作知识,他们在施肥方法、选种标准和田间管理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铁器的进一步推广,二牛一人式耕作方法及播种工具—耧车等先进技术的发明,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也有重要意义。铁犁铧有了重大改进,领先欧洲千余年;二牛一人耕作技术,则一直沿用到近代。汉代兴修了诸多用于灌溉田亩、肥沃土地的水利工程,如武帝时期开凿了白渠、六辅渠等水渠,其他地区也纷纷兴修引黄河水或川谷山河之水用以灌溉的工程,对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量有重要意义;对黄河的治理,更是政府安定百姓,为百姓生产、生活提供保障的重要举措。武帝晚年让主管全国农业的搜粟都尉赵过,在关中地区推广试验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代田法”是将耕地分成圳(小沟)和垄,种子种在田中内生长,可以防风保墒;第二年将圳和垄颠倒过来,轮换利用,以利恢复地力。这种方法后来推广至西北边郡等风旱严重的黄土高原地带,取得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良好成效。
■商业发展
汉初“无为而治”政策的推行,对于推动经济的恢复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的复苏,都有重要意义。道路和运河的建设,车辆、舟船的普及和运输动力的开发,在推动交通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商业都会的繁荣和贸易的往来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商业都会大多位于交通便利之处,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商品的重要消费场所。当时北方的商业都会远比南方的发达,比较重要的如长安、洛阳、邯郸、宛等都在黄河以北。围绕这些城市,形成了几个商业兴旺发达的区域,而各区域间也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商业贸易关系。商贾是物品得以周流交通的中介,他们有的赀财千万,有的仅是小商小贩,差别很大。一般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肉类、水产、果菜等,市场上应有尽有。奢侈品贸易,如玳瑁、珠玑之类,是最为兴盛的商业活动,因为它们体小价高,便于携带,又受权贵富豪的喜爱,在贸易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武帝时期的“算缗”、“告缗”政策,对工商业打击较大,商业发展一度受阻。此后虽有所恢复,但已经大不如前。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及商品贸易也有飞速发展。
■《汜胜之书》与《四民月令》
古代中国以农业立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发展,使得农业技术的科学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等问题提上日程,从而推动具有总结性质的农学著作的产生,著名的有《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汜胜之书》,又名《汜胜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个人(汜胜之,一作汜胜)独立撰写的农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学专著。该书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技术,提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的耕作栽培原则,研究总结了作物栽培的综合因素;针对不同作物的特性与要求,提出了不同栽培方法和措施,为中国传统农学的农作物栽培理论奠定了基础。《汜胜之书》开创了中国农书写作的先河,其写作体例也成为中国传统农书的重要范本。《四民月令》的作者是东汉的崔。这部书按一年十二个月和节气先后,安排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以及手工业和商业经营等事项。《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如耕地、催芽、播种、锄耘、收获、贮藏以及果树、林木的经营等农业生产技术,反映了东汉前期的农业生产概况。书中最早记载了“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压条繁殖法。《四民月令》一书对各月的安排次序比较合理细致,不失为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和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