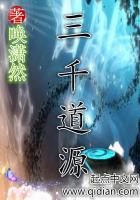“要妈妈……”虽然仅仅嘴唇无声的翕动,却清晰得让他们二人都为之一震。因为羞愧或者喜悦,终于从恐惧中挣脱的王宣流下滚烫的热泪,一直滴到郝青蓝手上。
也许,郝青蓝的泪更先于王宣——不用再旁敲侧击地求证了,也不必再自欺欺人地狡辩了,一切都昭然若揭:他是恋母的,而自己,只是一个以假乱真的替代品。
虽然此前有过郝青白的警告,并且她自己也有过朦胧的预感,但真的掀开这真实的面纱,即使再通情达理、再有自知之明,郝青蓝还是感到巨大的失落,现在得承认了吧,花费那么多心血、承担那么多的嘲讽、抱有那么多的幻想,到头来,还是应了他们的预言:换汤不换药,第三个笑料而已。
郝青蓝现在感到多么寒冷呀,她一个人在生命这个辽阔的海上航行了这么多年,总以为前面是可以憩息的小岛,却只是从一个冰山到另一个冰山,她感到自己真的永远到不了尽头了,她这辈子都不会踏上那座阳光明媚、莺飞草长的岛屿了。
郝青蓝忽然觉得自己慢慢飘了起来,一直飞身到半空中,远远地俯看着自己和王宣。无辜的蛋糕被推到一边,刚刚吹灭的蜡烛升起了一股淡淡的蓝烟,散发出石蜡特有的干焦味儿;对坐的男女宛若一座雕塑,像落水的人那样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像是准备同生共死,或是一并坠入深海,或者同时得到救赎……
那么,现在该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该如何度过?外面的人们还是走啊说啊……他们怎么都知道应该往哪里去呢……
从恐惧的泥淖里爬了出来,王宣终于恢复了他的感知。从郝青蓝的脸色,他知道她想到了什么。
这个敏感却又迟钝的孩子终于开口了,他一开口又是实话:“青蓝,你不要误会。我对你……不仅仅是因为……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离不开你,想永远呆在你身边,跟你说话……你不要生气,不要想得太多……你以前不是说过,只要在一起,便足够……”
王宣的台词只是另一种佐证,他对她的依恋,像奶汁那样浓厚天真,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不过,是依恋还是爱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都合理,她是不可能拒绝的,就像一个母亲不可能拒绝自己的孩子;也许,命中注定,她本来就该是个母性的情人……
姚一红在自己的小屋挂了一面墙的照片,是她这些年来各个时期富有代表性的单人照,有风景照、有工作照、有居家照,有的甚至只是略显呆板的证件照。照片里的自己以各种姿势各种表情穿过时光的屏障从各个度看着现在的姚一红——一群姚一红陪伴着姚一红,姚一红站在一群姚一红中间——这情景的画外音传递着一种鲜明的令人同情的孤独。
但姚一红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她一向有着解剖现实的冷静和勇气,她坐在照片墙下边,一面看着从前的自己,一面直面当前的问题和症结。
在与郝青白的那顿午餐并共同聆听了《流浪者之歌》之后,她终于开始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信号:她的爱情之舟遭遇了搁浅之虞。她丝毫不怀疑郝青白对自己的爱,但爱了又如何,他在爱情观上是个逃避主义者、不作为者、柏拉图主义者;他不可能以丈夫的名义成为她后半生的情爱对象。她的计划现在碰到了意料之外的问题,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上,另一个主人公与她的想法背道而驰。
变化总比计划快;办法总比困难多。姚一红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她真的感到了无助,这些照片,又不会说话,又不能给她拿主意……她该怎么办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她能停得下来吗?为什么,她抛掉一切所追寻的这个爱情,却让她陷入如此的尴尬境地?难道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爱?
天色晚了,晚饭还没有准备。但姚一红不想动了,她甚至都没有开灯,她就那么一直坐着,任由浓重的暮色把她淹没。
而王向阳,就是在这个时候敲响了姚一红的门,他拎着一大罐刚烧好的母鸡汤,穿过小半个城市,站到了姚一红的门前。
前面这些日子,王向阳一直在做一件事:寻找姚一红的新住处。对自己的新家,姚一红的保密可谓无懈可击,就是对心爱的儿子王宣,她也照样只字不漏。她可以跟王向阳通电话,相互问候,变天了还会打电话回去提醒王向阳关阳台窗户。但在空间上,她却严格而刻意地保持了生硬的距离,以杜绝可能的不速之访。
但王向阳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实干家!大海捞针他也不怕。在排除法、推测法、跟踪法的相继失败之后,他终于依靠网络搜索这一新手段从一个网上书店的交易记录里找到了姚一红的名字,然后,又费劲周折、通过若干民间的渠道从配货员那里打听到了姚一红的准确住址。
他还没有马上告诉儿子,因为他得先探探姚一红的底,然后再决定用什么方式让王宣去见自己的母亲。
这些四处奔波的日子里,做父亲的还睁着另一只眼关注着王宣。王向阳是个粗砺的男人,但在儿子身上,他心细如发,他注意到了王宣的怪异之处,如提前回家四处乱翻、像孩子那样坚持开着灯睡觉、对着姚一红的旧东西爱不释手等等……
王宣这样让王向阳既心疼又生气,他不喜欢儿子在情感上如此脆弱,这太不像个男子汉了,太不像王向阳的种子了,姚一红离家独居,最失落的应该是谁?当然是做父亲的了,可是看看我王向阳,尽管想和她睡觉、想听她骂人、想看她的凶样都想得快要发疯了,不还是活得好好的,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天天精神抖擞地等着姚一红回来!王宣这样算怎么回事儿,真让人看不上,说到底,这还是姚一红的错,从小给王宣那么些多愁善感的渲染,听冗长古怪的音乐,还去看那十足娘娘腔的昆剧……现在好了,她一甩手就走了,都不知道可怜的孩子陷入思念的泥淖……
在去找姚一红之前,王向阳精心地烧了一锅母鸡汤,并在里面加了姚一红最喜欢的笋干和枸杞,又到市场上挑了最新鲜的茄子青椒土豆,拿出看家手艺,做了两个清清爽爽的小炒放到双层饭盒里一并带上——礼多人不怪,有这两样东西在手,王向阳的底气就足了。但在去往姚一红新居的路上,王向阳还是有些踌蹰,这样贸然地找上门去,姚一红准会皱着眉头连声训斥、说不定连门都不让进,但是没关系,王向阳劝自己,即使一句话都说不上也没关系,只要姚一红喝点鸡汤吃口小炒,他就无上满足了。
对于自己的厨艺,王向阳是很自信的。结婚这么些年,只要不出差,家里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他一手采买操刀,八平方米的厨房就像是他的小小舞台一样,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主角和明星的感觉,每一顿饭菜,哪怕只是简简单单三碗盖交凉面,都会赢来妻子及儿子的真心赞叹。最好玩的是,有时姚一红刚刚挑起眉毛训斥过自己的,还关起门来到房里生闷气,但是,等到五颜六色、香气四溢的饭菜一上桌,儿子又装着小心翼翼的样子去敲门,她却好像早就在等着了似的自己就开了门坐到餐桌边,前嫌尽释,拿起筷子就吃起来,并且还饶有兴趣地评头论足——想到平常的那些家庭小景,王向阳又是心酸又是期望,时过境迁,不知往日的技法今天是否同样有效。
姚一红听到敲门声吃了一大惊:这里的地址,她只给了郝青白一个人,难道他真的来了?他改变主意了?或者,她听错了,因为渴望而出现了幻听?
不是幻听,敲门声不紧不慢,像在试一面鼓似的。姚一红连忙开了灯,出自本能地照了照镜子,以最快的速度加了一点口红,再打量了一下屋子——然后,她才走到门口:“谁呀?”
“一红,是我。”王向阳激动坏了,妻子现在跟自己就一门之隔呀!他简直体味到一种类似初恋的新鲜劲儿!
姚一红听出了丈夫的声音,她在心里冷笑了一下,不准备开门,可是她的手却背叛了她的意志毫不犹豫地扭开了门锁。
“一红,对不起……我过来看看……主要是不放心,怕你没啥好吃的……喏,趁热吃点儿,我打车过来的,还热乎着呢……”王向阳有些莫名的紧张,都不敢看妻子了,只自顾着把汤呀菜呀的往桌上放,像要把姚一红对自己的注意力全部移到菜上似的,又到厨房里张罗着用热水烫净了碗筷拿出来摆好:“吃吧,趁热吃……”
鸡汤的浓香、小炒的清香立刻在小小的两室居里弥漫开来,一直缭绕到墙上的那些照片上面,好像在邀请所有的姚一红都来享用似的。
王向阳这一招真的灵了。这个时候,姚一红倒正好是饿了,这些菜又正好是姚一红最最喜欢的,有什么好推托的呢?王向阳又不是外人。姚一红都忘了她方才酝酿好的一堆责问了:怎么找到这儿的?来干吗的?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这算什么意思?现在通讯这么方便,难道有什么事非得见面不可?等等,姚一红把这些全都扔到一边儿,她不客气地坐到王向阳对面,大吃起来,偶尔还客观地夸奖一两句。
现在的场景跟以前的有一幕有点儿相象,还记得吗?姚一红约着王向阳出来谈离婚的那顿晚餐——不过,那一次是做丈夫的胃口大开,而这次,换成妻子了。不知姚一红是否也有些触景生情了,还是吃了别人的嘴软,还是她今晚本来就需要一次情感的发泄,在心满意足地喝下最后一小碗鸡汤之后,姚一红推开碗筷,竟然拉开架势跟王向阳谈起话来。
“……唉。”她长长的叹了口气。“不知道,我现在真的搞不懂,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向阳,我一直,都还没问过你,我倒也说说,你心目中的爱究竟是什么?”姚一红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盯着王向阳。
从恋爱到结婚这么些年,妻子从来没有如此正经八百地跟自己讨论过情感话题呢,这绝对不仅仅是那锅鸡汤的功效,而是——姚一红开始对自己另眼相看了,她一定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一阵成功的喜悦漫过心头,但王向阳脸上却极为平静乃至郑重,他没有马上开口,而是在脑中进行着紧张的考虑,他想组织好一个深刻却又通俗的答案,既要表达出自己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又要符合姚一红的思维模式:“这个,我认为,我觉得……”
还没等王向阳结结巴巴地说完一句话呢,姚一红却自言自语地打断了他:“唉,最近我就在想,真正的爱,其实就是忍让、退缩与妥协,总之,是没了自己,忘了自己,像个最软弱最老实最可欺的呆子那样,不要面子,不要名声,不要好处,全都由着对方……”姚一红的眼神有些虚起来,从王向阳的头顶上穿过去,一直穿出这间屋子,穿到大街上,飞到一个王向阳永远猜不到的那个人心里——姚一红这话本来是想跟郝青白说的,可是他不来,来的是王向阳,那怎么办呢,谁来就跟谁说说罢,要不然,她会憋坏的,她得替自己的爱情找点儿理论根据呀,要不然,她下面怎么过呢。
妻子的声音轻得如同床边细语,在王向阳听来却简直像耳边惊雷:她说得太对了太准确了,好像一下子钻到自己心里似的,原来她早就知道,自己是在这样爱着她……王向阳喃喃地点着头表示同意,一边几乎都要流下泪来了,行了,只要姚一红知道自己的这份心,就是再多吃点苦再多折腾些花样又怎么样!
“……想明白了才知道,向阳啊,瞧我以前在你面前的那份劲儿,那样趾高气扬、专横跋扈的,整天冷嘲热讽,那算什么呢,可笑,跟真正的爱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话虽这么说,姚一红却还是看着虚无的某处,好像她只是在客观地分析一篇文章似的,并无任何内疚检讨之意。
尽管如此,王向阳还是大大的感到了安慰和温暖,形势真是一片大好,当然,他的姿态还是底得不能再底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都习惯了,觉得挺好……”
“老实说,原来我提出要分手,心里还有些不舍不忍什么的,也怕自己会做错事,可是,现在,经过一些事情,有了比较,我才敢确定,我离开你,是正确的。”姚一红终于看了看王向阳,心平气和的,带着一点俯就的,像对文章的作者说:很遗憾,这篇文章本刊不能采用。
王向阳这下子懵了,没想到,说了半天,她说的是她自己,她根本没想到他,唉呀,姚一红啊姚一红,你怎么会这样看问题呢!王向阳现在什么不考虑了,什么措词什么语气,或者姚一红会不会生气,他涨红了脸几乎脱口而出:“可是,一红,我对你,就是你说的那种爱呀,忍让、退缩与妥协,最软弱最老实最可欺,不要面子,不要名声,不要好处,全都由着对方……一红,你想想看,我对你不就是那样的,你怎么能说,你离开我是正确的呢,你把我的爱放到哪里去呢?”
“可是,我呢,如果顺了你,我的爱又要放到哪里去呢……”姚一红下意识地反驳到,说到一半,她怔住了,她终于意识到王向阳的处境和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他岂不是和自己同病相怜——他们的症状都一样:因为爱了,在被爱的人面前,他们就低下去了。
这对夫妻,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谈到情感,他们在认识和体验上完全一致,可是他们的心意和愿望却完全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