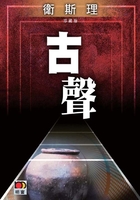“营养液……什么营养液?”老者好像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儿。
“营养液嘛……就是根据水培花卉的种类配方……”谢霓见景焕老半天不做声,只好结结巴巴地替她回答,“把什么硝酸钠啦、氧化钾啦、过磷酸钙啦等等,按一定的比例配在一起……您看,这棵用营养液培养的仙客来,株高都有四十厘米了,一年可以开一百三十朵花呢!”
老者拈着银须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真是活到老,学不了哦!……欢迎你常常来!”
这后一句话他是对着景焕一人说的,而景焕却又有些听而不闻的样子,弄得我和谢霓很尴尬。
“这棵仙客来,先留在我这儿,下个月,你来取,好吗?”老者又对景焕说。
“行行行,这花就先放您这儿吧!”谢霓慷慨惯了,生怕景焕说出什么小气的话来,急忙替她答应着。
“当然,我也要给你看看我的花。”老者把那个开门的老人叫了来,略一示意,那老人便掀开花房里面的珠帘,端出一盆昙花来。
这昙花被精心地盘成了一种扇面形。碧的叶,像绿翡翠似的发亮,托着两朵极鲜嫩美丽的昙花,玉碗似的,晶莹透明。
景焕的眼睛发亮了。她轻盈地跑上去,对着昙花仔细观察。
“昙花……怎么会在白天开呢?”景焕讷讷地自言自语。
老者朗声大笑了。“我不仅会使夜晚的花白天开放,而且会使春季的花在冬天开放,冬天的花开在夏天……哈哈哈……你认为这些是不可思议的吗?……”
“不。我认为,什么都是可以实现的。”景焕突然一本正经地说。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补了一句:“只要,只要是自由的。”
我和谢霓面面相觑。但老者显然听懂了这句话,睁开一双睿智的眼睛,和善地望着景焕:“还应当补充一句:那么,一切就都是自由的。对吗?”
景焕的眼睛变成了两团明亮的星光,“您……您见过弧光吗?”她突然问。我真担心她突然又犯病。
但老者并未感到惊奇,他从容地微笑着:“没有见过。但是它可能存在的。一切都是可能存在的。”
“下个月,我一定来。”景焕突然像个未成年的小女孩那样天真地笑着。
但是景焕失信了。“下个月”,她没有能够去。
“下个月”是二月,正是一年一度的春节。景焕加倍地忙碌起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又开始对插花艺术感兴趣了。她先是搞一些小型插花,利用空的香水瓶子,酒杯,贝壳等等,设计成各种小巧玲珑的造型。比如,插上一片造型怪异的小叶子,或者,几株婆娑淡雅的葭草。虽极简单,然而颇有趣味。后来,她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她用一些化学药品把鲜花制成可以长久保存的干花,利用竹子,秫秸秆,麦穗,石子,藤子等等可以随手拈来的材料,设计成一些造型优雅的大型插花。
春节那天,谢霓家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极精美的礼物——插花。
谢霓得到的插花是由马蹄莲和郁金香制成的干花组成的,这雪白和鲜红的色彩放在一起,显得格外热烈和明亮,用来插花的器皿是一个水绿色的长颈玻璃瓶,谢霓高兴得手举瓶子,在原地旋了好几个圈儿。
连一向冷漠、矜持的谢虹也忍不住惊喜地叫起来——清晨一觉醒来,她发现自己的床头柜上摆着一架十分别致的插花——一只白瓷的大雪花膏瓶子里,别出心裁地插着一束用加工以后变成雪白的秫秸弯成的凤尾,两棵碧绿的麦穗和一束叫不上名字来的白色小花,洋洋洒洒的,就像是清晨的一片乳白色的雾。和送给谢霓的插花那明亮热烈的风格相反,这风格是纤秀、典雅。
我来到谢霓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正聚在谢伯伯和文波阿姨的卧室里,欣赏景焕的杰作——一架大型插花。
一个扁圆形的钧瓷瓶,变幻着浅蓝、淡绿、深紫的色彩。上面的插花像是一丛长得极茂的乳白色的珊瑚。细细一看,才知道是经过药品处理后的藤萝,被盘成了珊瑚状。“珊瑚”后面是几根长长的孔雀尾羽,把整座插花点缀得很华贵。前面是两朵玉碗似的昙花,和那天在老者家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这东西要是摆在工艺美术商店出售,准得打破脑袋。”谢霓抱着膀子,得出结论。
“倒是有点日本花道的那个味道呢。你说呢。阿波?”谢伯伯对一切事物做出评价之前,总是要征求夫人的意见。
文波不置可否地微笑着,眼睛不离这座插花,看得出,她十分满意。
“对了,妈妈今天不是有日本客人吗?正好可以叫人家评价评价。”谢虹闪着机灵的大眼睛,挽着妈妈的手臂。接着,她突然向我嫣然一笑:“柳锴,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卖上个千儿八百不成问题!”我也一笑。
“真是钻钱眼的脑袋!”
“既然是商品社会,那么谁也离不开孔方兄。”说实话,我很讨厌在生活上穷奢极侈而又自命清高的人,特别是这种话从谢虹嘴里说出来,就更叫人反感。我决定趁机抒发一下我的见解:“依我看,不如和哪个工艺美术公司挂上钩——反正现在形形色色的民办公司多得很。和他们签好合同,然后由他们代销,利润分成。可以先试销一下嘛!如果这笔买卖真做成了,解决的不仅仅是景焕的衣食,她的精神世界也会跟着解放——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被社会所需要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精神病的最好的治疗方法。”
“哎,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试试。”谢霓兴奋起来。
我讲话的时候已经发现,谢伯伯和文波阿姨颇有些不悦之色了。这时,文波望着小女儿,颇不以为然地说:“小霓,什么事情不要脑袋瓜一热就讲话。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是不会做买卖。什么公司不公司的,不要赶那个时髦。”
谢霓悄悄拽了一下我的袖子。走出房间后,她悄声对我说:“别理他们,咱们自己帮她联系!”
谁知道,就在这天的下午,由于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景焕永远走出了这个家庭的大门。
“糟了!景焕走了!”
午饭后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谢霓便气急败坏地敲开了我的房门。她来我家次数虽不多,却远比我在她家随便——这可能和我家的家庭气氛有关。妈妈极喜欢她,每次她来,都倾家中所有,为她烧一顿可口的饭菜;而谢霓,也从不辜负我妈妈的一片心意,每次总是风卷残云般地把饭菜一扫而光,一边还摆出品尝大师的风度,发出些具有权威性的评论。我十分相信谢霓评论的真实性,因为在这里,她可以换换口味,吃到一些在她家里永远也吃不到的新鲜玉米面、小米,甚至野菜、野果。
“怎么了?”我一边披上棉袄一边问,仍旧迷迷瞪瞪的。
“都怪他们!都怪他们!”谢霓急得直跺脚,“走走走!我们去找她!路上我再跟你说!”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拽得长长的,变了形,像一幅抽象派的画。一路上,谢霓断断续续地讲起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中饭时候,两位日本客人来访。看到景焕所做的插花,十分感兴趣,执意要见见作者。
“她们对那座插花的评价可高了,”谢霓一边蹬车,一边把飘到脸上的发丝掠开去,“她们两个虽说都是妈妈的同行,但都懂得花道。她们说那座插花色彩鲜明而不失协调,造型怪异而不失典雅,而且明暗对比,动静结合,是插花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可妈妈不知为什么,不愿意让景焕出来见她们,甚至不愿让她们知道作者是谁,当时给了她们这样一种错觉,好像作者是我和谢虹其中的一个似的。后来其中一位发出邀请,说无论插花作者是哪位小姐,都竭诚欢迎她去日本做客,并且说,一切费用都由她们包了,还保证提供与日本花道同行切磋技艺的机会,等等等等,结果妈妈的回答很是含糊其辞。临走,那两位女士还留下了一份小礼物,说是请妈妈一定转交作者——那是一只手持花束,做得很精美的日本桃偶。谢虹一看就喜欢上了,央告妈妈先让她在房间里摆两天。妈妈对此要求不置可否,却反过来对谢虹提了个要求,要求她去向景焕拜师学习插花,并且要尽快学会其中技巧……”
“行了,你别说了。”我打断了她的话。她看看我。两人心照不宣地默默地蹬着车。
“其实,我妈妈那个人并不坏。”她忽然说。
“当然。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女儿比别人的强,这太可以理解了。……那么,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更不可思议了。我一直没对你讲,为了了解景焕的过去,我和她以前的男朋友夏宗华建立了联系,打了几次交道以后,我发现这个人很自私,而且……在心理生理方面都有些变态——这可能和他至今独身有关系。我也摸清了一点他对景焕犯病所起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但不知为什么,尽管我很想了解他和景焕关系的全部底细,然而我的这种好奇心却战胜不了对他的一种厌恶感,我对他这个人有一种本能的防范。懂吗?我指的并不是那种侵袭,他骨子里很胆小,做不出什么事情来,而我也决不给他这种机会,这个我拿得很准。我指的是另一种侵袭——一种破坏你内心平静的侵袭,一种你明明厌恶却还要为了某种原因不得不敷衍的侵袭。为了摆脱这个,我不再去找他了解景焕的情况了。可是我没想到他竟敢不经允许地打上门来,更没想到,他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谢虹给迷住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谢虹——那只高傲的、矫情的天鹅,那个把世界上一切男人都踩在脚下的公主!
“是啊,昨天我听到谢虹的宣布时也很吃惊——”
“宣布?”
“嗯。昨天晚饭之前,谢虹向全家郑重宣布,夏宗华是她的男朋友——未婚夫!”
“当时景焕在场吗?”
“不在。日本客人走后,她的神色一直不对头,我猜到,客人和妈妈的那番谈话是被她听到了,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哄她,拉她出去听音乐,还从谢虹那儿把日本娃娃抢过来给了她。到晚饭时候,她总算好些了。听到谢虹的宣布之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决不能让景焕见到夏宗华!可是……事情就赶得那么巧!我刚刚把景焕哄出花园,想陪她到外面去吃点东西的时候,谢虹把夏宗华拉去赏花——正好撞了个对脸儿!”
“我的上帝!”
“景焕一见到夏宗华,就死死地盯住了他,那种眼神——唉,我的天,我这辈子也没在哪个人的眼睛里找到过!她的脸色变得灰白灰白,奇怪的是,夏宗华似乎很害怕,当时他唧唧缩缩地说了一句:‘你好!’不明戏的只有谢虹,她还挺得意地向景焕介绍说:‘这是我的男朋友!’景焕当时的表情很奇怪。她好像微微一笑。可那一笑真可怕,就像是《百慕大三角洲的魔鬼》里那个嗜血的布娃娃似的……”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当天晚上,景焕就失踪了。最糟糕的是,她可能认为我也是合谋者,把她骗出花园,好让夏宗华和谢虹来尽兴地赏花……唉,总之完了,这次找她一定得由你出面!……”
第四天,我们在肿瘤医院的肝科男病房找到了景焕。
景宏存在这里住院。那躺在床上的一动不动的瘦老头儿,假如不是那双灰色的眼睛还有些生气,我会把他认作一具死尸。这就是那个曾在五十年代声名赫赫的景宏存吗?
景焕显然是吃了一惊。接着,露出一种厌烦的表情,她显然是不愿让我们来打扰她。她正在给父亲喂吃的。一个橙黄色的鹅蛋柑,被她很仔细地剖开了,放在一个小碟子里,然后用一只不锈钢的小调羹把柑子一瓣瓣地放进父亲嘴里。在她做这一切的时候,显得那样熟练和轻巧,让人看了很舒服。
“景焕,你父亲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谢霓走过去,很动情地握住她的手,“真把我们急坏了,这几天,你是怎么过的?”
景焕慢慢地抽出自己的手,不吭一声。
“景焕,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谢霓轻声地说,我还从没见过她对谁态度那么诚恳,“我想我以后会跟你解释清楚的,希望你给我机会。”
景焕仍是一语不发。唇边,又出现了那种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在这种情况下,谢霓只好采取暂时回避的策略,由我单独和景焕打交道。
我遵照谢霓的旨意,每天去肿瘤医院。然后把景焕一天中的全部表现记录下来。景焕的情绪曲线起伏很平缓。她每天陪着父亲,似乎生活得很有规律,她尽心尽力地侍奉着父亲,病房里其他的病人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说景宏存有个孝顺的女儿。
一天雪后,我照例来到医院,一眼便望见景焕一个人推着轮椅,正把景宏存从医院后门那个用洋灰抹成的斜坡上推下来。坡度挺陡,上面被轧实了的落雪又格外滑,她两只手死命地拽着轮椅把,全身后仰,但即使这样,也无法控制轮椅下滑的速度。她像片被飓风卷着的小树叶子,不由自主地向下坠落着。
我跑过去抓住了轮椅的扶手。
她仰脸看我,虽然是瞬间,但我却很难忘记那眼神。那双眼睛变成了两团迷人的星光,美丽而神秘。里面藏了数不清的无法言传的意义。我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起把她父亲推到医院后面的小花园里。
这是座多年失修的花园,荒草长了老高。石雕的残垣上堆满了残雪。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景焕仍戴着那顶鱼白色的旧毛线帽,苍白的瘦脸在阳光下变得半透明了。
她细心地把盖在景宏存腿上的小被子叠好,垫在他的后腰上。我扶他下了轮椅,他虽然极瘦,但却颇沉重,他仰脸儿坐在那把绿漆斑驳的长椅上。混浊的眼珠儿不停地转来转去。但我不相信他是在看现实中的东西。我看着他,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死亡实际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停止呼吸之前,身体的各部分器官早就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
我奇怪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会被耗干成这样。
景焕的兴致倒是格外高。她一会儿折一根枯枝,一会儿拣几粒石子,忙个不停。末了儿,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父亲轮椅的底座里,又从底座那儿拿出了一个小小的肥皂盒似的东西。
“爸,我给你表演个小节目吧?”她的眼睛望着父亲,我却觉得她是在对我说话。
她打开那个肥皂盒,那里面是泡好的肥皂水和一支细细的蜡管。
她吹起了肥皂泡!有多少年没见过这玩艺儿了!大的、闪亮的、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彩色灯笼似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她鼓着腮帮子,好像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太阳暖融融地照着,树上落下的雪粉像蒲公英的绒毛似的,到处飞舞。
景宏存像是恢复了一丝生气。那双灰蒙蒙的眼睛定定地望着一个个闪亮的肥皂泡,竟慢慢湿润了。
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午。一个扎着红蝴蝶结的小姑娘,也是这样地向天空吹起串串彩色的肥皂泡。一个个亮晶晶的,在蓝天里像星星似的发着光。那时候的天很蓝。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纯净的蓝宝石色了,大约是空气污染的缘故吧。
“喂,帮帮忙,帮帮忙……”她拼命举着两条细瘦的胳臂,向上赶着一个正在坠落的肥皂泡,累得满脸发红。我不由自主地受她情绪感染,竟真的帮她赶起来。那个很大的、亮晶晶的肥皂泡,在轻微的气流中开始慢慢上升,反映着各种虹彩。
“轻点儿,轻点儿……”
她的认真样子令我好笑。但我却不忍拂去她的热情。就像是大人们永远不会在孩子们面前戳穿童话的秘密一样。
还是把圣诞老人的糖果留在她的鞋子里吧,我想。
但这个硕大的肥皂泡终于还是碎了。
她舒了口气,看看我,看看她的父亲,又举起小塑料管。
终于,有几个肥皂泡挂在雪松的枝条上面了。
“爸爸,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她突然有点羞怯地望着父亲。
一棵美丽的圣诞树。但那彩色的“灯泡”在阳光下很快就消逝了。
“我看到了。懂了。”突然,景宏存的嗓子里发出一种低哑的喉音。他一直出神似的看着那个最大、最漂亮的肥皂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