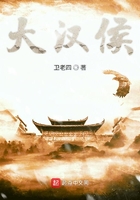放牛
那个年代,牛是农民耕作最主要的役畜,也是许多人家极重要的经济来源。家境稍好的,都有一两头牛。放牛的人自然也多—或是丧失劳力的老人、残疾人,或是穷苦人家的小孩。无学可上的父母,跟许多同龄人一样,也放起牛来。
每每聆听父母讲述小时候放牛的生涯,总是感慨系之,唏嘘不已。
父母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生不逢时,其命运可想而知。
先说父亲的放牛生涯。
父亲的生父是个赌鬼(恕我无礼),居然把10岁的父亲卖了做赌资。
父亲的养父,即本人的爷爷,虽也赌博,但相对理智,仍顾家,只是被风气所染,加之有婚无育,无所指望,未能免俗罢了。而他呢,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但看重读书;疼爱小孩也是有名的,父亲没来几天,就将其带往垄面塆的一位叫雍庚的私塾先生家里,恳求收为学生。后因人数太少,开不成学。那个年代,牛是农民耕作最主要的役畜,也是许多人家极重要的经济来源。家境稍好的,都有一两头牛。放牛的人自然也多—或是丧失劳力的老人、残疾人,或是穷苦人家的小孩。无学可上的父母,跟许多同龄人一样,也放起牛来。
第一年,父亲到双树下,给阿举放一头母牛。工钱为通价,即放一头牛一年,牛主给一担干谷、一担番薯米。古诗画里虽有牧童横笛牛背优哉游哉的描写,其实,放牛囝几乎是享受不到这种快乐的—哪位牛主会允许其骑于牛背作乐?父亲大多放牛于厝边附近的路旁、水圳和田塍。早上放出,晚上牵回。中午有时牵回,有时拴于野外—当然是靠近人家的地方。因为常有老虎、天狗、黄猺出没,袭击牛羊。最常放牛的地方,当属附近的油茶林,内有许多牛们爱吃的草,也是放牛囝寻欢的迷宫。若有伴,就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若无伴,就爬油茶树,当一只栖息的小鸟,或闭目养神,或跟远处放牛的人对唱山歌。油茶成熟季节,油茶林里的草被铲除,不高兴的是牛,最高兴的是放牛囝—可把牛放于附近,自己学做斑鸠,悄悄钻进油茶林,迅速捡些茶籽—并不贪多,一两抔,装满口袋就够了。等到回家时,跑去杂货铺,兑换糕点、瓜子或花生;边走边吃,好不惬意。只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父亲吃瓜子、花生却也如此,真是闻所未闻。瓜子虽不饱满,但其表面的盐花颇有味道,撒几粒入嘴,慢咀细嚼,直至无味,连壳咬细,吞下。吃花生亦然,一概舍不得皮壳。山花烂漫的日子,野果成熟的日子,桃软李红的日子,花生结荚的日子,番薯落地的日子,放牛囝的乐趣会更多些。而能给父亲带来欢乐的,仅有山花、野果。父亲老实,对别人栽种的东西,仅有觊觎之心,绝无偷窃之胆。然而,一天傍晚,父亲刚到家,侨庚、矮二兄弟,就像传说中的恶鬼“高哥、矮八”,气势汹汹而来,侨庚攥着一把软蔫蔫的花生藤,矮二拎着一串麻绳,不问青红皂白,恶声恶气地对爷爷说:“要吊你那死囝!”爷爷莫名其妙,惊讶地问:“他怎么啦?”侨庚一边抖动手中的花生藤,一边妄言:“不要吃青草假甜,你还不晓得你那死囝做了什么坏事?”爷爷满腹狐疑:“他偷拔花生?你们亲眼看见?”侨庚一口咬定:“还要亲眼看见?整个下午,就你那死囝放牛经过花生地,不是他偷拔的,难道还是鬼?”爷爷喊出躲在厨房角落里觳觫不已的父亲,厉声质问:“你到底有没有偷拔花生?”父亲怯怯地说:“没有。”爷爷又问:“当真没有?”父亲紧咬嘴唇,刚毅地点了点头。爷爷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诬赖,要吊人,那就吊我吧。”不等爷爷话音落下,矮二就挥起麻绳,冲过来,当着父亲的头掼下,幸好被爷爷的手臂挡住。武功高强的爷爷随即拉开捍卫的架势。侨庚和矮二见情势不妙,悻然退去。翌日,真相大白:前一天下午,父亲牵牛路过那花生地后,有个叫密庚的小孩(后来成了我的舅舅)去那里偷拔了几丛花生。密庚的父亲当时是保长,掌握生死予夺之权。侨庚和矮二能不噤若寒蝉?事后,他们不来道歉半声,爷爷也没去理论一句。
第二年,父亲到大温洋,给肥三放一头牯牛。牛个头不大,双角张而曲,觺而壮,天生一副好斗相。它从不服输,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每次出去,别说遇上其他牛—无论是牯的、母的,还是大的、小的,即使远远望见半缕牛影,隐约听到一声哞叫,也会昂起头,睩起眼睛,竖起耳朵,撅起鼻翼,打起响鼻,尥起蹶子,挣脱缰绳,狂奔。父亲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捯不回来,反被拉倒在地。有一天,父亲与东安的虎庚、玉田的阿弟各牵一头牯牛,在一个叫暗塆的地方,碰到下郭的维云、家欢等四五个放牛囝。为争占地盘,双方对骂一阵后,维云耍起花拳绣腿,以为那三两下猫行虎步,就能唬住对方。父亲这方没人会耍拳术,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呐喊:“牛—牴哩!牛—牴哩!”生性好牴的牯牛,有了如此高亢的怂恿,如同引燃的炮仗,吱溜出去。双方的牛瞬间混为一堆,牴来牴去,惊心动魄。双方都在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的牛助威。连山上劳作的大人也激动难抑,远远地招呼:“哎吔,姓陈的放牛囝跟姓郭的厮打起来了,快看,快看啊!”对方人多、个大,牛也多,七八头,而且全是大牯牛,可谓人多牛众。父亲这方人少,个也小,真正具有战斗力的牛就一头,显然力单势薄。“一拳难抵四手。”牴了几下,父亲放的那头犟牛抵挡不住,又使出惯用的伎俩:打滚—好像学过本地拳术地术犬法,旋风一般,贴着地面,打转起来,且转且牴,且牴且踢。不一会儿,它完全丧失还击能力,有如体力不支却又逞强的拳击手,抱头挨打。众牛自觉没趣,各自散去。而人却不服气,又骂又嚗,越逼越近,终于扭成一团。毫无悬念,又是父亲这方败北。此事已过一甲子,维云碰见父亲,有时还会笑嘻嘻地问:“记得那次相牴吗?”父亲乐呵呵地答:“记得。当然记得。”
第三年,父亲到横路坪,给勉庚放一头大牯牛。牛很乖,很听话,没有难为父亲。
第四年,父亲留在寨里,给邻居潘庚(爷爷的哥哥)放一头小母牛。小母牛是从岭口大妹家“碰喂”过来的。所谓“碰喂”,即由牛主提供小母牛,对方养大后,生下的牛犊,双方均分。规则虽简单,但牛主并不会将小母牛随便“碰喂”出去的—慎重如嫁女,务必考察对方家道,尤其是负责放牛的人。大妹看了看潘庚那个瘦弱的儿子,噘着嘴问:“牛是给他放的?”潘庚灵机一动,指向立于一旁的我的父亲,答道:“不,是给这个放的。”大妹说:“哦,那还马马虎虎。”那时,爷爷已去邻县仙游打工多日,缘于被邻居细妹诬赖偷钱,也因自己赌博输了钱,卖掉年仅16岁的养女,偿还赌债,深感愧疚,一面想外出悔悔过,一面也想挣些钱。父亲的养母患有癫痫病,不仅不能照顾父亲,反而视若仇人,一碰见,便劈头盖脸地咒骂一通。父亲深为惧怕,没有丝毫亲情可言。爷爷出走之前,将父亲托付给潘庚;同时托付的还有2.8亩田地、两三担番薯米,作为代养费用。实质上,从托付那一天起,父亲即成孤儿,不仅没有得到爷爷所叮嘱的善待:少做事,不挨饿,不受冻,反而成为义工—放牛。仅仅放牛倒也罢。最难受的是,每天吃着“冇气饭”(没有尊严)—果腹的,不是残羹,便是冷炙。饭桌上虽有极好吃的鱼—据说来自日本,叫“黄泽”(音),短而肥,秃嘴,皮黄,无鳞,肉赭,刺少,油多,味道绝佳—却从不敢伸箸去搛。吃尚且如此,遑论穿着。除了过年,能穿布鞋,平日要么赤脚,要么穿用荐草编织的土名叫“草指拖”的草鞋,要么穿用油桐板劈成的粗糙不堪的木屐;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始年不变地穿一件来历不明、也不知缝补多少层的大襟衣。夜晚,父亲就像猫一样,蜷缩于一张稍宽的木椅。热天还好,冷天呢,仅遮一块又黑又硬的破棉絮。无数的虱子、臭虫隐匿在大襟衣里、破棉絮里,搦也搦不到,常常被它们咬醒;醒了,便挠痒,不停地挠,皮肤破损一片又一片!无奈之下,父亲拣个大晴天,把大襟衣抱去山涧,扔入水中,压上石头。虱子、臭虫浮出水面—白茫茫一片,一如落满雪花!放牛终究是苦活。寒冬的一个傍晚,雾浓,雨大,风也透。同伴纷纷赶牛回家,父亲的牛却失踪了。漫山遍野地寻找、呼喊,终于听见远处传来隐约的回应—分不清是牛哞,还是虎啸,反正越发惊恐了。最后在一个叫仙妈宫的偏远山场找到牛。然而,天已漆黑,不知路在何方……两年后,母牛拥有两头牛犊。可爱的牛犊不仅没有给父亲带来欢乐,反而平添了许多烦恼—每天都要担忧牛犊的安全。一天中午,回家吃饭后,立即返回拴牛的地方—坑门里。走到半路,发现母牛发疯似的往回跑,仅一头牛犊跟随。父亲不知山上发生了什么,继续前往,寻找另一头牛犊。但见一群天狗从狮子峰上呦呦叫着,直扑下来。父亲害怕至极,跑回叫猎人。邻居众庚拿了猎枪,急奔而去,到那里一看,山涧里的大岩石上除了一滩秽物,几根骨头,片肉不留。
下面,再说母亲的放牛生涯。
外公不仅当过保长,开过屠宰场,而且是颇有名气的中医,45岁时死于腹部鼓胀。遗留的家底,本来是够一家人敷衍生活的,而外婆却将十多担大米放出去寻租,结果颗粒无回。苦熬两年之后,时年13岁的母亲不得不去放牛,以求果腹。
第一年,母亲到大温洋,给肥三放牛。放的也是父亲当年放过的那头牯牛。跟父亲一样,也是赚工钱。牯牛依然好牴。每逢牯牛角斗,她都无比害怕,甚至大哭。牯牛的放荡不羁同样令人胆寒。初春的一天,它挣脱缰绳,跑到离本村很远的一个叫山表的自然村偷吃芥菜,被人牵走。母亲冒雨寻找大半天,才找到。母亲苦苦哀求,那人却铁心不还。天色朦胧时分,一位依姆路过,见母亲圪蹴在湿漉漉的地上—赤着脚、全身湿透、瑟瑟发抖,当着那人的面,解开绳子,把牛交给母亲,还安慰了几句。母亲号啕大哭。过七月半那天,肥三挽留母亲吃煮早米粿。那无疑是好吃的,只是佐料—丝瓜花的表面居然还有几只正在挣扎的蚂蚁!母亲好不容易活跃一回的食欲瞬间即逝。秋末的一个傍晚,牯牛从一丘山坪跳下另一丘山坪,竟然踣裂大腿!山坪并不高,矮矮的呀。母亲九个月的工钱全被克扣。
第二年,母亲到下玉井,给仕庚放一头小母牛。小母牛温顺如女孩,没让母亲多吃苦。
第三年,母亲到岭口,给新庚放一头牯牛。油坊拉碾的大犍牛,性情温顺,好放。那一年,母亲不再赚工钱,而是住入他家,当长工。自古以来,俗语仅劝“放牛兼砍柴”,而母亲每天还要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要拔猪草、煮潲、喂猪,几乎成了不知疲倦的打杂机器。不过,新庚妻子是个大好人。每逢节日,她都会悄悄地把肉或白粿、白米饭埋入碗底,盖过番薯米,然后以饭桌坐不下为由,叫母亲把饭端到厨房外面吃。有一次,她的好心被公公察觉,遭到责备:“放牛囝不要吃那么好,给一碗剩饭,冇饿死就行。”她赔着笑脸说:“阿爸呀,您怎能那样说?破布也是好布来,财主也是穷人来。放牛囝也是人,也爱吃乇。她又乖,又能干。何况她还是个细囡。给她一点好吃的,应该的呀。”经她这么一说,严苛的公公终于埋下头来吃饭。
第四年,母亲到高脚山,给会庚放一头牯牛、一头母牛。那一年,也当长工。会庚一家待人刻薄,每顿留给母亲的,几乎都是一碗被置于饭桌后边的剩饭!他们从来不管母亲吃还是不吃—反正已有成群结队的苍蝇吃过那碗饭。
第五年,母亲到盘富半山,给泰庚放一头牯牛。那一年,还当长工。泰庚老人一家就夫妻俩。他们心地善良,通情达理。母亲是秋天到他家的,在那里获得有甚于家的温暖。不过,初来乍到,母亲难免拘谨,做饭时说:“阿伯,我怕饭做得不好。”泰庚和蔼地说:“冇要紧,随便煮,有熟就行。”而且给予充分的自主:母亲想吃番薯加米的饭,就煮番薯加米的饭;想吃米饭,就煮米饭;想吃干饭,就煮干饭;想吃稀饭,就煮稀饭—最重要的是,母亲感受到了做人应有的自在与庄严。可惜好人没长命。到第四个月,泰庚妻子因腹部鼓胀而死。遭此变故,泰庚心灰意冷,要把牛卖掉。卖牛那天,泰庚叮嘱母亲:“等我收了钱,你拉住牛鼻圈不放,向买牛的要牛鼻钱。”多少放牛囝,都盼望有一天能拿到牛鼻钱—这是放牛囝唯一的权利—买牛的,如若不给,放牛囝可以解开牛鼻圈,使他牵不走牛。索要牛鼻钱,母亲虽有耳闻,但未曾尝试。母亲遵嘱照办。买牛的,犹豫许久,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五角钱—迟疑着,舍不得递交。立于一旁的泰庚见他如此为难,说:“给两块吧,你出两角,其余的,我贴。”泰庚爽快地把钱塞到母亲手里。母亲执意不收,连连退却。泰庚有些生气。母亲忸怩地收下。母亲舍不得回家,要留下,继续为他煮饭灴茶,而他再三婉辞。更令母亲难忘的是,他居然上街买回一块碧枝花布,赠给母亲!母亲首次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崭新而漂亮的布料,不禁热泪盈眶。
回家后,17岁的母亲听到“提倡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的宣传,决计寻找新的生活—把自己嫁了—再来一回投胎,比出生更为重要的投胎!
羊殇
「偷吃不瞒牙齿,好坏不瞒乡里。’你总看见了吧。你瞒得了别人,你能瞒得了自己吗?」母亲的声音很大,全然不怕别人听见。
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回来,务必做两件事:中午放羊,傍晚收羊。放羊成为我的第一要务。
放羊本不是什么难事,但在那个年代,的确成了难事。所有人都窝在村里,天天与那些少得可怜的土地作对。凡是可耕种的地方,一概被开垦,种了粮菜。根本没有羊的天地,没有羊的自由。只能揳,给羊画地为牢。于是,常常为揳羊发愁,急得在旷野里饮泣。
常言道:“一只手难搦两条鳗。”而我每天中午却要拎一串羊橛,牵一群羊,有大羊,也有羔羊,有羊牂,也有羊羝!有的羊羝很“秋”,毫无商量地从后面骑上羊牂的背,害得羊牂提心吊胆;有的急于觅食,急急忙忙,左冲右突;有的自甘落后,慢慢吞吞;有的却无缘无故地举起前脚,用头或角猛牴同行的头或角,訇然作响……羊绳也就乱了,缠到我的小腿上。牵羔羊的是麻绳。牵大羊的多为铁链。在田间小路上,与其说是我牵着羊群,倒不如说是羊群牵着我,生拉硬拽,趔趄而去。麻绳制造的疼痛尚可忍受。而铁链除了给我制造酷刑般的剧痛外,更有累累的伤痕和淋漓的鲜血!有时还被放倒在地,四仰八叉。更痛苦的还在于:有时控制不了局面,大乱,羊涌入路边的菜园或番薯地,吃了人家几株蔬菜或番薯什么的,结果招致人家冲天大嚗,被嚗得浑身发热却无汗可流,满腔怒火却无话可说,连鼻翼也没了风……
只要有一些青草,羔羊一般是不会吃稻蔸的。对于它们,相对好办些,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把它们揳于田塍。伤脑筋的是大羊。找过一塆又一塆,一垄又一垄,都无法把它们揳下来。饥饿的羊伸长脖子,低低往前冲。枵肠枵肚的我也直打哆嗦,眼冒金星。羊似乎不愿跟我继续寻找,停在水田边,拉也拉不动。我只好先揳一只怀孕的母羊。那里的青草虽不茂盛,倒也嫩绿。母羊高兴地啃了几口,抬起头来,仰视我,打个响鼻,又噘噘嘴唇,像是催我回家,又像在说:“你放心吧,我有这些青草就够了,不会偷吃稻蔸的。”此前,我听邻居放羊的小孩说过,有的大羊也不吃稻蔸。我将信将疑,掐了几片稻叶,递到它的嘴边。它嗅了嗅,果然不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