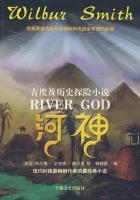[8月7日]夜宿深山
昨天下午,第二窑起火。他们担炭回家。我留在山上,负责看寮、添火。这是我头一回独处深山老林。
父亲即将动身的时候,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其实我怕得要命。
落日离对面的山顶还有两三丈高,我先填饱肚子,让饭为自己壮胆。可能是心理作用,感觉天暗得奇快。暮色像中弹的野猪,火速扑到眼前。那些曾令我惊恐得不能入睡的故事,也开始蠢蠢欲动,从记忆深处钻出来:土匪寨,好几个担夫逃跑,摔下悬崖,化作森森白骨……
悬崖就在不远处。
可恐可怖的故事还有:在这附近,曾有几个烧炭人,为排遣夜间寂寞,常常凑在一起弹琴作乐。有一次,弹至深夜,忘了“送”,各自回寮。人去寮静,时而鼎盖在动,时而碗箸在动,时而汤匙在动,时而饭勺在动,骚动声不断。三更半夜,这些异常的动静,是很吓人的。传说夜间在野外弹琴会引来鬼怪,收场时,务必弹一首专门的曲子,送走鬼怪,否则它就彻夜不归,骚扰人。故有俚语:“未学弹琴,先学送。”
老人常说的那些山精树怪,也从记忆深处跑出来,兴风作浪。最可怕的山精,当然是山魈。至于树怪,也跟山魈一样,它的厉害没人见识过,真相也没人揭示过,纯属臆想,各执一词。有的说,树怪白天类似鹦鹉,学叫人的名字,那是不能应的,一应,就会跟着它走向不归路。所以人在山间,彼此不得喊名字,只能一个人呼“喂”,另一个人应“哎”。有的说,树怪喜欢夜间捉弄人,时而砍树,时而破竹,时而滚石,时而又……
天越黑,联想越多,越害怕。
给猫灶喂饱柴禾之后,搬一大堆干柴,备在猫灶前。抱来一块大石头,又捡了七八个小石头,和大、阔嘴斧一起放在枕边。床前还放一根木棍,那是青冈,铁棍似的,又硬又重,像迎接一场战斗—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是自己?是暗夜?是突如其来的野兽?还是悄然出现的鬼怪?准备这么多武器,心里仍不踏实。又想点洋油灯。只要炭窑在烧,放射出来的光亮足以照明,就不点洋油灯。可今晚不能不点。只是洋油所剩无几,只好把亮光调到最小,像一只浮翔的流萤。光,向来是神秘的,即使是微弱的光,其作用也不可低估。我相信光,相信它能驱散黑暗与邪恶;我相信灯亮着,希望犹如睡莲盛开,灯灭,一切告吹—而此时,我透过昏暗的灯光,看着那些武器,不觉莞尔。
最先惹恼我的,是几只花蚊子。前几个晚上,就有这种蚊子,但没这么多,这么密集。蚊子好像跟我有仇,下手很快,叮咬很凶。打开寮门,反复甩动衣服,才把大部分蚊子驱出寮外。然而,毕竟寮门、寮壁均为草编,弥合再好,也有蚊子可钻的缝隙。
何必为蚊子烦恼,跟它们纠缠不休?还是看看书吧。书可吸收我的心理压力,能转移我的注意力。《高考复习大纲》带来这么久,一直没打开过,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我喜欢哲学,喜欢辩证法。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命题,叫我冥思苦想。而蚊子却不容许,乘机偷袭,我的脖颈、脸颊、耳朵、额头和手臂,所有裸露的部位,都是它们袭击的目标,都是它们饕餮的美餐。只得放下书,用被单把自己裹成茧—很快闷得一身汗涔涔的。令人惊讶的是,蚊子针状的口器,居然刺透被单,扎入我的肌肤,抽去我的鲜血,留下长时间的疼痛和奇痒!在与蚊子的周旋中,与蚊子的较量中,我是最终的失败者。在小小的蚊子面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奈。真想不通,人类可以应对虎豹豺狼之类的猛兽,却奈何不了蚊蝇虱蚤之类的小虫,还有肉眼看不见的病毒!
我没有信心坚持。毕竟坚持下去,也是无谓的—烧炭是权宜之计,不可能终身以此为业,迟早要另寻出路。
寮顶忽然“沙啦沙啦”作响。我有点怕,举起大打去,响声骤停。响声又作。呵斥一声,不停,反而更猛烈,想钻下来,找我较量。我坐起来,左手拿大,右手握斧头,毛孔扩张,头皮发麻。
猫灶的火焰越来越小,必须添柴。再怕也要出去。我知道,独处深山,金属声响,最能壮胆。举起大,对着身边的那块大石头,猛打几下,以手腕的发麻,换来些许火星和火药味。火星,响声,火药味,成了我的亲密战友。怯怯地,飞快地,添了柴,钻回寮里。
热闹只属于夏虫。刚刚睡着,又被吵醒。蚊子始终没有放弃对血的渴望,对我的袭击。睡去,醒来;醒来,睡去。熬到天亮。
父亲到山上,我问:“昨夜寮顶沙啦沙啦,是什么声音?”
“应该是老鼠。”父亲轻描淡写地说。
老鼠?我怎么会被一只老鼠吓成那样?
[8月8日]担炭回家
今天,首次担炭回家。担炭几乎都用炭篓。前两天编了几担炭篓。阿文、阿革不会编。我也不会。全是父亲和二哥编的。编炭篓跟编匾、编筥、编篮、编畚箕、编斗笠一样,大多从小由大人手把手教出来。聪明人亦可无师自通。比如二哥,只看别人怎么编,先记在心里,再回家尝试。不远处就有毛竹,砍来就是。难的是劈篾、编篓。父亲和二哥很讲究,力求篾片厚薄、宽窄一致,炭篓方格、大小一致,尽管炭篓不回收,多为一次性使用。炭篓像放大多倍的蚕蛹,立起来,跟我的个子差不多高。
“山逐寒云断,天随暮霭低。”山路仅仅高长,仅仅弯曲,并不算什么,最糟糕的是,路面有许多石子,像小滑轮,稍微不慎,就会滑倒。一旦滑倒,说难听一点,那叫:“连骨头都没地方找。”陡峭也是可怕的。有的路段跟梯子似的,可比华山天险,高个担炭都怕炭篓后碰,何况我。尤其是“龙崩”那段路,由于山体曾经大面积滑坡,乱石成堆。虽有好心人在那里整理出一条小路,蜿蜒下来,但窄处无可展足,高处又要半蹲下行。每块石头都像将要掉落的老牙,看似稳固,实则不踏实,散落其上的石子,更是暗藏的机关。即使空手途经那里,双腿也会发抖。再说,炭篓体积那么大,装满,担不动,没装满,又不结实。真是左右为难。只好用筥装炭,筥绳好办,想结多短就结多短,想结多长就结多长。我把筥绳结到最短,担在肩上,仿佛两个大金瓠。而我的人呢,则像金瓠架的一根木柱,斗笠便是一片金瓠叶。有的人擦肩而过,又回头注目,摇头晃脑,表情古怪。
走到半山,跨过横在路中脱皮的大枯树时,脚底打滑,还好没有倒地。但是,魂魄跑走一大半,心脏跳到喉咙上来,双脚哆嗦打个不停,几乎要跪下—好不容易,挪了几步,来到一块岩石上。“啪达”一声,蹾下担子。岩石广大而平坦,表面微白,散落其上的枯枝败叶,历历可数。眼前有一条树根,约一拃长,弯弯曲曲,略显湿润,暗红色,酷似刚刚掘出的小松树根,随手捡起把玩,看似静止的它倏地仰头,伸出挑衅的信子,猛扑过来—原来是条小蛇!虚惊一场。刚上山时,父亲提醒过我,山林里,蛇多,蜈蚣多,要小心一些,不撩惹它,就会相安无事;有一种俗称松树根的蛇,最喜欢呆在山路中间,比眼镜蛇还厉害,别踩了它。小小的蛇竟有如此高超的伪装本领!
常言道:“大船有大浪,小船有小浪;力大扁担硬,力小扁担软。”扁担怎么不体谅弱小的我?肩膀被扁担压得通红,磨得发烫,火烙似的。口也黏稠,喘不出气来,硬撑到一个叫油麻坪的地方。有个同学家在这里。我曾经去过他家。他的命真好,高中一毕业就补员,有了舒适的工作。也许他的父母还认得我。本想到他家喝茶,又不好意思,只在他家的后山上,一边看着缭绕的炊烟,一边舔着干燥的嘴唇。日头像灶膛喷射出的火舌。被火舌舔过的石阶荡漾着一阵阵热浪。面对热浪,我神志恍惚。路边枯草蒸腾的刺鼻异味,裤脚散发的不知从哪里沾来的野猫臊味,使我难以呼吸。仰望天梯似的山岭,所剩无几的力气,似乎被谁偷了,迈不开脚步,斜靠于岭边的杉树头,在一小片斑驳的树阴下,“吭哧吭哧”地直喘粗气,泪汗俱淌。怨恨命运。怨恨暑热。怨恨山岭。怨恨扁担。怨恨沉重的担子,真想甩了它,永远—甩了它!
风,一丝也没有。若有力气,我会呼唤风的。敞开衣襟,斗笠当扇,被汗水浸透的斗笠带子,也溅出汗水来。体内所有的“水龙头”完全失控,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如同虚脱,俯首可闻炖蛋般的心跳。
这时,上面下来一个人,奔奔跳跳的,像活泼的小白兔。他那白色的确良衬衫敞开着,随风飘动,又像一只白鹇在亮翅俯冲。他还和着树林里画眉鸣叫的节奏,打起悦耳的响指,吹起欢快的口哨。
第六感觉告诉我,一定是他。他家在炭山对面,也就是坑头自然村,我的爷爷和父亲曾经压番薯的地方。他在一个相当体面的单位工作。今天,他回家—不,应该说衣锦还乡。因为包括坑头以外的几个自然村,总共一千多号人,就他一人通过考试,下一条岭,上一条岭,下一条岭,再下一条岭。曲曲折折,坎坎坷坷,走出小山村,来到乡亲们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的县城。按乡亲们的话说,那叫吃“皇粮”。乡亲们羡慕得眼珠都快跑出来。
他离我还远,想必不会注意到偎于杉树头的我,赶紧戴好斗笠,压低斗笠边沿,头伏于膝盖假寐,如同受惊的鲮鲤,缩成一团。以为他会继续奔跳着,箭步而过。可他偏偏停下,轻叩我的斗笠,看我没反应,又翻起我的斗笠,见我睡着,一边轻声“喂喂”,一边扳动我的肩膀。我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他。他先是一愣,继而曼声喊道:“家恬—”彼此相视无语。“怎么,你也烧炭?”他好像隔着一座山跟我说话,分贝有点高。“嗯。”我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唉!”他长叹一声,往前走几步,又回头看我。我也看到他那怜悯的目光,白净的脸蛋,蔚蓝的背心,雪白的衬衫,体面的公文包,锃亮的凉皮鞋,背在身后的那顶麦秸草帽,以及上面的铁路标志和“南昌铁路”字样……
忽然,记起小时候唱过的山歌:“前山高来后山高,前山后山两把刀,一把刺进云雾里,一把插入我腰间。爬上一山又一山,一山放过一山拦,前山是虎后山狼,一步更比一步难。”喉咙仿佛着了火。艰难地向上蠕动,终于发现一泓水。水从石头上流下,脑海里闪出家中橱门所刻的两句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细看,石头表面不乏厚厚的青苔,爬虫般的水垢。水流极细小,几乎觉察不到流的态势、力量和动感,倒像鼎里潽出来的泡沫,跟我一样,有气无力。哪有王维笔下的那种美感?水泓又浅又浑,底下是烂泥,可见蠕动的水蛭和别的水虫;四周布满零乱的牛羊蹄印,一坨新鲜牛屎的旁边散落着一粒粒椭圆形的羊屎,牛羊滞留的臊味联合它们排泄物的臭味,似乎在共同捍卫它们的领地。牛已远去。羊已远去。口渴令我顾不了水质,摘来几片菝葜叶,折成小饮杯,先用它荡开水面秽物,再舀些水,尽管有浓重的异味,烫如开水,总算解渴了。继续呈“之”字形向上蠕动。“诸娘生囝不如担担上岭。”对于这句俗话,此时此刻,我有了真真切切的体会。
[8月10日]卖炭
“家里一分钱也冇了,连盐巴都借了好几盏。你们明天回炭山,总要带些子去吧?”母亲满面愁容。
我说:“带些酸菜黄豆就行。”
“你们可以配酸菜黄豆,阿革、阿文不行。”母亲始终把他俩当客人看待。伙食费因此增支许多。
本想过几天,集多一些炭再卖,看来不能等了。
上午,我和父亲去卖炭。这本是件开心的事。可我不能。磨破的肩膀还在痛,垫上毛巾,也会痛。大热天担担,穿短裤、光肩膀、搭毛巾是常态。穿短裤、光肩膀为凉爽,搭毛巾为护肩、擦汗。我怕羞,从来不敢当众吃东西,何况穿短裤、袒胸露背。隔衣搭巾,又显得另类。从老家到梧桐坂中街,要走一个钟头。以如此担夫模样上街,我真的有些为难。路上行人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都看着我俩,眼神怪怪的。我有一种难言的感受,跟在父亲后面,畏畏缩缩,亦步亦趋。
到了坂中街,几人围拢过来。这头瞧瞧,那头瞄瞄。这里敲敲,那里叩叩。都说木炭不错。市侩就是市侩,对于他们的出价,我一听,火气就往头上冲。他们也不摸摸自己的良心,那么低的价钱,居然叫得出来,也不怕丢失自己的居民身份?那么便宜,倒不如赠送。那样至少也赚一份人情。
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一家打铁店。父亲把担子架于门口,局促地进去询问。低头拉风箱的铁匠侧过老花镜,摊开左手,伸出五指,意思是一担五元钱。“也想食三骹!”父亲忿然,扭头出来,到门口时,丢下这一句。
我们继续往前走,一个光饼店的老板迎出来,看了看木炭,“嗯,好炭,好炭。”他似乎认识父亲,“你想卖多少,就出个价吧。这么热的天。”
“叫我出价,也不好说,差不多就行,六七块吧。”
“你这么实在,我也不还价。这样吧,别人一担六元,给你加五角。怎么样?”那人挺干脆。
“称去。称去。”父亲连声说。
除去重,合计净重200斤,我的80斤,父亲的120斤。父亲接过钱,都是零票,一大把,像一团糟菜。边走,边点。点毕,留下一元。其余卷成一捆。拉开裤头。擩进印袋。食指又伸进去,向下压了压。扣上纽扣。印袋是缝在裤头内里的小袋,可放私章,也可藏钱。裁缝师傅一般就缝长裤印袋,不缝短裤印袋。父亲的短裤印袋是母亲的创意。
没走多远,父亲拐进光饼店,提出一串光饼。总共十块,交给我。父亲叫我先吃一块。刚出炉的光饼,余热还在,好香。我先捋出一块递给正在弯腰整理筥绳的父亲,他仰起头,咬住光饼—口水顺着光饼边沿淅沥下来。一块光饼五分钱,剩下五角,握在父亲手心。
光饼串和筥挂于扁担,背在身后,右手搂住扁担,左手拿着光饼,边走边啃。虽不文雅,倒也是不错的享受。
从坂中街过来,到达梧桐街。父亲在一家鼎边糊店门口停下,向我噘了噘嘴。一碗鼎边糊两角钱。父亲大概想把手中的余钱花掉。他如此大方,让我窃喜。
即将跟随父亲进去鼎边糊店的时候,我瞥见一个姑娘正在埋头吃鼎边糊。于是,我趑趄不前。她是我初中二年级的同学,居民户口,家在梧桐街道。她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好,当然不是长相的问题,而是她那瞧人的目光,走路扭动的姿势,折射出来的那种令人讨厌的优越感—可以肯定地说,除了我,没有一个农业户口的同学能在她眼角的余光里。语文向来是我的强项。她坐在我的前桌,经常有求于我,甚至抄袭我的作文。后来,她考上大学,读了一个很吃香的专业,拥有一份很吃香的工作。而我这副模样,怎敢见她?我躲在隔壁弄口,等父亲。
不一会儿,父亲出来,拿着一个馒头,东张西望。我赶紧迎上去。“鼎边糊都舀了,你去哪了?”父亲把馒头摔在我的手心,气呼呼地走开。
我把馒头放入口袋,在后面默默跟着,心绪如麻。
[8月12日]神秘的事
今天是七月十六,也是进山以来的头一个牙日。
按照传统习俗,到山里做事的人,每逢初二、十六,都要做牙。昨晚,父亲回家,为做牙准备东西。
父亲回到山上,顾不上歇息,就在炭窑前面的空地上忙乎,一处摆着:1笾煮熟的“大耳”、1盘捞过的粉干,点烛2根,焚棒香3条,化纸钱3千,敬请土地神;附近的一处摆着:1碟菜、1碗饭,焚棒香1条,化色纸若干,让“鬼子”尽情享用,从此远去,不来惹我们的麻烦—毕竟“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就是做牙。做牙主要是请掌管土地的老大—土地神,祈求庇佑。人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在一个陌生、复杂、广阔的环境里,总觉得卑微,仿佛时刻受制于某种异己力量,时刻都有不测降临,诚惶诚恐。于是,敬畏大自然,并产生傩意识—战战兢兢而又毕恭毕敬地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庇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