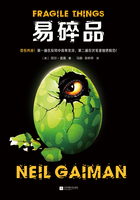“文革”中,母亲对我的诸多教诲都收效甚佳,尤其是尊师,当红卫兵们正在批判“师道尊严”的时候,母亲义正辞严地对我说:“师道尊严有什么不好?没有尊严能教育出好弟子吗?中国的古训就是‘天地君师亲’,老师比父母亲还要紧,师恩深如海、重如山哪!你千万不要去斗老师,斗老师就不是人!”母亲的话如雷贯耳,在学校和社会掀起批斗老师的高潮时,我竟斗胆利用自己在学校红卫兵组织中的一丁点权力,悄然巧妙地保护自己的班主任和其他老师。有一位老师在学校被斗得死去活来,我和盟友以“扩大社会影响”为名,将他悄然转移到社会上某个安全的角落,避开了日甚一日的惨烈批斗……
然而更加考验我的还是1967年父亲重病的时候。那年秋后,父亲常感不适,开始发病,及至病重住院,已接近年关。平时有病,父亲能捱则捱,从不住院,这次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住院。我们心中都明白这回父亲的病是危及生命了。我不能再住宿学校,赶紧撤回家里,赶赴医院,和母亲以及其他亲人全力护理父亲。就在大年二十九夜晚,父亲终于熬不过年关,撒手人寰了。他的死,使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从此,我开始静默而深沉地思考着人生。他一生辛勤劳作,老实厚道,朴素清贫。从乡村小贩到城市搬运夫,终年劳顿,疲于奔命,却粗茶淡饭,布衣寒舍。他一生为着什么?为着我们。同时,也对得起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他的一生非常平凡,却又实实在在,多做好事,于人有益,不枉此生。临死前几天,他告诉我,夜里常常听见汕头港湾的海潮声和礐石松林的风涛声,看见火葬场高高的烟囱和飘飘远去的白烟。他的遗嘱是:丧事从简,生活要紧,全家大小都要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
临终之前,父亲似乎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后来母亲证实的确如此。可憾已经病危的父亲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怀着无限的惋惜与遗憾,父亲抚摸着我的手掌,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
十一
母亲度过了最悲痛的情感时期。
一天夜晚,姐妹们都不在家,家里只有母亲和我。我正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似乎听到母亲在唤我,我立即走到母亲跟前。
端坐床上的母亲让我靠床沿坐在她的身旁。
“阿宗,你已经长大了,也快要下乡到海南了,有一件事,你父和我一直想告诉你。你父临终前本就要说的,可是来不及了。现在我该让你知道了。”母亲凝重地望着我迷惑不解的眼睛,继续沉重地诉说:“你的父母,就是说,你的亲生父母……”我本能地打断了母亲的话:“那不就是你和父亲吗?”
“不是的。”母亲坚决地摇摇头:“你爸和我只是你的养父养母,而亲生父母却是……”我又本能地打断了她的话:“别说了,您就是我的亲妈妈,我一辈子都离不开您……”
如梦初醒,更如醒后再入梦。真不愿意听见母亲说出这样的话呵,而母亲终于又说了出来。人世间,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不是常有的事吗?回想懂事以后,便觉时有外人背后指指点点,故里乡亲吐露过,左邻右舍议论过:“阿宗近来瘦哩,吃不饱呀,毕竟不是亲生的”;“人家养的比亲生的还疼,就单让阿宗上高中”。有的人干脆单刀直入:“你妈还没告诉你吗?你看你长得像你爸你妈么?”
我已经不是小孩,能想事、懂分析了,但我绝对不愿意相信那些杂七杂八的话是真的。这辈子我就认准家中的父母,但愿这是与生俱来、始终如一的天伦。哪怕到头来只是一个梦,但只要长梦无憾,又何必唤醒长梦呢?
如今,唤醒我的长梦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可敬可爱的母亲!我的心痛了、苦了、酸了、涩了……
如梦初醒,涕泪交加。母亲,二十年来,不是好好的梦吗?为什么不让我这辈子永远梦下去,而非唤醒我不可呢?
母亲,二十年的梦是那样的美好,我眷恋这长长的美梦,我盼望重回梦里,再续美梦!可是,我好难入眠,恳求您为我催眠呀,就像我小的时候……
唉,人哪,长大才觉童年乐,醒来方知梦中福。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二十年前,一个不幸的小男孩辗转了几家才幸运地落了户,投入了一位陌生母亲温暖的怀抱,受到全家的疼爱,开始了幸福的新生活。
他的名字叫什么好呢?养父养母商量了好多天,又征询过故里有文化的人,最后还是按照双亲的意愿,叫“继宗”,以后实在需要他“继承祖宗”啊。
为了让小继宗喝足奶水,母亲痛下决心,毅然断了仅比继宗大十个月的姐姐的奶水。小姐姐饿了,白天黑夜哭个不休,不知怎的,小弟弟也跟着哭了起来,妈妈双手搂着一对哭闹不止的婴儿,日子可难哪。
弟弟长大了,要读书啦,全家打心里高兴。两位小姐姐争着快点进工厂做工,挣了钱才能保弟弟读书哩。
这就是我依稀知道的童年。
母亲真情告知了我的身世,了却心事,如释重负。她慈爱地端详着我,说:“阿宗,后半世人,阿姨就跟着你了。”母亲习惯了自称阿姨,“你去海南,阿姨同意。几年后,等你在海南安了家,阿姨就跟去海南,给你理家。”母亲说得十分坚决,毫不含糊。
1969年7月24日,我在人山人海的广场码头,在震撼人心的喧天锣鼓声中,告别了家人、亲友,告别了母亲,登上了红卫轮。经过四十八小时的颠簸,终于在海南岛西海岸的八所港登陆,然后穿越二百里地的山林与草地,抵达安家落户的八一农场,开始了屯垦戍边的新生活。
就在汕头市人民广场等候红卫轮的时候,我构思了小诗《海滨极目》:“鮀滨徐寂月明时,似有椰风拂布衣。搔首天海生百念,引步堤林待千里。礐山挥峰题辞语,韩水奔流吟别诗。滔滔眼下尽逝远,却见琼州飘红旗。”
“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在那火热的年代,无论是母亲还是我,都感受不到白居易诗歌《母别子》中的那份情怀,但我倒能领略到清人高其倬《行役晓发》诗中的意境:“慈亲起送我,语好颜色凄。爱我不便哭,愿我平安归。”
十二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每当离别母亲的时候,我都会自然地想起唐人孟郊的名诗《游子吟》。我和母亲各自体会着人世的永恒主题——母子之情,但无论怎样,我都不如母亲体会得更深沉、更厚重、更久远。
母亲的身边有三个亲生女儿,而她却愿意远离女儿,放弃城市,千里迢迢,到那陌生而荒凉的边疆,跟随自己的养子,住进茅棚,过艰苦、紧张而穷困的日子,这是一份怎样的养母情结呵!
我深深地为母亲所感动了。但当我将母亲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却遭到了几乎一致的反对。知青朋友们自不消说,就连“再教育”的老师们——部队首长和农场老工人都婉言劝止。
人们的看法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宁可远离母亲,也不能让母亲受苦。为此,我给母亲写了一封封家信,劝说她安心在汕头,和三姐妹好好过日子。母亲终于接受了我和大家的劝阻,留居老屋,为姐妹们带大了一个又一个的孙子。但她人在汕头,却心想海南,永远怀着一份不了的挂念与忧思,且弥久弥深,像陈年老酒年复一年地酝酿着悠悠的酣醇。
夜,一弯迷蒙的新月从东端的长岭山后升起。当月过中天的时候,凝望纷飞盖月的乱云,迎着阵阵清凉的山风,我依然徘徊在胶林的小路上。
思潮涌来,我想起了古人的诗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小雅》);“短衣孤剑客乾坤。奈无策,报亲恩。三载隔晨昏。更疏雨,寒灯断魂”(元朝·陈孚);“荒鸡断续天将曙,游子辞亲寸心悸,霜鬓携灯立槛前,频语加餐暗垂涕”(清朝·许润)。但我印象更深的是清人蒋士铨的《岁暮到家》:“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因为当我重温此诗之后不久,便被组织批准第一次回汕探亲了。
探亲,给母亲和家人以巨大的惊喜,可是惊喜过后,却是更深长、更凝重的忧思。
“衣裳再添几件,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有妈熬的小米粥。一会儿看看脸,一会儿摸摸手,一会儿又把嘱咐的话装进儿的兜。如今要到了离开家的时候,才理解儿行千里母担忧。千里的路呀,我还一步没走,就看见眼泪在妈妈眼里流……”这是我刚学会的歌曲《儿行千里》中的歌词。那年探亲结束,将要离开母亲的时候,那情景多像这歌唱的哟!
汽车,离开汕头,向着广州、向着海南的方向奔驰。没有座位,我站在车里,一闭上双眼,就浮现刚刚辞别的母亲那溶进无限忧思与愁绪的泪眼……哦,母亲,虽然成吉思汗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个最好的女人,便是我的母亲”有些偏颇,但是但丁所说的“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却是千真万确的。而犹太人的谚语则更显示出母亲的神圣:“上帝无法分散在每个人的身边,因而创造了母亲。”周总理也一语中的:“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
就在我结束第一次探亲返回海南不足一个月之时,无甚大病的母亲突然中风,从此偏瘫,卧床不起。人们都说:这是愁阿宗得的病。
母亲的突然病变使我如从悬崖忽坠深渊,从惊呆状态中激醒过来之后,毅然走上第二次探亲之路。
心负深深的内疚,日夜陪伴着因我而病的母亲。母亲渐渐微笑了,她的精神有了明显的好转。可是,这短暂的探亲假,又怎能尽儿的孝心呢?
一晚,饭后,母亲拉住我的手,绽开神秘的笑容,悄然问我:“阿宗,别忘了你爸临终的嘱咐,有人了吗?”我明白母亲又在操心我的大事了,为了安慰她,让她安心养病,只好说了谎:“有了,有了。”母亲兴奋地追问:“怎么样?在哪里?”我爽朗地笑起来:“在海南,你会满意的。”“下次带来,让妈看看。”像黑夜里看见了月亮,母亲将我的手拉得更紧了。“阿姨,你放心,我会让你高兴的。”
灿烂的笑,甜蜜的笑,溶化了母亲的病容。
出嫁的姐妹们常来照料病中的母亲。
冇兄、冇嫂、阿舅、三姨、阿婆、锦清姨、斋姨、圆嫂、油姆,多少亲戚、邻居、朋友甚至不甚认识的、不知名的,越来越多的好心人,关心着病中的母亲。
母亲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那么多的人关心她,给了她巨大的慰藉,但她心中深深的情结,依然是远在海南的养子。世上万般哀苦事,莫非死别与生离呵!
“皎皎长安月,漫漫京洛尘。出门今六载,万里望吾亲。”黄遵宪的诗《二十初度》,表达了我的心境。在下乡海南的第六个年头,我终于回到了汕头市,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此后六年,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十三
回城后的第二天,我就到汕头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第二年夏天,又转到汕头港务局;1977年4月22日,我和凤贞结了婚,第二年生了儿子林瀚。在这段岁月里,精神的欣慰,生活的照顾,使母亲的面貌为之一新。望着新媳妇,搂着小孙子,母亲满足地笑了,笑得那么自在。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为人父之后,我更领会了“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凉”(《礼记·曲礼上》),晓得了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什么“久病无孝子”,那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林某人永无此心。
毕竟病魔不饶人。我痛心地发现,母亲的病情每况愈下了。
起初,母亲还能够扶着墙或桌椅在斗室里移步,后来,生活便基本不能自理了。她极爱清洁,却又鞭长莫及。洗脸洗头,洗澡洗脚,打饭打水,都必须依靠家人。有一夜,她把大便拉在裤裆里,想自己悄悄清洗,结果却更脏,连油灯和毛巾都沾上了大便,满屋子臭气。母亲眨着一双惶恐而又惭愧的大眼睛,像做了错事的孩子,继而泪流满面,又羞又气,狠狠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在病榻上,她非常痛苦地度过了九年,直至临终时,她没有哀叹过一声。
母亲安详地走进了梦乡,永远睡着了。她一生给予我们子女的,不知比我们应尽的义务多了多少。然而,她却惴惴不安地离开了我们,生怕拖累了我们!
我久久地默坐在母亲的坟前。
寂寞临墓儿凭吊,蓬草遍地牧童歌。
风吹山野纸钱飞,陵墓层层春草绿;红棉花映金凤树,尽是生离死别处。此刻,王安石的诗似更确切:“山川凛凛平生气,草木萧萧数尺坟。欲写此哀终不尽,但今千载少知君。”最后一句应改为“但今百载多思亲”。
我又久久地默坐在母亲的坟前。
善魂红晚霞,热泪湿春风。坟荒草已陈,墓湿土犹新。我想,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春尽有归日,老来无去时。岁去人头白,秋来树叶黄,于是,便有了“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生命景象。山中常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我想起了唐人李孟的《照镜》诗:“衰鬓朝临镜,将看却自疑。惭君明似月,照我白如丝。”苏轼也说:“老去怕看新历日。”昔为春月华,今为秋日草。白发生来如有信,青春归去更无情。
默坐在母亲的坟前,轻抚着凄凄的芳草,眺望着滚滚的浮云,领略着辛弃疾的哲言:“事如芳草春常在,人似浮云影不留。”
从此,我总喜欢唱些关于母亲的歌曲,踏着歌声,轻轻走进温暖的梦乡,去追寻母亲的足迹,谛听母亲的声音。
金梭银梭,穿织着飞逝的日子。转眼间,小瀚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就要结婚了。在双亲的香炉前,我默默地告诉老人家关于孙子的成长历程,让小瀚结婚时秉烛持香,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我想,天上的母亲必定亲抚着可爱的孙子,绽开爽朗的笑容,对父亲说:“你还没见过内孙呢,已经长大了,正要结婚哩。”
父亲频频颔首,憨憨地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