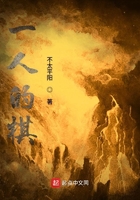呵,大姐,远离故乡的亲人,你可曾想象我们对你是怎样地牵肠挂肚?你是否领会双亲临终前对你的呼喊和渴见?老人家弥留之际,总是叨念着“惠卿”的名字,心里惦挂着这个最懂事的大女儿。父亲长年外出做工营生,难以照顾家庭,幸而大姐你,常帮母亲操持家务,照料五个弟妹。后来,你远嫁香港,有了几个孩子,还到工厂里打零工,你实在太累了——双亲从心底里疼你,尤其在生死诀别的时候。所有的亲人都见面了,惟独大姐你没有回来。父亲干瘦的脸颊淌着依稀的泪水,母亲轻轻地呼喊着你的乳名。双亲在两层世界的界碑前徘徊,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翘首盼望着远隔万水千山的女儿,留恋着人世间美好无瑕的亲情。父亲和母亲终于都没能见到大姐,直到父亲再也淌不出泪水、母亲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的时候,但他们仍然不肯闭上眼睛。
大姐终于未能回汕与双亲的灵灰遗像告别。从此,她成了家族中有争议的人物。
真想不到,我竟然有了赴港的机会,梦魂飘忽般地走进了大姐的家门。五岁以前,我一直由大姐带着。她比我大十五岁,特别会疼人。她深切而动情地提起了我小时候的许多事。她领着我到村头摘麻叶回家煮地瓜汤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她的脸上泛起沉醉在记忆中的幸福的微笑,可是当她一谈起父亲临终前未能返汕诀别的往事时,便情不自禁地喁喁而泣了。那时候,她正怀着八个月的孩子,还抱一个,背一个,拉一个,带一个,家里又没有老人,请保姆或送托儿所、幼儿园,都付不起费用。当一纸电报飞来时,她的心快碎了,心尖滴着血……母亲病逝时,她也离不开家,负担重着呢。如今,她只有泪水涟涟,深叹永生的遗憾。
双亲去世以后,大姐深信人的命运难以由己,从此开始吃些斋饭。时年八节,她便到沙头角的蓬瀛仙馆烧香拜圣。
我眺望白练似的香江、骏马般的山岭、高高耸立的楼宇和湛碧如蓝的维多利亚湾,忽然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那隽永凝重的词句油然而上心头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夜来幽梦忽还乡……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我不胜感慨,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
大姐和外甥带我登上了高高耸立的太平山,山巅,天风浩浩。我们俯瞰着繁华的港岛、九龙和香江,又不约而同地遥望着家乡的方向,那苍茫雄健的江山,与太平山下的风光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啊,山水相连人分离,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月如无恨月长圆……
大姐依然遥望着故乡的方向,她又想起那巍巍的文光塔;想起小时候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拉尿,父亲没打她,反而笑了;想起父亲每次回家便给她带来好吃好玩的东西;想起每每思念自己的生父生母的时候,母亲便倾情地安慰她,替她擦拭着泪水,紧紧搂着她哄她安睡……她伤感起来,神情凝滞而肃穆。她恳求我:回汕之后,向亲人们说明情况,希望家乡亲人谅解她。
怎么能不谅解呢?大姐带了我几年,那时我虽小,却也初解人意,晓得她上敬父母、下疼弟妹,她时常背着我爬山越岭。谁又料到,正是这万岭千山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重重阻隔着我们骨肉情亲呢?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曹操《苦寒行》)。大姐,我理解你,在香江的每一个春秋,你又何尝不怀着满腔的思亲情愫呢?那般深情,有如香江,有如韩江,那么清澈,那么悠长……
五
从懂事的时候起,母亲在我的心目中,便是至尊至亲的。最先启迪我的是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大凡至尊至亲的,都比作母亲。党是母亲,祖国是母亲,故乡是母亲,以至于母亲河、母校、母本,等等。《诗经》早就歌颂了母亲的伟大功绩,在“小雅·蓼莪”篇中写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常用大木盆给我洗澡,边洗边说:“你不要贪玩,要好好学习,书读好了,就让你上大学,还要送你到美国留学。”母亲的启发与鼓励,在我幼小的心中播下了热爱读书的种子,以至成为经年不竭的动力。
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多层面多渠道的,也是潜移默化的。
小的时候,家住棉城。母亲常常携着我,来到文光塔玩耍。懂事以后,朦胧地感受到文天祥丞相浩然的正气和雄健的文才。母亲和父亲多次给我讲述文丞相的动人故事。后来,双亲领着我多次登上海门莲花峰。迁居汕头后,每每清明节,我便随母亲回潮阳祭祖,一有机会就登莲花峰,那形象,那灵性,便伴随岁月不断延伸和强化。随着岁月的推移和阅历的沉积,我渐渐读懂了双亲对于莲花峰的情结和文天祥的情思。那情结,那情思,不是别的,正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双亲的熏陶、教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着认认真真做人、老老实实办事。
记得五岁时,母亲带着我到父亲工作的家俬店里玩。大人们忙着说话呢。不知谁的黑香云上衣吊在衣架上,我不经意地从那上衣的口袋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画着图案和像头的纸张,觉得又漂亮又好玩,于是当玩具带回家中。母亲发现后大吃一惊,赶紧带着我连同那些“纸张”重返店中,问明“纸张”是谁的,立时赔礼道歉,如数奉还,再三数说我,说是我不懂事,还以为是小人图。那时候,我真不懂那就是钱呵。
想起儿时的朋友和邻居,我自然感慨一番。他们有的当了教师医生,有的已是国家干部,有的成为能工巧匠,有几个还是工程队队长,发家致富了,而我更关心的还是自幼残疾的拉里和恩怨有加的“白毛孩”。拉里从小不能直立,只能爬着走路。母亲见他孤独,便让我与他交朋友。我同情他、帮助他,不许别人欺负他。我们成了患难之交、莫逆之交。迁居汕头之后,每年清明我一回故里便去看望他。当他经过苦练成了木匠已能自食其力之后,我真为他高兴,以这位身残志坚的老朋友为荣。至今想起来,还真感谢母亲的引导。
我的同桌同学“白毛孩”,他从头发到眉毛,与生俱来便是白的,全身皮肤白里透着淡红。我们友好相处。可是有一次,他无意中将我的语文课本丢了,还说不知道。我一气之下,撕烂了他的语文课本。他最疼课本,于是哭哭啼啼上我家告状。妈狠狠地打我,他反而急了,挺身护我,谁料也挨了一竹条子。妈疼不过,放下竹条子,一面自责,一面抚摸白毛孩的痛处,可他却说:“阿姨,不要紧,我不疼,只要你别打阿宗就好了。”妈妈打我,我没有流泪,可这时,我的泪珠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心中默想:“阿毛,我永远忘不了你!”第二天,母亲买了两册语文,我高高兴兴地送他一册,他却从书包里掏出崭新的语文课本,说:“我用压岁钱买了,没让家里知道。”后来,我们将多余的一册送给了一位丢书的同学。第二年,我们全家人搬到汕头市定居了,从此再也见不到白毛孩了。几年后重返故里时,才知道他随父母去了上海。如今,听说他已当了教授。
读小学的时候,逢年过节,母亲有时做可口的驳梓粿,让我到市郊摘些驳梓叶来做粿。我乘机用小竹管做支驳梓枪,又采了许多驳梓粒当“子弹”。于是,手痒了,动不动就“发射子弹”,一不小心,竟射中了邻居女孩的眼角,她哭闹不休,我赶紧逃回家中。母亲知情后,狠狠地克了我一顿,领着我登门赔礼道歉,偿了医药费,还没收了我心爱的驳梓枪和所有的“子弹”……
六
像放电影一样,少儿时代,母亲给我的印象一幕幕,生动、深刻而有趣。
我还记得那一片生机蓬勃的麻田。母亲多次带着我到麻田里摘麻叶回家煮红薯,那味道真爽人。有一回,我想摘嫩叶子,于是骑在母亲的双肩上。右手勾住母亲的头额,左手伸出去摘麻叶,谁知手伸得太长,身体向前一倾,差点儿摔下来。我一紧张,竟然撒出尿来,母亲一手按住我的双腿,一手撑住我的上身,疼爱地说:“我的小祖宗,撒吧,撒吧,把尿全撒完,不要留一半在肚子里,会伤身体的。”那淡黄色的尿液灌进了母亲的脖子和脊背,湿透了她的上衣,可她还笑着说:“烧烧,等一会就凉快哩。”
我走过麻田,来到一道清泉沁透的坑沟旁,那潺潺流淌的泉水诉说着一桩平凡而又难忘的往事。我六岁那年,母亲经常上山割草,我总爱跟着。一次,我扭伤的脚还没有痊愈,却缠着要跟妈妈上山去割草。妈好说歹说劝我养好伤再说,我岂肯善罢甘休,拉着妈妈的裤腿就是死死缠住不放,明一程暗一程地跟着妈妈到了坑沟边。妈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把我放进坑沟里,让泉水浸到我的肚子上,我放声大哭,幸亏大姐赶来,将我从坑沟里拉了上来,背抱着我走进打破碗花盛开的山坳里,采摘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山花,还捉了一对彩蝶给我玩,我才破涕为笑。妈妈割完草,就匆匆寻找,找到了姐姐和我,见我笑了,她也乐了,双手一抱,就将我抱进草筐里,然后一边挑着我走路,一边逗我高兴。妈说,下回到祖父母的坟上扫墓,她带我去。我兴奋极了,一路笑声……
妈妈真好,她没哄我。清明,妈妈真的第一次带着我去给祖父母扫墓。翻山越岭,路不好走哇。半路上,我不小心扭伤了脚脖子,肿了起来,痛得不行。是妈妈背起我,翻越两个山岭,扫完墓,又背着我翻山越岭走回家,眼看妈妈喘着粗气,累得满身大汗,快走不动了,我便央求妈妈让我自己走路,妈妈当然不答应,她只在路上歇了两回脚,硬是将我背回了家。将近到家的时候,她大气吁吁,已经举步维艰了,幸而大姐跑来接应,才解了妈妈的围。累归累,妈还是有说有笑,抚摸着我的头,挺高兴的样子哩。
母亲对我的教诲是不拘一格的。还在家乡时,我曾拾了小半木桶的蚶壳,移居汕头后,早忘了这件事。不意过了两年,有一天,老家的邻居——八十多岁的葵姆叩开了我的家门,母亲和我都感到意外。老人家慈祥地望着我,轻轻抚摸我的头,呵呵笑着,合不拢的嘴说话了:“阿宗!”她颤巍巍地从肚腰里掏出一个小红包,“你那堆坩壳,我帮你卖了一角三分钱。奴呵奴,拿着,以后买纸买笔用。”我红着脸,不肯接过来。葵姆硬是塞进我的手心。那小纸包,还带着老人家的体温呢。望着满脸皱纹、吟吟微笑的葵姆,我深感故乡的人情那么纯真、那么憨厚,又是那么美好。遵照母亲的吩咐,我将小纸包小心地保存下来,一分钱也舍不得花。直到笑口常开的葵姆九十二岁去世时,我才打开小纸包,把钱拿出来,凑着让母亲买了纸钱香烛送到葵姆的墓前……
小的时候,母亲曾经多次领着我游览过文光塔与莲花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美好的情结。随着岁月的推移,那小小的情结发了芽、生了枝、长了叶,不断成长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驱使我跟随着双亲和乡人,屡屡游览了潮阳的古迹和景点,触发那绵延的回忆与美好的乡思。攀上棉城塔山的西岩,瞻望清爽幽深的岩寺观和北帝阁,谁人不赞“问潮井似明心镜,连理树成白象形”?凌登县城东边的东山,景仰供祀唐代名将张巡、许远的“双忠祠”,颂扬文天祥的“大忠祠”和纪念韩愈的“韩祠”,尝一口“曲水流”甘甜清冽的泉水,令人油然而忆起“山灵兼爱千秋笔,岂重今人薄古人”的佳句来;神游群峰苍茫、碧水潺湲的龙山湾,面对清幽高雅的灵山寺和留衣亭,不禁发出“大颠自有僧人衲,韩愈何劳赠俗衣”的慨叹;驻足于“绽石莲花光宇宙,冲霄正气动天人”的海门莲峰上,天悠悠,水悠悠,何处方能见帝舟?我又想起了启功先生咏莲花峰的诗来:“无愧天南第一洲,风帆如画碧波秋;地灵人杰昭千古,又幸奇缘过汕头。”深感故乡的历史、人文和自然,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矿藏,有待我们世代不断地发掘。
故里的文化矿藏,更长久、更深刻地牵动着我的心灵的,还是那巍巍耸立的文光塔。而将文光塔立于我的心宇苍穹的,还是我的母亲。
小的时候,我就时常在母亲带领下游玩于文光塔,我家就住在离塔只有三百米左右的地方。懂事以后,母亲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文光塔的故事。文光塔始建于宋朝咸淳二年,即公元1266年,后倒塌。明崇祯十年重建竣工,因地震闪射毫光,时人以为人文昌盛之兆,于是更名“文光塔”。塔高十六丈,八面七层,登上塔顶,一览县城全景,极目远眺,东西端小北山群峰起伏,南面的南海浩瀚无边。文光塔在人们心中的神威,正如塔门两侧的对联一样:“千秋文笔振金石,百丈光芒贯斗牛。”母亲闪着虔诚的双眼告诉我:相传棉城是一艘驰向浩浩南海的大船,而文光塔正是它的桅杆。多少乡人乘坐这艘船,飘洋过海,到处落户,到处创业,扎根于世界各地。于是,文光塔,这故乡的象征,便成了所有潮阳人心中的桅杆,不论你漂泊多远,它都是你心中的定海神针,是乡魂缭绕的支柱。我多少回梦见母亲,又多少回梦见文光塔啊!
故乡,多少乡景,多少乡情,多少乡思,令我动情。而最使我梦魂牵萦的,还是那高高耸立于棉城中心的文光塔。梦去,醒来,泪光闪闪。每每梦见母亲,必在梦境里重见文光塔;每每仰望文光塔,就像凝望慈祥的母亲。母亲呵,您真像那文光塔;文光塔呵,您就是我慈爱的母亲……
七
或许由于私塾家庭的长期熏陶,或许由于缺少文化带给人生的遗憾与启示,母亲尤其重视我的读书学习。家里很穷,兄弟姐妹五个,只保住我一人上中学。后来生活略有改善,妹妹也才上了中学。
记得那时候,家里只有两盏煤油灯。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当着全家人提出,把较亮的那盏油灯给我使用,首先保证我夜晚的学习。全家人异口同声,都爽快地赞成。惟独我大声回应:“还是大家一起用吧。”结果自然是辞却不得。母亲的关怀,家庭的温暖,使我暗暗地落下了热泪。
可是,好景不长。我初中毕业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家里自然更加穷困了。我明白家庭需要我辍学做工,以求维持艰难的生活。但我心中又十分热爱读书。经过激烈的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向双亲开了口:找工做,不再读书了。双亲很吃惊,不过他们深懂自己的孩子,还是规劝我继续读书。我当然知道家情,知道双亲心有余而力不足,便坚持辍学做工。母亲只好请亲戚帮忙找工作。开始传话过来,说是让我到某机械厂当锻工,学打铁。我身体结实,体力很好,于是满口答应下来。那时候,老师、同学们,以及知道我学习成绩的亲戚朋友们都为我可惜,纷纷劝说我继续升学。我决心已定,也就放弃中考了。可这回命运捉弄了我,两头空了。不知什么原因,打铁的锻工也做不成了。
我心灰意冷,母亲更加后悔。夜里,常常传来她那深沉的叹息声。好几次,我忍不住起身安慰母亲,可是,母亲却摇着头,连声自责。她太伤心了。她了解我的学习成绩,班里一些同学曾经七嘴八舌告诉她:阿宗是班长,作文曾获93分,破了学校的高分纪录,文章曾登在地级报刊上;全校数学竞赛曾获第一名,英语竞赛获第二名,还在全校介绍学习英语的体会。每学期各科平均分数总是数一数二……母亲越想越难过。
无可奈何。那一年,失学的我只好自己找活儿干了。先是拉煤,后是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