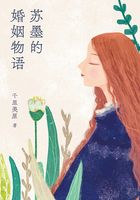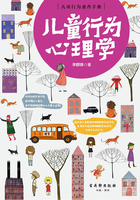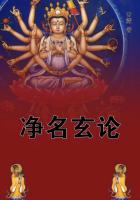一
梦里依稀慈母泪。
这二十多年来,我时常梦见慈祥的老母亲。那些梦境,有时是清晰而真切的,但更多的是迷蒙而依稀的。因为在梦中,常常感觉泪眼模糊,或者母亲,或者自己,或者母亲与自己。
当我的母亲经历了九年疾病惨痛的折磨、脸上浮现一丝解脱的微笑、似乎安详而又心有不甘地离开她依恋的世界、家庭和所有亲人的时候,我和亲人们不禁急促、惊恐而又近乎绝望地以各种称呼叫起来,可是,母亲依然是一丝解脱的微笑,依然是似有不甘的安详,静静地躺在那张用木板拼成的、铺着草席的再熟悉不过的小床上,不再回答我们了,永远地,永远不再回答了。但我却分明听见母亲一声微弱的长长的叹息!在场的人中,姐妹们也说听见了,而其他亲人和邻居则说没听见。多少年后,我仍然确信那似无而有的长叹,相信在母亲最亲近的子女中,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守灵——脑里一片空白。
听经——心中起伏杂音。
过桥——阴间冥冥有路。
入殓——寿衣、纸被、纸钱遮住了泪眼模糊的视线,颗颗寿钉钉在我滴血的心头。
出殡——从母亲的床前跪至棺前,我一拜再拜,长跪不起,悲极而泣,苦涩的泪水汩汩流入口中。细雨,淅淅沥沥;微风,喁喁如诉;人们,悲悲切切……“传呼犹在耳,会哭已填门”(宋·王安石)。
送葬的亲朋好友,身穿麻服,或戴着黑纱,排成长长的队列,低头默默地行进。手中点燃的香火,吐出一缕细细的、断断续续的烟雾。我被排在第一位,扶柩护灵,跟随母亲,肝肠寸断地步步走向礐石山,走向那陌生的、可怕的火葬场。永远忘不了那焚心的一刻,烈火吞噬了母亲!我仰首凝望着火葬场高高的烟囱和飘飘远去的白烟,反复思索着母亲的遗嘱: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办事。
我滞立在火葬场凄凄的草坪上,呆愣愣地眺望着如幻如梦的天际,久久追寻着承载着母亲的英灵远去的那一缕总不飘散的白烟,苦泪无声地流淌,此身恍然梦境中。那一刻,那一幕,永世定格在我深深的记忆之中……
当无情的炉门慢慢开启,火葬人员将母亲温热的骨灰熟练而又庄重地装进骨灰盒中的时候,我又无声地洒下了滴滴苦泪。那引灵的亲人已然手握点燃的香火,默默地走在前面。我双手捧紧骨灰盒,步步跟着引灵的亲人,呆呆地走过草坪,走向海边,走在回家的路上。崭新的骨灰盒顶盖,静静地流淌着我的泪水,和着人世间那好像善解人意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丝丝雨水……
母亲的灵盒安然置于家中的神龛上。我常常默默地注视着灵盒,感受着老人家的温暖与慈爱。我多么希望灵盒能够长久安放家中,让我和亲人们日夜相伴呵!可是,按照长辈们的吩咐和安排,必须选择吉日,将灵盒安葬于故乡潮阳的山岭上,让母亲重归故土。作为晚辈,我没有自主的权利,只得遵命。但我恳求:让母亲和此前十三年去世、已安葬在潮阳公鸡岭上的父亲合葬在一起,好让两位老人家永远相依相伴。我的请求,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却遭到家乡老辈的否定,当时以风水为理由,至今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非分葬不可的原因。于是,只得盲目地服从。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物资严重匮乏。我想了许多办法,才弄到一包水泥,便用单车载着,沿着崎岖的山路,越过蜈田岭,由我一路载到潮阳。
临穴之时,至今历历在目。母亲的灵盒安入陶缸,用水泥封盖。然后砌基、安穴、培土、封穴、造坟、立墓……那时那刻,临穴频抚灵,至哀反无泪。并非杜甫低吟的“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只觉人间痛离别,此岭正是长别处。
那一夜,故居的黑屋里,通宵听雨。夜雨愁更咽,春日淡无光;草露随风泣,松涛向夕哀。第二天回家,母亲的居室里,椅子上挂着遗衣,床上铺着遗被、陈着遗枕与遗帽,桌上放着遗存的碗筷,地上还摆着遗鞋……这一切,让我处处感受到母亲依然还在身边,她仍然活着,活在我和亲人们的心间。
二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宋·李清照)。
每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母亲的祭日。这一天,母亲的子女们便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我家,烧香祭灵,忆念母亲。常怀鞠养之恩,倍增思念之痛。虽说黄泉无晓日,我辈青草自知春。
每年,当绵绵的春雨带来回忆、追思与缅怀的节日——清明节的时候;当我走在那熟悉的乡间小路上,追溯着父母远去的足迹的时候;当我伫立在双亲的坟头,凝望着这片古老的丘陵松柏成林、山草青青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陷入那深深的沉思,久久地思索着永恒而又常新、高远而又现实的主题——亲情与人生。
我依稀记得第一次跟随母亲返回故里上坟扫墓时,正是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是作为惟一承接香火的“小祖宗”踏上清明之路的。天那么蓝,地那么黄,水那么绿,山那么青,人那么多,路那么长。手捧红烛香火的我,兴致勃勃地走在山间弯弯的小道上,虔诚而又好奇地想着,想着自己的祖宗。当我穿越几棵大榕树的浓荫,爬上水库的坝顶,看到大片大片的墓地时,忽然拉着母亲的手,认真地发问:“妈,祖父祖母死后上哪里去了?”
“上天。好人上天,坏人下地。”母亲胸有成竹地微笑着,理所当然似的。
“死后不是都埋在坟里吗?”我执拗地问。
“那是身体。还有灵魂,公公的灵魂上天了。”妈说。
“妈,人迟早都会死吗?”我惶恐不安。
“坏人的死,是永久的死;好人的死,是到比人间好得多的天堂里过日子去了。”母亲说得那样的自然、畅快,竟在我幼稚的心灵里顿扫对于死亡的恐怖,并强烈地产生了做个好人、永生不死的希望。
又是一个清明节。我又来到公鸡岭上,祭奠双亲,拜扫父亲的老坟和母亲的新坟。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惟此两三辰。冢头莫种有花树,春色不关泉下人。但野草却长得繁荣兴旺,绿染春山,无论如何,泉下的母亲是喜欢蓬勃的春草的。此时,我又想起了王安石的《孙君挽词》:“丧车上新垄,哀挽转空山。名与碑长在,魂随帛暂还。”母亲的灵魂不必随帛暂还,原本就在碑下,就在山上,就在云间,就在我的心里。
一生身是寄,百岁去如飞。杜牧曾低吟:“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杨慎更深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母亲虽不曾领悟过如此诗情,但她启示过我——人,是捏着拳头来出世的,空手而来,活着时,总想抓点什么,可是到死的时候,手是撒开的,什么也不抓了,人人空手而归。生无带来,死无带去呵!母亲的启示使我领悟到——每一个人,当他降生时,总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周围的亲人却笑着欢迎他的降生;而当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周围的亲人们在哭泣,在哀伤,他自己却应当微笑,应当宽慰。为什么呢?因为,哭着生来,是意识到人生的重任;笑着死去,是庆贺完成了人生的重任。
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母亲的一生,平凡而又坎坷。
1910年,母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私塾教师家庭里。外公是深受乡民及弟子们爱戴的私塾先生,一生教出了许多出色的弟子,屡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母亲从小接受外公的教诲和私塾的熏陶,但也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未能免俗,没能读完私塾,只跟着外公粗略学了一些文化,也算颇能断文识字了。在我的记忆里,她能够读信读报,也能写写信,而更拿手的是读歌册。每逢闲暇之时,左邻右舍的老婶老姆、嫂子媳妇和姐妹们便聚拢到“四点金”院落的厅堂里,围着我母亲。此时的母亲,真是神采奕奕、满面春风。她戴着眼镜,捧起歌册,一句一句地朗读起来,而那腔调与韵味,又分明像在唱歌,正如潮州话所说的“唱歌册”。什么“薛仁贵征西”、“杨令婆辩十本”……
母亲的人品,亲友们是有口皆碑的。那时候,家境虽不算很穷,但也不宽裕。然母亲持家有道,省吃俭用,时常接济邻居与亲友。为了解除亲戚与好友的忧患,母亲毅然先后收养了原本穷苦无依的两位姐姐和一位哥哥,虽然给家庭经济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但母亲咬紧牙根,步履艰难地承受了下来。
三
潮阳的老屋早已破旧不堪。母亲苦心维护,居住了多年。在我家迁离潮阳到汕头定居之后,潮阳老屋又经年借给亲人居住。
汕头市中山路的房子也是破旧的,贝灰砂结构,楼下的前墙全是木板,二楼的前墙则是假墙,连同阳台和小厨房共三十多平方米。一家八口人住下,紧巴巴的。好在我家在屋后用竹篷和木板搭建了八平方米的后间,屋前又用木栅栏围了十几平方米作为前庭。庭里有一棵巨大的苦楝树,每至晚春初夏,那苦楝树便是满树冠的绿叶簇拥着满树冠的盛开的紫白色细碎的花朵。在幽幽的花香里,生活着通体漆黑而双翅缀满白点的美丽而活泼的甲虫——苦楝牛,那长长的、弯曲的黑白相间的触须,那强健有力的双翅和那对锋利异常的门牙,以及八条能够紧紧攀附人手的强劲的美腿,使它浑身充满生机与活力。苦楝树和苦楝牛那美好的形象,早已深深地刻烙在我的童年和少年里,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欢乐与情趣。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懂事以来,便清楚地知道,同当时的许多家庭一样,我家是贫困的。在旧家俬店工作的父亲,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一元五角钱,光靠这份工资赡养八口之家是非常拮据的。于是,竹篷和木板搭建的八平方米的后间出租了,每月便有了两元租金。我的哥哥阿憨三岁时,遭受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惊吓,得了严重的精神病,终其一生而不治,书不能读,活不能干。在他十五岁时,某夜彻夜不归家,全家人四处奔走寻觅,第二天终于发现他失足溺死于市郊的一个池塘里。此前,最小的妹妹又死于白喉症。家中除了父母,就只剩两位姐姐、我和妹妹了。而比我们大得多的两位养姐,早已嫁人。为着生计,十四岁的大姐已经在织席厂做了三年工,而十岁的二姐也在织席厂做了一年了。妹妹还小,全家只让我读书。
多年来,家庭贫困的状态一直延续着。日常三餐,全家人难得吃一顿干饭。有时候,母亲也用竹制的饭戽斗,在稀稀的粥汤中为父亲捞一碗干饭。可当父亲吃饭时,他总是将大半碗干饭分给饥饿的子女们,尤其多分点给我,甚至连菜都分给我们。其实,由于太穷,母亲留给父亲的菜也不比我们好多少,通常是一盘芥蓝菜或空心菜,两条巴浪鱼或几片猪头肉。不过,对于饥肠百转的我们来说,这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1960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父亲得了水肿病。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每月可以得到少许特殊供应的糠饼。糠饼本是治水肿病的,但对于饿得发慌的我来说,却奇香无比。每当父亲背着母亲悄悄塞给我糠饼时,不懂事的我便吃了起来。有一回,母亲发现了,又吃惊又生气,一把从我的手里夺回糠饼,交还父亲,刚开口责怪了我两句,便呜呜咽咽哭了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我知道错了,伤心地大哭起来。父亲也满脸泪痕。全家人哭成一团……
贫穷紧紧跟随着我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近乎半工半读了。从割青草、拾柴火到拾菜叶、挖地瓜,从拉车运煤到赶海抓鱼,我在读书之余,便刻苦干活,以微薄的收入聊补家用。
父亲死后,母亲又重病在身,而我又下乡海南。家境更加穷困了。而破旧的房屋又已成危房,非维修不可。没办法,家里只好压缩楼下十几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出租后以租金修屋养屋。当时杉木起价,据说一斤杉木等于一斤猪肉的价钱,于是将楼下前墙的所有大木板拆下来卖掉,砌成了便宜的土墙,一样挡风防盗,一样过日子。
有一位老朋友要修房,看中我家已经拆下的那一对大片的杉木门板,那时候就是出高价也难以在市面上买到,但他又不好意思开口要。我明白了他的心思,主动将那对大门板运送到他家,逼着他收了下来。另一位朋友修屋,正好缺一根大杉梁,到处寻买,一时也买不到。我悄悄运用力学的物理知识,计算了一下,认定可以从家中拆下一根受力很小的大杉梁,并不影响老屋楼板的承载力,于是将那根大杉梁拆下来,运送到他家,说是家中多余的旧杉梁,让他急用再说。他非常感激,及至使用后一年,他才偶然发现了秘密,又负疚又生气,竟一时说不出话来。第二天,他病了一场。天哪!
四
尽管家境贫寒,但父母对于我的学业是倍加关注的。父亲就曾经给我讲述了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故事:解放前,某乡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目不识丁。一次,乡绅郑爷笑吟吟地请农民顺路带信给乡公所。信没有封口,一字不识的农民将信带到乡公所,所长抽出信纸一看,立即叫乡丁将农民抓起来,农民大愕,不知所措。所长大笑起来:“信里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你欠郑爷的地租至今未还,郑爷让我抓你的。你这头青盲牛,自己来送死,可笑,可气,可怜呀!”农民自知窝囊废,只好束手就擒,俯首听命。
这个辛酸的故事,常使双亲长叹不息。
在双亲的激励下,我刻苦用功,年年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又从少先队中队长当到大队长,从学习委员当到班长,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初中二年级时,还门门满分,老师带着同学们,敲锣打鼓,到家里报喜来了。全家人多高兴啊!邻居们也投来羡慕的眼光。当晚,母亲特意煮了一顿干饭,还有鱼、有肉、有菜,全家为我庆贺哪。
就在我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之后,父亲却不幸病倒了。一家人倾尽全力医治和护理父亲,但时运不济,数月之后,父亲终于撒手西归。走时只有五十九岁。
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正是大雨滂沱的清明。母亲毅然领着我上山祭拜。借着雨伞的掩护,娘俩一而再、再而三地划火,一盒火柴都快划完了,才终于点燃香烛。等到祭拜完毕,母亲和我就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似的,连连打着喷嚏,这不正是父亲思念我们的亲缘感应吗?真是天应地灵呵……
我们苦涩的泪水掺和着淋漓的雨水。父亲呵,您在天之灵既有感应,为何白居易还要低吟“冥寞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呢?
也许,对于人生,我依然似懂非懂,不过,我也明白,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岁去人头白,秋来树叶黄。于是,便有了“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生命景象,实在无可奈何啊!惟有惜时如金,方能终老无悔。
难偿世上儿女债,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的双亲,对于养子和养女视同己出,并无二致。不仅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健康成长,而且为他们的婚事尽心尽力。他们之中,尤其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远嫁香港的大姐。
全家人谁能料到,做了四十年的长长的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在那迢迢千里的地方由姑娘变成了老太婆的大姐就这么实实在在地站在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