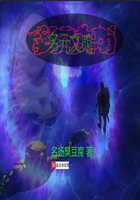好莱坞商业意识形态的第四个特征是作为意识形态错综复杂并置、妥协的产物,建立独特的意识形态“共鸣叙事”。吴宇森在《变脸》获得成功后所说:“要拍一部国际性的电影,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他们的思想行为,但是我拍电影的一贯方式是希望尽量找出我们一些共通之处,不论我们来自哪个地方或哪个民族。譬如我们中国人,不管是来自香港、台湾还是内地,我们可以找到共通的所谓‘仁义精神’。至于西方人,我也希望能找出我们之间的共同处,他们也有一种‘仁义精神’,也喜欢帮助别人,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外国人比较含蓄,中国人则比较豪放。在《变脸》里面我找到一个相通点,就是大家都有的‘家庭观念’”转引自《电影世界》1998年第6期。也就是说,共同的精神/心理及其结构可能包括人类共同的情感,如家庭、爱情、婚姻、亲情、友谊,人类共有的问题困境,如青春、善恶、生命、死亡、存在、毁灭等,也包括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共鸣点。好莱坞这种共鸣叙事正是非好莱坞电影生产者所迫切需要借鉴、学习的,但非常奇怪的是,无论欧洲还是亚洲恰恰在这个方面做得最为不够。比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仅在国内电影市场上票房成绩颇佳,而且在各类国际B级电影界上多有收获,如此官民同喜、中外皆爱的影片却并未受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者的认真对待,以期从中找出克服中国电影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市场/艺术分裂产生的文化焦虑手法,大而言之,从周晓文的《最后的疯狂》到冯小刚的“贺岁片”现象,我们最缺乏的不是对于电影艺术的研究,而是对于电影共鸣点、共同点、结合点的研究,寻找包含共同的精神/心理及其结构应该成为电影生产的基本规则。
中国影像生产的商业化已经运作了多年,那些充满表面商业化元素的影片其实也不少(表面商业化元素就是凶杀、爆炸、打斗、性等廉价的“卖点”符号),为何总难商业化起来?原因有多种,就本章论述的中心角度看,与我们没有找到将民族意识形态内容商业化的最佳途径密切相关,纵然我们身处全球化的普遍化浪潮中,我们所需要的商业化也不仅是移植好莱坞电影娱乐的表面商业元素,而是要将民间的愿望通俗地讲解出来、将大众的困惑故事化出来、将大众的理想愿望虚构化出来,从而拉近娱乐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影者从中看到自己的历史和未来,如此,电影中才能包含丰富的大众梦想,电影才能成为大众欲望的表达,电影才能市场化并受到市场的礼遇。因此,如果仅仅看到市场和金钱的密切关系,而忽视了市场意味着广大人群意识形态核心观念的复制和表达,那么,市场难以形成,更何来壮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进行中西娱乐艺术生产比较,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娱乐生产者对于人性、人道的坚持是十分理论而单面化的,娱乐中的人道叙事要么对立分明,要么片面黑暗化。正因为如此,尽管第五代乃至第六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声誉,其娱乐仍不能引起本土大众的热烈回应,因为在其中,大众难以窥视到完整的自己的意识形态形象,难以建立有关自身民族的整体文化身份,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看待这种生产者的产品。
从好莱坞的商业意识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商业意识形态就是商业影片中贯穿始终的本土文化基本价值观念体系,这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固、恒定而不变的,是支撑商业影片的内在思想结构也是商业影片进入大众心灵的基本手段和渠道,如果商业影片要挑战或者背叛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它就会冒失去大众市场的危险,因而是否具有或者是否能够建立一种有效的商业意识形态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娱乐艺术中商业意识形态建立存在与好莱坞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中国这种现实环境中,商业意识形态首先必须体现革命、政治能够承认并认同的意识形态并把它们当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建立稳固的消费基地,然后在此基础上寻获大众意识形态构成元素,在革命、政治、商业之间建立其合理的商业意识形态体系。阿多诺认为,“什么地方存在着纯粹直接的权力支配关系,什么地方就没有意识形态”马丁·杰:《阿多诺》,第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话的确适用于某种情况下的中国,但在WTO时代,革命、政治和商业意识形态建立和谐共存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可能了,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政治已经不可能依靠行政手段建立市场,它必须市场化地运作其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承诺中事实上正在把政治文化化为一种民族国家文化精神观念、哲学、神话和理想模式的代言人,这种政治的宽泛化为商业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传统狭隘化的政治标准。
从WTO文化传播角度言,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正成为一个愈来愈焦点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使得一切制约娱乐艺术生产的不适宜机制正在被淡化或取消,商业影片虽然不可能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核心,但作为一种传播范围最广泛的手段,作为最容易吸引大众眼球的形式,对民族娱乐艺术市场的形成和健康发展显然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如果徘徊在政治和商业之外的大众逐渐失去对娱乐消费市场的兴趣,转而依靠进口的娱乐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一旦大众变成一块漂移的异域“娱乐文化居民”,民族娱乐艺术市场也就随之消失了,这种局面对于民族文化群体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益处,因此,民族娱乐艺术市场的建设氛围自然也会形成一种有利于商业意识形态确立的基础或前提。
当然,任何盲目的乐观都是一种一厢情愿,基于商业化娱乐艺术生产的商业意识形态能否建立还取决于各方面的努力。关于电影体制的问题,尹鸿有很好的论述,他指出,“电影改革与20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的进程相比似乎并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成果,不仅电影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仍然不适应文化产业化的发展,而且正如一位电影政府主管人士所说,‘有人说中国电影企业是整个中国企业界改革最早的行业,但是,改革的进程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中国电影业仍然面临‘体制不顺、机制待立、中介梗阻、节目短缺、资金困难、捐税过重、不平等竞争’等问题。直到90年代末,垄断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仍然在深层上制约电影的发展,公平的、开放的竞争体系的建立远远没有能够实现。电影体制转化的缓慢,不仅造成了发行和放映业的冲突,而且严重地影响到制片业的利益。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在中国,各制片单位的平均销售收入实际只占票房收入的22%,70%的国产影片制作方亏损,如此低的投资回报率必然会影响到电影的投入再生产。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电影制作部门的生产主动性,电影投资和生产的危机在90年代末可以说有增无减。
自然,真正制约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关键还是管理观念和制度的转型。在中国,电影曾经长期被简化地理解为政治宣传手段,被强制性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载体来管理。进入新时期以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化本性,逐渐开始被认识和部分认同,一方面,政府的电影管理观念和政策都作出了某些调整,电影与政治的关系逐渐具有了媒介和文化的相对独立,娱乐性影片和一些非主流影片也具有了一定的存在空间;但另一方面,电影仍然还是被看作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电影活动的空间仍然相当有限。所以,相关政府机构在用经济手段支持代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生产的同时,也通过法制化和行政化的方式规范电影生产。
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手段,政府有关机构近年来建立了相应的电影管理法规,如电影审查和检查制度、电影许可证制度以及一些临时性的题材和内容上的限制性规定。这些法规,对电影作出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制约,规定了一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共性,从而将电影纳入了整个社会主流文化的塑造工程之中。
但由于这些法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含义的可再解释性,在某些时候对电影题材、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的限制缺乏可参照性,某些规定和制约也缺乏文化层次,与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文化特性还存在一定距离。结果,不仅使中国内地电影受到的公共性(政治/政策/道德/传统/习惯)限制比世界其他主要电影生产国家和地区相对严格,而且也比在大陆放映的海外/境外进口影片更为严格,甚至比国内的公共电视的限制都更加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宣泄和疏导潜力,这不仅弱化了电影在竞争激烈的大众文化市场上的占有力而使电影的融资能力、投资能力下降,同时,也使得大陆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面对现实的开放性和电影观念、形态和风格上的多样化、层次性。而与此同时,电影管理机构利用政府性的电影基金和其他种种经济手段以及各种行政规划来扶持的主流电影生产虽然完成了一些具有较完整的艺术形态和形成了一定市场回报的影片,但由于各种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制约,这些计划性的电影生产却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或者违背电影的生产和创作规律的现象,特别是曾经已经被人们所遗弃的“题材本位”倾向和“概念化”倾向又有所泛滥,前者造成了题材上的单一性、重复性,而后者则造成了电影美学上的平庸性、教化性。电影的指令性行为与艺术性行为、经济性行为之间常常缺乏有机缝合,这使得多数“主旋律”影片在艺术上、在市场上乃至在意识形态教育上都没有获得想像中的传播效果。尹鸿:《世纪之交:90年代中国电影备忘》,《当代电影》2001年1期。不过,在我们看来,商业意识形态建立不是一个“等靠要”的事情,而是一个商业电影自身的认识问题,因为即使在好莱坞也不存在完全的政治正确,所以中国商业电影的成功有点需要像胡雪岩那样的存活手段,在间隙中寻找空间,就当今的时代而言,这种间缝已经有了很大的活动空间。
总之,对中国影像娱乐生产而言,它迫切需要一个属于自身的阐释系统并在这个阐释系统的支撑下可以连续不断地生产商业影片,更深入地说,应该每一种商业类型影片都要像好莱坞影片一样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西部片的文明与野蛮、英雄神话、种族对垒,爱情片的永恒浪漫、等级差异、性别独立与依附,惊险悬疑片的威胁、焦虑、恐惧、危机等社会心理矛盾情结,黑色电影的犯罪、暴力、非理性、人性恶……只有各种类型化的意识形态表述确立才能真正达到商业意识形态的完善和成熟,也才能为大众提供一个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天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像性关系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