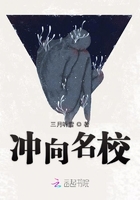苏牧云一愣,刚飞到脸上的红霞更重,不过也不是害羞了:“你给我滚!臭流氓!”苏牧云把手里的衣服直接就扔在齐烟山身上,齐烟山能轻巧的躲过齐秉锐连续几次无耻的偷袭,却躲不过苏牧云一次轻飘飘的衣服,任由衣服砸到身上。齐烟山一把把砸在身上的衣服抄住,然后低头一看,娘哎,齐烟山感觉气血一热,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鼻子淌了下来。苏牧云此刻才看清刚才扔过去的是什么,她啊的大叫一声,猛地冲过去,从齐烟山手里抢了过来,又扔到了盆里。
“滚!你个臭流氓!”苏牧云气冲冲的瞪着这个看似在擦鼻血,其实是在闻手里味道的色胚子。
“呃?这个不怪我啊,我不是故意接住的,再说我,那个,这是今天刚摘的杏,已经洗好了。那个,嗯,我先回去了。”齐烟山小心翼翼的捂着鼻子,把竹篮子放在门口台阶上,偷偷瞄了苏牧云一眼,慢慢的转身朝外走。
“不是让你向外滚,滚屋里坐着等我洗完!”苏牧云气呼呼的说道,脸上的红晕更是一刻也没有下来。
“哦。”齐烟山乖巧的又转回来,低眉顺眼的朝屋里走去。
齐烟山刚背过苏牧云去,立马贼眉鼠眼的笑了,而苏牧云则朝着齐烟山微微耸动的背部,狠狠挥了挥拳头。齐烟山快步拎起竹篮子,掀开门帘,在客厅站了一下,直接就进了苏牧云的房间。
等了不到五分钟,苏牧云就进来了,看到客厅没人,赶紧去了自己的房间,一看齐烟山老老实实坐在凳子上,暗暗松了口气。却是不知道,齐烟山刚进来之后的无良行为。
“你怎么不在客厅坐着,到我房间里来干嘛?”苏牧云走到跟前,接过齐烟山递过来的竹篮子,笑眯眯的盯着齐烟山,眼睛弯成了一道月牙,然后拿起一颗杏咬了一口。
“杏好吃吧,今天刚摘的。”齐烟山被看的心里发毛,然后避开苏牧云的视线,假装扫视了一下房间,虽然他在牧云没进来之前,已经仔仔细细的看过了。
“不许乱看,臭流氓!我爸妈快回来了,咱们出去坐着吧?”苏牧云难得细声细语的跟齐烟山说话。
“你是怕我把持不住,还是怕你把持不住啊?”齐烟山在凳子上起来,直接坐在床边,然后顺势躺了下去。
苏牧云放下手里的竹篮,嘴里吼了声滚,然后就要过去拉齐烟山起来,齐烟山则是从床上滚到另一边,打算在这块根据地常驻了。苏牧云转到另一边,抓住齐烟山的手,就要拉他起来,不料力气不够大,不仅没拉起来,还把自己也挣倒了,然后就倒在了齐烟山的怀里。
齐烟山懵了,他觉得他坚守了十几年的贞节被败坏了,于是他在苏牧云要起来的时候,双手用力把她拥在怀里,嘴里还念叨着:“真这么着急?咱爸妈一会儿可就回来了。”
苏牧云挣扎着要起来,却抵不过齐烟山的双臂。而此时,齐烟山看着身上这个打小一起玩的伙伴,他很久没有好好打量过她,都不知道她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那个跟着他一块下河捉鱼爬树掏鸟的小丫头了,齐烟山仔细的看着苏牧云的脸,甚至感觉到牧云皮肤上细细的绒毛在轻轻呼吸,此刻红晕再次弥漫在牧云的俏脸上,而她长长弯弯的眼睛此刻有些颤抖着看着齐烟山。齐烟山顿时觉得,自己的身体里那头潜伏起来的野兽睁开了他凶狠的眼睛。
齐烟山双手环抱着苏牧云,扭身将其压在身下,嘴巴狠狠的印在了牧云好看的唇上。苏牧云绷着嘴巴,全身更是紧张的在颤抖,而她睁着眼睛里却映出泪水,犹如一汪清泉,映照出世间形态。齐烟山看到牧云的眼泪,陡然结束了他手忙脚乱的耍流氓行径,立马站起来,然后更是手足无措的看着流眼泪的苏牧云。
此时大门外边有隐约的声音,好像是苏牧云的父母在说话,齐烟山看着哭出声音的苏牧云更是慌了神,匆忙对着苏牧云说对不起,而牧云听到对不起,则如六月里止不住的下雨云彩,一道闪电后紧跟着一声轰鸣声,再然后就是耳鸣不闻的滴答落雨。
齐烟山此刻真的慌了,脑子里只印着牧云那双含泪的眼睛,以前不是没见过牧云哭,甚至大多数是他自己把她欺负哭的,可是每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让齐烟山心慌。在他看到她清澈的眼睛里眼泪真的如窜珠般时,他心里更是仓皇如逃窜的野狗。
齐烟山木然的回到家里,没有跟母亲打招呼便进了自己房间,他坐在床边,懊悔的伸出双手插进头发里狠狠挠了挠。原本以智谋自诩的齐烟山此刻没了头绪,这时的齐烟山更是感觉自己懦弱,平日齐大炮便说齐烟山行平常事如意,行非常事往往不堪,但凡心里藏着乾坤,也早就不用如此费尽周折,于是平日里齐大炮便将齐烟山放出去,琢磨着如何给孙子挖坑。
此刻齐烟山内心天人交战,不知该如何跟家里人说,今年齐烟山才堪堪十七八岁,想不了太多深刻的道理和办法,他现在只是在想苏牧云的家人知道了会怎么做,他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自己家人知道了会如何,是否会带来不良影响,辐射范围再广一点,周围的人知道了会怎么想。齐烟山自小就有强烈的家族荣誉感,小心仔细的维护齐家在麻姑镇上的声誉,这使得齐烟山在这边的名声相当好,时不时的有大人人领着儿子或者女儿找到齐大炮,说被齐烟山打了或者欺负了,齐烟山一般听到这些话,如果是男的,心里就恨恨的想,活该,如果是女的,就觉得老子现在还是处男呢,怎么就欺负你闺女了。
在齐烟山胡思乱想的时候,齐妈妈张荽在外面喊了声齐烟山,说让他去二爷爷家有事。张荽见齐烟山没有反应,径直推门进来了,看到自己儿子木然的呆坐床上,不知在想什么,便过去伸手扶住齐烟山的肩膀,轻声问了一句。
齐烟山在想要不要给父母说一声,自齐烟山记事起,家里就只有爷爷和妈妈,爷爷每日百般折磨齐烟山,使得齐烟山有些怕这位老人,也就是现在长大了,才稍微有些男人的脾性,敢与爷爷顶针,而每每齐烟山问起父亲时,张荽则转过头暗暗叹气,齐大炮更是火起,硬声硬气的扔一句早死了,然后进到书房里关上一天。所以,齐烟山一般是大事跟爷爷说,小事跟妈妈讲。现在齐烟山也拿捏不准这个事是大事还是小事,心想要不含糊的当成小事吧。
张荽听儿子说完,心里则暗叹了声,都说子随父,真是不假。齐烟山见母亲怔怔不语,暗自出神,拉了拉胳膊。张荽看了一眼儿子,心里暗道长的也一样,看儿子一脸着急,说这事先不着急说,等爷爷回来商量。然后让齐烟山先去二爷爷家,并且嘱咐去了先不要说这个事,等回来再说。
齐烟山应了一声就走了,而张荽则看着儿子的神情有些担心。
齐秉锐与齐秉昆抽完第三袋后,还是一语不发。齐秉锐挠了挠稀疏的头发,暗叹了口气,拿出了石桌下面的象棋,然后一一摆上。
“十几年就这么过去了,自打老四没了之后咱哥俩就再也没下过棋,今天给你个机会,让你好好的折磨一下我,也出出你这积攒了多年的怨气。老规矩,执黑先行,我先来。”齐秉锐也不等齐秉昆回话,便摸起自己的炮走到正中。
齐秉昆不搭话,自顾自的坐在凳子上,木然的脸上此刻终于显露别样的神情,眼神望向远处,似是在回忆往事。
齐秉锐着急的拐了一下齐秉昆:“走棋啊!”
不料,齐秉昆突然涨红了脸,冲齐秉锐吼了起来:“你我架炮甩车拐马,托相拜士,拼尽最后一卒,仍敌不住对方一子未动,隔岸明将,将死,死棋!我们这已经耗费了多少年,折了多少儿郎,现在又要把齐家子孙放出去,齐大炮,别人养你我十年,你我报恩三十年,不够吗?”
“老二,你到现在还不懂啊,你还是不懂。”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齐家就要遭殃了。你亲儿子都不敢趟这浑水了,齐大炮,你非得如此吗?”
“老二,老三王野鹤二十年前曾帮我选好一块墓地,说山河流转,气运转变,二十年后有大气运,我埋首于此,福泽子孙倒是不求,只求了心愿,还因缘。受人恩惠十年,我们还不了便要子孙还,谁也赖不掉,这盘棋,终究还是要继续下去。至于他,我就当没有这个逆子。”
齐秉昆摇了摇头,暗叹一声,终究还是拿起棋子,扶鞍上马,御车征战。
老哥俩都是江湖里的老油条了,布局绵长阴柔,徐徐图之,出击则杀伐果断,直指将帅。一局棋还没结束,齐烟山便推门而入,见得两位老人正在下棋,乖乖站立一旁,默默注视棋局。齐秉昆棋力稍差齐大炮一些,正准备进车占肋,胁迫抽棋时,听闻齐烟山突然连连咳嗽,猛然警觉,把拿起的车又放下,仔细打量起棋盘,而后胸内了然,回车看家,跳马跃进,携炮入底,配合悄悄溜进来的卒,活生生把齐大炮的一番经营给毁了。齐大炮看了一眼齐烟山,奇怪的是没有暴起敲打,而是默默不语的重新摆放棋子。
齐烟山看到两个爷爷下棋,就把刚才的事情忘了,毕竟少年心性,定不下来,也幸好齐烟山在齐大炮的日日蹂躏下,悟性也是不错,不然还真看不懂这俩个老狐狸的斗智斗勇。齐秉昆看齐大炮在认真摆棋子,便抬起头嘿嘿对着齐烟山一笑说咱爷俩今天把这老家伙赢跑咯,齐烟山也没避讳观棋不语的规矩,二话不说便从中间位置挪到了齐秉昆背后,以二敌一的意味很是明显。齐秉锐看到这个架势,笑眯眯的说道你小兔崽子怨念挺深啊,看今天不把你们爷俩收拾了!而齐秉昆这时也就看不到背后齐烟山的微妙模样了。
于是齐秉昆在齐烟山的加入下,大胆放手,凶猛进攻,死不悔改,华丽丽的连输三局,之后一脸恍然的表情,嘴里念叨着大意了,让个雏给糊弄了,然后一抹棋盘,把已经摆放好的棋子打乱,不玩了。
齐大炮和齐二旺走进屋内,招呼着要喝茶,齐烟山收拾完棋子,然后又去摆弄茶具。用南山上的山泉水,以柴火烧开,趁着滚烫,冲泡附近产的乌山茶。齐大炮喝完第二泡,放下杯子回去了,让齐烟山在这边待着好好伺候着跟二爷爷喝会茶。
还没喝完第三泡水,齐大炮就又匆匆的跑回来,瞪了一眼坐在下首的齐烟山,齐烟山此刻小心翼翼的又给齐秉锐倒上茶,齐大炮一口喝下去,对着齐二旺问老苏家人怎么样。齐二旺瞄了眼齐烟山,笑眯眯的端起茶杯,三指护鼎一饮而尽,而后不言不语转着茶杯细看上面的细小暗纹,指了指上面的图案闷声道雕纹入股,当得玲珑心思,却不通透,不过也是块璞玉,值得下一番功夫。
齐秉锐又是一口喝尽精致茶杯里的水,也学着齐二旺的姿态,也不看齐烟山说道明日去提亲,你去道歉。说完也不理会齐烟山,就又一阵风的走了,留下一脸错愕的齐烟山和恢复木然神态的齐秉昆,相对无言,默默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