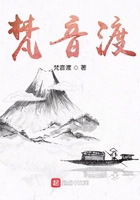反腐败与忍让腐败,实际总在纠缠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个更可怕?是腐败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是宽恕李侍尧这样的贪腐者可怕,还是将其一网打尽可怕?置腐败于何地,粗看是反贪坚决不坚决的问题,其实与如何治国相关。《清史稿》曰:“人君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爱憎喜怒,屈法以从之,此非细故也。”诚哉斯言!可惜仅是史家如此认为,乾隆们却未必持此识见。
容忍度
在清朝统治史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一直都警惕贪腐。放大一点说,不仅清朝,任何一朝帝王都知道贪腐是蛀蚀皇朝根基的恶劣行为,因此大赦天下时都不包括贪官污吏。然而,警惕归警惕,重视归重视,贪腐现象仍很普遍。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到吏部视察,专门谈到对官员的考核情况。他对那里的官员说:贪官何其多呀,这些家伙平时侵渔小民,当遇大察考官之年,也会小心谨慎。大学士范文程等人说,贪贿之人未做官的时候,也知道不该做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见利忘义、利令智昏。顺治说:这都是因平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如果持守有定,怎么能被金钱财物所诱惑呢?
顺治十一年(1654年)四月二十七日,吏科给事中林起龙给顺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也是对贪腐的探讨。其中说:州县官员所以贪污有三条缘由:一是日用之累;二是媚奉上官之累;三是曲承差使之累。林氏所言着眼于当时的现实。他在奏折中请皇帝对官员严加教诲,使贪官痛改前非,各尽职守。同时乐观地认为,如此一来,则大法小廉,太平可致。显然,林起龙的话颇合皇帝的心意,顺治闻奏后,命令有关部门研究讨论。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许可以推测出顺治皇帝对付贪腐的措施。严肃考核,做好思想工作,提高官员待遇。不过,这未必管用。清朝不仅没有从贪腐的泥沼中挣脱出来,而且后世子孙一代腐过一代,难以自拔,和珅大案即为明证。约略说来,和珅一案有三点使平民百姓特别震惊:一是涉案金额之大,二是作案时间之长,三是他与皇帝距离之近。做过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将吏法言》中说:“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后,和珅尊宠用事,以聚敛自丰。是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辈,赃款动至数百万之多,皆恃和珅为奥援。用事二十余年,康、雍、乾三朝之气,尽斩丧于一人之手。”其实,和珅敛财的本领再大,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面前,也属于奴才,说拿下就拿下了。况且,任何人也没有办法一铁铲挖一口井,一下子贪污几亿两银子,和珅的脏手肯定已经伸了不知道多少次,但从不被捉。乾隆是何等人物,居然酿成如此局面。不用“姑息”、“纵容”等词汇,万难解释这种奇离古怪现象。
从根本上讲,专制皇朝不容易解决一个“贪”字。因为酿造贪腐社会风气的原因,在于专制制度本身。如果官员的命运是由身居高位的上司决定,而这个上司又只受皇帝本人的监督,实际上一切监督措施只是具文,都不存在了。这就为贪赃枉法之辈千方百计寻求一个手握重权的人作靠山提供了动机,十分自然地,社会风气、政治风气也就日益糜烂。古今中外,贪污腐败为共有的现象,但像清朝后期那样贪污成为常态,几乎无官不贪是极其少见的。试想,和珅的贪黩,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尽人皆知,却在乾隆去世后才事发,这个皇朝如何不破败!腐败之事,俸禄低只是一个借口,哪里是真正原因。
据说,顺治非常崇拜朱元璋。顺治十六年(1659年),皇帝定下惩罚措施,曰,贪官赃至10两者,痛打40大板,流放到席北(吉林省境内)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衙役犯赃1两以上者同样流徙,赃重者处以绞刑。这些条例,不由让人想起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律令虽严,却仍然遏制不住贪风蔓延。
揭露官员贪污案的多与少,与老百姓耳闻目睹的贪污行为并不是一回事。世人知晓的那些案件都是被曝光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决定曝光概率的,又与反腐体制和容忍度相关。朱元璋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嗜杀成性,对贪墨者挺残暴。不能说这样认识不对,但失之于笼统。其实,在对贪污的容忍度上朱元璋超出大部分皇帝,几乎是零度容忍。他在贪墨还是清廉这件事上有洁癖,他总希望自己亲手打造的社会没有一个贪官,让下层人都过安定的日子。所以,他容不得官员有丝毫贪污,贪一点,就大开杀戒,几近变态。朱元璋慨叹:“我欲除贪官污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未尝不是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因此说,社会公布的贪官数字,很难说预示着什么,任何时候它都与朝廷对贪墨者的容忍度有关,与及时有效的监督有关。反腐成效,最直接的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而不单纯是数字。反腐措施起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先进制度的支撑。
身边人
时下的新闻中,常有某骗子冒充领导亲属行骗的消息。初闻此类事,似觉新奇,查诸历史,其实没有一点新意,旧滓泛起而已。
晚清时,陕甘总督乐斌的家丁陈二,就是一个招权纳贿,贪赃枉法,无所不为的家伙。别看陈二只是一介家丁,呼奴唤仆,十分自得。乐斌在四川为官时,陈二赴宴归来,必坐四人大轿提灯而回,衙役数人环绕侍候。乐斌做了陕甘总督以后,陈二的地位也随着攀升。陈二再娶,兰州各位官员都送了贺礼。结婚那天,候补文武各员都前去祝贺,奔走趋跄,甚于奴隶。成亲拜堂后,兰州知府章桂文、皋兰知县李文楷亲自秉烛送陈二入洞房,新娘则由和祥与章桂文的老婆搀扶。清朝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不无嘲讽与无奈地感叹道:“一堂鬼魊,暗无天日,不仅政由贿成也。”
陈二的事情虽与“行骗”无关,起作用的因素却完全一样。一个家丁,婚礼场面这样张扬,这般宏大,官员们趋附的是当事人陈二吗?非也!在于乐总督也!没有乐斌这张皮,陈二安有这样的毛?《左传》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兄弟也好,姻亲也罢;门生也好,故吏也罢;心腹也好,幸奴也罢,都是官员这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都是官员那张关系网上的网目。身为布政使的张集馨,不在乐斌织成的关系网上,处境就非常孤立,地位颇受威胁,竟生“决意引退,避其逆锋”之想。张集馨查办的案子,很多涉及乐斌,碍于各种因素,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所以说,陈二之流,虽然可恶,撑腰的则是总督乐斌,一些人趋跄若仆役,也是希望得到乐斌的遮蔽。前时,曾有落马的贪官解释情妇多的原因,自诩魅力无穷,讨女人喜欢。这种愚蠢至极的糊涂话,玷污了操守良好的妇女不说,也抬高了追逐金钱、权势的那些情妇。树倒猢狲散。无良官员不受制约,乐斌的陈二就会永存不息。
陈二只是官员身边的人之一,凡官员的亲朋故旧吏胥家丁衙役,都可归入这个类别内。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彰显着他们自己的品行,也可以透视出官场的种种作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说,吏、役、官之亲属、官之仆隶,这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清代的邵晋涵把幕宾、书吏、长随,作为对清朝“吏治”起实际作用的三种人,认为“官拥虚声而已”。清代的长随是什么人物?赵翼《廿二史札记》“长随”条曰,在明代,长随本来是那些跟随大宦官的小宦官。至清代,长随成为对官员跟班的俗称。实际说,不论官员身边的人怎样弄权,根子都在官员本身。从没听说哪位倒霉的官员仍有长随,仍有点头哈腰的逢迎者。
陈二们的做派,得益于长官的权力,陈二是“标”,长官才是“本”。陈二的行为,昭示制度的缺漏:地方官要保住乌纱帽并且升迁,就要建立自己的吏役队伍,编织庞大的关系网。这样上下遮罩、提携,便可视上司如兄弟,视考绩为无物,或将它作为打击、拉拢人的手段。上下皆这般操作,非一个乐斌如此。直隶总督桂良,卖缺受贿,劣迹昭著,“丑声载道,民怨如仇”,但因是恭亲王奕?的岳丈,朝中有奥援,便无人参劾。于是桂良越发有恃无恐,无所顾忌。细想,桂良与陈二只是地位不同,手段则丝毫不差。
因为没有实质性的监督,选才用人都是几个有地位的人说了算,陈二便有机会搂抱乐斌的粗腿,便可明目张胆贪赃枉法;乐斌因为上下有人赞扬、拥护,即使对公事例案不甚了了,也照样做官。晚清与入侵的外敌打了几次仗,最后皆以惨败收局,不是清朝皇帝不想胜利,也不是清朝老百姓不爱国,而是制度造成的各种因素使然。
倘说陈二的作用,他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大清的自负、荒唐与荒凉。
何尝知道是新机
对清王朝失去几次发展机会,表示惋惜的人不少。比如清朝入关初期,外国传教士汤若望颇受皇太后和顺治皇帝礼遇,但随着顺治帝病故,汤若望被攻讦,从而使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了。言外之意,倘若清王朝沿着顺治的路一直走下去,近代中国就不会落后于西方。其实,这是学者的慨叹,是坐在书斋里生发的良好愿望,也可以说是痴人说梦。那些权力人物哪里会这样走路?
顺治尊崇汤若望只是一个个案,就像李世民与魏徵君臣建立的关系一样,世人可以羡慕,也可以称赞,但那不是可以复制的君臣关系。就顺治和汤若望来说,是皇帝本人的个性和汤若望个人的能力造成的良好关系,也是清朝立国初期特殊情势结出的果实,而不是一种稳固的国策。时过境迁,这种关系便不复存在。顺治一生尊敬汤若望,可惜去世太早,不久汤若望便蒙冤了。
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治国方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存在很久了,清朝统治者不仅完整地把这一点继承下来了,而且还有光大之势。原因在哪里?因为这种治国方式所有的人(君、臣、民)都驾轻就熟,能给当权者带来最大的利益,没有任何法令,更没有任何人可以约束皇帝。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点野心的人都想当皇帝的原因。即使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还是舍弃大总统不做,做了几十天皇帝。辛亥革命后,人们的民主思想确实发芽了,这事倘若在清之前,袁某人很可能成功,但那时不行,这块土地上有了民主幼芽。不得已,袁世凯取消了帝制。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为什么干这等龌龊事?曰:利也。这个“利”
字,不单指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方面的。帝制培育的国民是低眉俯首的顺民,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统治,使原来的顺民又“顺”成了奴才,成了奴性十足的顺民。最后,民:不管用什么方式变成君之后,一如早先的皇帝;臣:不管用什么方式变成君之后,更是一如早先的皇帝。中国专制社会,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就变个皇帝,却万变不离其宗。“宗”指什么?是不是那个“利”字呢?
没有高深道德修养的人,抵御不了这种诱惑,只顾集团利益的人,不会痛击这种诱惑。顺治哪里有力量抵御这种铺天盖地的诱惑呢?不要说顺治,就是他的后代,哪里有一点抵御的可能呢?马基雅维里说,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他们不易为共和做牺牲,反而更容易被专制权力所网罗,为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成为专制的帮凶。
具体点说,顺治确实对汤若望很敬重,尊称他为“玛法”(满语,长者或爷爷)。1653年4月,又诏赐汤若望为“通玄教师”(康熙时为避讳,改“通微教师”)。顺治皇帝对汤若望介绍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感到十分新奇。可以说,汤若望为顺治皇帝了解西方打开了一扇小窗。不过,帝制培育的土壤是个创造奇妙事物的场所,顺治重用汤若望,别人干涉不了就不加干涉。但事情不算完,顺治死后再说。果然,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康熙即位。康熙三年(1664年),一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起诉汤大人,鳌拜等四辅臣支持杨光先。
杨光先列举了汤若望等人的三条大罪:其一是潜谋造反,其二是邪说惑人,其三是历法荒谬。杨光先认为,在中国传教的汤若望,有颠覆中国的阴谋,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73岁的汤若望此时已重病在身,肢体瘫痪,言语不清,由作为“同案犯”的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在旁代为申说,而汤本人根本无法向审判大臣解释。其实,不老迈就有解释的机会吗?即使有机会,解释又有何用呢?另据有的书籍披露:杨光先在控告过程中大施贿赂手段,他花费了白银四十万两,买通了许多办案官员,还施惠宝珠十八颗,堵住了一些人的口。其实不用破费,杨光先必胜——此一时彼一时也。治国策略总是随皇帝的更替而变化,就是同一个皇帝,也常常前期与后期大不相同。
刑部采信了杨光先的说法,将汤若望等人的罪名定为大逆之罪,并根据刑律拟出处理方案:将汤若望等钦天监官员凌迟处死;相关人员之子斩立决;不及岁之子、妻室、家人、地亩、财物等严查入官。四辅臣向孝庄太皇太后作了汇报,孝庄太皇太后非常不高兴,斥责他们说:“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岂俱已忘却,而欲置之死耶?”
孝庄太皇太后这些话救了汤若望,年逾古稀的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宣武门他的教堂里去养病。康熙五年(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逝于寓所,享年75岁。康熙八年(1669年)9月,汤若望得到彻底昭雪。
简述汤若望这一阶段巨大的人生转折,是想说,顺治重用汤若望不是清朝走入新路的契机,统治者们没那个觉悟。“机会”不是随处可见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倘若清朝统治者意识到过去曾经失去过机会,后来为什么在统治力已经日见其绌的时候仍然错失良机?况且,几千年培育的土壤已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习惯于固有的一切,习惯于争论“夏”“夷”问题。晚清时,郭嵩焘说了几句西方的好话,便惹来了满朝文武及在野士大夫的愤怒。卸任回到老家时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
那个岁月,据清朝开国的时间已经很远了,尚且如此,顺治时代人们的思想是何种水平,完全可以推测出来。专制带来的政治利益,必然也使经济利益附在政治这张皮上,从上到下贪污腐化且明目张胆。然后恶性循环,无视新的机会,贻误新的机会,扼杀新的机会。
缺欠
溯观前人的反贪行为,不仅律令的言辞不失严厉,而且特别重视对贪官的惩罚,“雷声”大,“雨点”也不小。比如,几乎所有王朝都不赦免贪腐之徒,异地做官的奇特之举更少之又少。然则反腐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常常按下葫芦浮起瓢。事情这般蹊跷,不免替古人担忧,生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之感。喜者,除了想过把权力瘾的皇帝以外,大多数帝王对贪污腐败恨之入骨,一生要拿出很大精力处理这件大事;忧者,自然与效果不佳有关。不少权力持有者,重视皇朝国力的培育而轻视反贪反腐,把净化腐败行为看作政权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固定程式,不能不反,也不可太反。于是,腐败成了弹簧,当掌权者的反腐力度加大时,腐败便慌张遁迹,而一旦环境稍变,它便横行于世。历朝反对贪污腐败的措施虽然有增有损,然而其效果却总在重复先前的旧迹,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