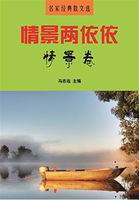在中国小说史上,冯梦龙(1574—1646)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虽然,长期以来,他被定性为通俗文学家,但这并不是十分准确的评价。实际上,他是一位扭转了宋元明以来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小说改革家。算得上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拓荒者。在中国,写小说者很多,但对大家读惯了的小说,无论内容无论形式,能实行一次根本变革者很少。
凡能行非常事者,必非常人,他决不是文学史上可以马马虎虎对待的人物。
中国的白话小说,始于宋代的话本。但从话本出现那天起,内容无非两端,主要是说史,其次为神魔、灵怪、烟粉、传奇之类。应该说,是这位冯梦龙,将旧的小说格局,引出神天鬼地,回到大千世界,瞄准帝王将相,关注芸芸众生。
这是极具勇气的创举。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14—15世纪的中国,由于作坊手工业的发达,由于商贸交易活动的活跃,初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开始萌芽,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便在城市中出现。与小农经济不同,这些城市中的有产者和平民,是一个涌动着消费欲望的群体。他们的文化需求,和躺在地头上由着太阳晒屁股讲两个荤笑话就心满意足的农民不同,他们渴望着美学价值高一些,文化品味强一些,以市井人物为主体,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学出现。
于是,冯梦龙的“三言”应运而生,扬弃话本小说中旧的讲史模式,遂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冯梦龙,江苏长洲人,在明代,江浙是经济最发达地区,因此,他能得风气之先,创新行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过,对这位具有前瞻性的小说改革家,文学史缺乏足够的估价。一个“俗”字,给他盖棺定论,是不甚公正的。
中国文人有一个通病,一旦衣冠楚楚,人五人六,马上就把裤腿放下,遮住未洗干净的泥巴,马上叼起雪茄当精神贵族,一张嘴,全是洋人的名字,一说话,全是西方的名词。中国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本土的东西,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下里巴人能够接受的东西,是不放在他们眼里的。这些人的文学史,必然就是圈子的文学史。
因此,别指望这本文学史里,会留张椅子给冯梦龙先生来坐,他哪有资格进到这大雅之堂?即使他捧上一大束玫瑰,诚心给圈子里哪位老太爷献花,门口一定有人拦住,你有请柬吗?休看他买了九十九朵玫瑰,但不是人家要邀请的一百位客人中的一位,他也只有吃闭门羹的份。
有文学,就有圈子,好者好之,恶者恶之,但只要圈在一起,必然是一个宗旨排外的团契。犹如海明威所言,像养在一个玻璃瓶里的蚯蚓,钻来拱去,互相以彼此的排泄物,抚慰着自己,做瓶子里的文学大师之梦。
好在冯梦龙识趣,不想干扰人家这种****似的自得其乐,何况他的事情多得很,日程排得很紧,一方面,他要下乡去采风,为已经出版了的吴下民歌集《挂枝儿》,再编一本《山歌》续集。一方面,他要马不停蹄地访遍江浙一带的书市,觅寻散佚的宋人话本。
因为,他要据其中“市人小说”的断篇残章,来撰写他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他的这些创新作品,订名为“拟宋市人小说”,算是有别于传统的新品种。“市人小说”,也就是“市井小说”。“市井小说”,也就是市民当主角的小说。对今天的作家来说,愿意写谁就写谁,愿意咋写就咋写,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五百年前,自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的规矩,凡小说,必讲史,成为金科玉律,要破它,需要一份胆量。
我钦佩冯梦龙这种敢于否定的勇气。否定一个两个前人,也许并不难,但否定几朝几代的定论,否定几百年来的规矩,在习惯听命,比较软骨的中国文人行列里,像他这样的抗命者,是罕见的。所以,明亡以后,一说于忧愤中死,一说为清兵所杀,便足证他的风骨。
站在嘉年华盛会门外的冯梦龙,探头朝里一看,瓶子里的哥儿们姐儿们正玩得开心,便不想打扰,伸手拦住一辆桑塔纳的士,上了高速,打道回府,奔长洲去也。
每个人都有他的快乐,只有最没出息的作家,最没起子的评论家,才能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我认为,冯梦龙的快乐,是他将大家已经习惯了的,文即史、史即文的神圣法则推翻,以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人和事,也就是活生生的,你熟悉,我熟悉,大家都熟悉的人和事,为描摹对象,这种另辟蹊径的快乐,这种颠覆传统的快乐,是作家的至高境界。他在这三部书中,改编,迻译,移植,更主要是自创了大量的“拟宋市人小说”,诚如一首赞他的诗中所说,“千古风流引后生”,《红楼梦》也好,《儒林外史》也好,“五四”白话文运动也好,甚至我们大家写的当代小说也好,溯本追源,最早是从他这条涓滴小溪开始,然后才成为滚滚巨流的。
我想他这种快乐,与跟屁虫得以列席某次盛宴的快乐,与写不出东西而穷折腾的快乐,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作家来说,创造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现在回过头去看收录在《三言》中的,每部四十卷,三部共一百二十卷的小说,无一不是呕心沥血,倾肠吐肝之作,这里面既有宋元旧制,也有明人新篇,更有冯梦龙他自己操刀的拟作。由于经过他程度不同的润饰增删,最后,神仙也分不清每一篇之由来,之所本,这就是大师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力。
中国台湾作家苏雪林说过:“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要老幼咸宜,雅俗共赏。像《今古奇观》那部短篇小说集,除二三篇艺术水准略差外,其余各篇,俗人读固觉有味,雅士读也觉有味,少时读是一种境界,中年读境界便进一层,老时读,境界更深一层。这便是耐读,耐读的作品,当然是好。《今古奇观》之所以好,是由于文人作家冯梦龙曾将其大加改作的缘故。”
其实,仅仅从阅读角度来肯定冯梦龙的作品,是不够的。应该看到,《三言》的出现,是中国白话小说由口头传述到文字表现,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分水岭,而小说,作为一门艺术,也是从《三言》起,在审美追求上才有了实质的进步。人物描写从粗略化到细腻化,故事情节从传奇化到现实化,语言表达从粗鄙化到文采化,章回结构从随意化到严整化……这一切,将冯梦龙看成一位通俗文学家,而忽略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显然是不公正的。
由于冯梦龙,小说从天上回到人间,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子虚乌有的神话世界回到身边和周遭的生活中来,市民阶层中的极其普通的人物形象,卖油郎、杜十娘、蒋兴哥、灌园叟,才能在小说中登堂入室。因此,他的作品,不但奠定了中国白话小说的写实主义传统,更奠定了文学创作中最宝贵的平民精神。因此,他为中国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迭出,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稀有。”这种讲史传统,是和我们这个民族容易沉湎于往事的国民性相关连的。
我们大家都读过的,南宋陆游的那首小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我们看到了露天晚会那熙熙攘攘的盛况,也看到了说书人将抛弃发妻的蔡中郎串演得如何有声有色。这个蔡中郎,据说为后汉末年的蔡邕,其实倒是冤枉了这位大学问家,他与那个第三者插足的家伙毫无关系。但赵家庄村民,曲终人散,月牙高挂,还在谈论一千年前的这个故事,意犹未尽。可见这种偏爱往回看的受众意向,是中国读者的痼疾。
英雄气短,美人迟暮,可从前代的衰颓中找到慰藉;春风得意,衣锦还乡,马上生出名垂青史的自负;老百姓看帝王之大卸八块,贵族之扫地出门,淋漓痛快而不亦乐乎;权贵们视江山之朝秦暮楚,朝廷之瞬息万变,殷鉴不远而赶紧捞取。黄钟大吕般的盛世华章,向隅而泣的末代哀音,振奋也罢,伤感也罢,对这个读《三国演义》,替古人掉泪的民族来讲,是永远的热门。
因此,在这样一个总体氛围下,15世纪的这场小说改革,那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冯梦龙在他深入地头田间,桑林茶园,从农夫牧竖,老妪乡姑那里搜集“民间性情之响”的歌谣曲调时,自然也在了解这些最基本的读者或听众,对于讲史类话本小说的倾情所在,说到底就是“故事”二字。陆游诗中那个赵家庄的村民,所以沉醉于盲人的鼓书中,是被蔡中郎的故事深深吸引。而历史小说,无一不是由密集的浓缩的色彩强烈的跌宕起伏的故事组合而成。
小说之本,为故事,小说的要害,也在故事。有了好的故事,也就有了好的小说。在英语中,小说又称story,而story,也就是故事。因此,冯梦龙以故事连着故事,大故事中套小故事,故事之外又有故事,旧故事引出新故事等等手法,来结构他的三部小说集****一百二十卷作品。他就凭他所讲的这些故事,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持西方小说观点的胡适,对这种故事加故事的中国传统小说写法,是不以为然的。在《宋人话本八种》的序言中,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以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胡适认为:“这个方法——用一个相同或相反的故事来引入一个要说的故事——后来差不多成了小说的公式。”
胡适是以西方小说观点,作出这个“公式”的结论,其实,真正掌握了中国读者阅读心理的,是冯梦龙而不是他。作过多种文本试验的胡适,也曾写过小说,我能记得起来的,也就一篇针砭国民性的非常概念化的《差不多先生传》,因为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故事,终于湮没。与他同在“五四”以后不久写出来的鲁迅的《阿Q正传》,由于有内容,有故事,而且是一个个有意思的故事,从此家喻户晓,成为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不朽之作。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小说,虽然是西方小说写法,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写法相嫁接的产物。但在植物学中,母本的基因,常常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在这个世界上,文学也好,具体到小说也好,有其相通之处,也有其民族的,本土的,传统的,习俗的种种不尽相同之处,因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是能够把握住冯梦龙的故事魅力的作家,便能拥有中国读者。
拿什么拥有读者?故事。而故事是什么?说到底,故事就是想象力。
对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中国作家来讲,你能指望他写出精彩故事的小说来吗?
就这么一碗米,你偏要让这位作家做出一锅饭来,他该怎么办呢?除了拼命往锅里添水外,还有别的什么高招吗?
于是,小说的粥化,便是当代长篇小说的普遍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