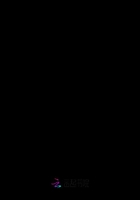1836年11月4日是普希金的朋友也是他皇村中学的老同学雅科夫列夫的生日。这一天同学们相约在酒店里聚会。大家喝着香槟,回忆着中学时代无忧无虑的生活,天真烂漫的童年趣事,大家谈笑着、畅饮着,只有普希金愁眉苦脸地喝着闷酒。
“怎么啦,诗人,沉默不语这可不是你的性格。”雅科夫列夫走过来关切地说。
“愤怒已经让我无话可说了,世界上还有这么恶毒的人吗?”普希金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着痛苦地说着,接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了那封匿名信:“你们瞧,这有多卑鄙!”
“噢,你是在为那封肮脏的匿名信生气,这不值得,这是搬弄是非的小人的卑鄙伎俩,你为它生气,不是太抬举他了吗?”雅科夫列夫善意地解劝着。
“不,我真想知道是谁这么卑鄙,我要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普希金气愤地说着。
雅科夫列夫接过那张纸仔细地看了又看,他经管皇家印刷厂已经五年,对纸张的品种、质量有相当的鉴别能力,他发现匿名信的信纸质地优良,没有水印,俄国目前还制造不了。于是他肯定地说:“这种纸是外国出的,进口时要纳重税,根据这一点判断,写这封信的一定是某家驻俄使馆。”
“那么一定是荷兰公使馆的盖克恩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和他的无赖养子一样的混蛋。”普希金气愤已极,没等聚会结束他就离开了饭店。
他要报仇,他要严惩诽谤者,他不能容忍那些卑鄙的小人侮辱他,普希金下决心要和丹特士拼一死活,他要和丹特士决斗。于是普希金给丹特士寄去了挑战书。他哪里知道这下他正中了敌人的奸计,那些沙皇专制的卫道士们,那些被普希金揭露过的人们,写这封匿名信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侮辱性的语言激他同丹特士决斗,借丹特士的枪杀死敢于向专制制度挑战的诗人。单纯的普希金怎么会想到他的敌人是这样强大,又这样狠毒呢?他只看到盖克恩这对无赖父子的丑恶嘴脸,根本没有觉察到隐藏在他们后边的更狡猾更残忍的敌人的快意的笑脸。他决心要和丹特士决斗了,朋友们千方百计地劝阻他,但却无济于事,他忙着选择枪支,忙着找决斗的证人,证人可真难找,因为只要是俄国人谁也不愿意看见伟大的诗人会遭到意外,谁都不想当这样的证人。普希金焦急地在街上走着,无意间看到了他皇村中学的同学丹扎斯,他长得虎背熊腰,是近卫军骑兵团的一个中校,在中学时代他是班里最差的一个学生,普希金平素跟他很少交往,这一次他见到丹扎斯就像见到了救星,他立刻拉着丹扎斯坐上了雪橇,丹扎斯莫名其妙地跟着普希金来到法国大使馆,因为丹特士的证人是法国使馆的官员。到了使馆,普希金向丹扎斯说明了情况,请他做决斗的证人和法国使馆丹特士的证人一起商定决斗的规则。
危险迫在眉睫,决斗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按照俄国的法律决斗是被禁止的。普希金准备决斗的事情早已闹得满城风雨,沙皇政府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为什么不阻止呢?因为在宪兵司令宾肯道夫看来,普希金用他的诗歌扰乱了人民的思想,危害着帝国政府的统治,如果在决斗中普希金被杀死,那么帝国政府正好少了一个敌人;如果丹特士被杀死,帝国政府也可以因此判处普希金流放,总之,这是沙皇政府巴不得的好事,他们怎么会阻止呢?
娜塔丽亚听到丈夫要去决斗的消息,吓慌了,她泪流满面,痛苦万分跪在普希金面前,泣不成声地说:
“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你千万不能去决斗,千万别去,我求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去决斗,我们还有四个年幼的孩子,他们需要父亲,萨沙,亲爱的你不能去决斗,这样你会死的……我永远爱你……”说着她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普希金,仿佛一松手,他就会跑了一样。
普希金痛苦地看着妻子,轻轻地把娜塔丽亚推开,讲了一句心里话:“娜塔莎,亲爱的,起来吧,难道我去决斗仅仅是为了你吗?我面前的敌人太多了。”是的,普希金是在同整个俄国的黑暗势力决斗。
1837年1月27日,这是个严寒的日子,苍黄的太阳无力地照着自雪皑皑的大地,狂风在呼啸,干枯的树枝在狂风中摇曳着,普希金一大早就起来了,穿衣,喝茶,然后走进书房,审阅稿件,为《现代人》杂志第五期的出版做好准备。奇怪,马上就要决斗了,生死未卜,然而他心里却感到特别轻松,多少天来困扰着他的问题总要有个结果了,他能不轻松吗?妻子和孩子们还在熟睡着,不能让他们知道今天自己就要去决斗,干吗搅了他们的美梦呢。这一天他整个上午都在书房里写作,还给一个叫伊什科娃的女作家写了一封信,请她为《现代人》杂志翻译剧本。
下午四点了,离决斗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普希金洗了个澡,浑身上下穿得整整齐齐,还洒了点香水,然后叫上仆人穿上皮大衣,坐上雪橇出发了,路上碰见朋友,普希金笑嘻嘻地打着招呼,仿佛不是去决斗,去送死,而是去赴一个期待已久的约会一样。
夕阳西下,已经是黄昏了,普希金坐在雪地的一个高坡上等待着。两个证人在厚厚的雪地上量出了十步远的距离,然后让他们两人脱下各自的大衣放在两端当界桩,并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交给他们,把他们领到离界桩五步远的地方,决斗就要开始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几只乌鸦在旁边的枯草树枝中盘旋着发出哑——哑不祥的叫声。
普希金和丹特士相对站着,眼睛都逼视着对方,这时丹扎斯一挥帽子决斗开始了。普希金马上跑到界桩附近开始瞄准,丹特士这个无赖不等跑到界桩就开枪了,一声清脆枪声过后,普希金一下子扑倒在作为界桩的大衣上。证人急忙跑过去,普希金慢慢地抬起头来说:“我的腿可能被打断了。”
对面的丹特士看见击中了普希金,高高兴兴地准备溜走。普希金大声喊到:“请等一下,我还有权利还您一枪。”
丹特士又回到原地,他侧着身子,把右胳膊放在胸前以便保护心脏,普希金握紧了手枪又一次瞄准了丹特士,枪响了,恰好击中了丹特士的心脏部位,但因为丹特士用右胳膊护住了心脏,他穿的又是军装,子弹击中了丹特士的右膊。由于受到军装上两枚铜扣子的阻挡,子弹的力量大大减弱,只击穿了他的两根肋骨。丹特士就势倒在地上,普希金看见对方翻倒在地,叫了一声“好极了”。便昏死过去,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白雪。
医生们守候在普希金身边,做着挽救诗人生命的最后的努力。这时普希金病体垂危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彼得堡,年青的大学生,近卫军军官,普通的市民……聚集在他家的周围,静候着他的病情报告,一个年迈的老兵回忆起当年库图佐夫元帅去世的情景,他说:“元帅死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探望啊!”是啊!普希金的真正的朋友是广大的人民,因为在残酷的世纪,诗人歌唱着自由,为被压迫的人民乞求过幸福。人民怎么会不热爱他呢。
1837年1月29日下午,这是诗人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好像觉得不那么疼痛了,普希金握着医生的手说:“达里,请把我扶起来,抬高一些,再高一些!好了!”他脸上带着微笑对医生说:“我刚才梦见在这些书架上攀登,我爬了很高,很高。太高了,我有些头晕。”说着他又昏厥过去。
古老的挂钟滴嗒滴嗒……不停地走着,“当当”敲了两下,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普希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艰难地对朋友们说:“生命结束了。”普希金就这样平静地离去了。他生命的火花是熄灭了,但他思想的火花将永远照耀着人间。
普希金去了,永远的离去了,上流社会对这个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逝世无动于衷,可是普通的百姓们,那些贫穷的小职员,那些半饥半饱的大学生,那些穿着羊皮袄的车夫,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却悲痛万分,他们失声痛哭。在自发地为普希金举行的葬礼上,人们高呼:“那个外国人在哪儿,我们要把他千刀万剐!”
沙皇政府害怕人民举行政治示威,命令连夜把诗人的灵柩运到他的故乡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并且严禁报纸发布消息。
2月6日清晨,屠格涅夫和老仆人尼基塔及邻居三山村女地主的两个女儿及宪兵大尉等人来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圣山,看着几个农民为普希金挖掘坟墓,为他安葬。地冻得那么结实只能用尖头的铁镐来刨,棺木安放好了,屠格涅夫流着眼泪抓了一把黄土扔在墓穴里,那几个农民和三山村的两个女孩全都哭了。太阳渐渐升起来了,北风仍然在吼叫着,送葬的人们都离开了,空旷冷寂的田野里只有普希金那座新坟的十字架,在狂风中摇摆着,没有墓碑,也没有花圈。实在普希金也不需要墓碑,他早就用自己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正像他在1836年《我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中写得那样:
我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通向那里的小路上,
青草不再生长。
它扬起自己不屈的头颅,
高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绝不会死去,
我的诗歌,我的灵魂,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
整个俄罗斯都会传颂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芬兰人,
还是孤僻的通古斯人。
我将永远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因为我用诗歌唤起了人们美好的感情。
在残酷的世纪,我歌颂过自由,
还曾为受苦难的人们,呼吁过同情。
是的,普希金是不朽的,正像他在自己的诗歌里所预见的那样,诗人已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一位哲人说得好:伟大的人物都是属于未来的。在普希金活着的时候沙皇政府迫害他,无耻的小人们诽谤他,他活得很艰难。但是在他死后亿万人都在纪念他,朗读他的诗篇。他的名字早已飞越了国界,今天全世界人民都在纪念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