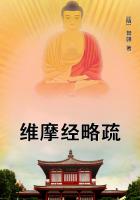雾色凝重,梁澍风尘仆仆地敲开天涵书院的大门,泛凉的手指,辘辘的饥肠。
解下包袱,沉浸在洗澡水兰花的幽馨。波光,轻扬柔水,褪去无边的倦意。
“小娘子,韩先生说不急,他在饭厅等你。”负责书院洒扫的女童梁理在门外禀道。
轻轻掩口,半梦半醒中,梁澍只道:“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自梁凡东游日本而去,书院的一切事务就交予他的书僮韩骆非。这个韩骆非,别看他弱冠年纪,可随从梁凡已有十余年,虽顶这个书僮的身份,但所学从未逊于梁凡的亲授弟子,这偷师的功夫在梁凡所阅人中无人能及,故而才才放心将书院暂交他打理。
师妹梁澍今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书院的门口,这是让他不得不吃惊的。住在国公府的她锦衣玉食,怎么会一身破败的来到这里,并且不带一个随从,莫非家里出了什么变故?没听说啊!
“师兄,师兄。”梁澍放下碗筷推了推他,“你发呆做什么?”
韩骆非恍过神道:“没事,没事,想些事情。”
“真是怪了,既说没事,又想事情。”
韩骆非言归正传:“雨卿(梁澍的字),你怎么想着来书院走走了?事先也不招呼一下。”
梁澍眯眼笑道:“我哥让我去苏门山走一遭,所以我就顺道来看看。一点小事而已,何必故意惊动你哟。”
原来不是家里有事,韩骆非舒一口气。
“说的什么话,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哪有你路过此地,我不闻不问的道理呢?!”
“我还不就是怕你客气,若不是三载没到过这里,我也就匆匆凝望一眼而去罢了。”
“如何就你一个人,你哥哥他也太不疼惜你了。本来就一个十三岁的豆蔻女子,还肯放你出门游学。国公府里不是有塾师,眼下世道又不太平,他也不知道担心。先生有两个女儿不假,可都是明珠在手,加上你平素标新立异,反倒让他更加忧心。”
“好吧好吧,全是我哥哥的错。不想师兄说话也越来越妇人牵肠挂肚了。”
韩骆非没好气道:“我为你好,你却嫌我聒噪。那苏门山的一些怪异事,我便不告诉你,好让你多吃些苦头。”
“怪异事?”梁澍一听有奇闻,立马浑身来了劲,“说说嘛!”直央到韩骆非叫苦了才罢休。
韩骆非命仆妇收拾碗筷,自己携师妹往书房走。
房内简洁敞亮,鲜有书陈,唯不过一两张琴,几十幅字画而已,从字迹上看,想来也是出自韩骆非的手笔。
“这苏门山,坊间传来确是名流众多,神乎其神却不是那么回事。”
“我爹年轻时两上苏门山求学而成,他亲口说,怎么就不是那么回事?!”
“话是不假,你可知先生第二次上苏门山,也带着我?”
梁澍点头:“是有这么回事。”
“那苏门山上,研习经义与通晓百家之人不可胜数,却鲜有人寻得他们。我只知那里没有一间书院,没有一个学生。”
“那又何为求学圣地?”
“三人行必有我师,所谓学,有时不过一个“偷”字。”
“啊?”梁澍不可思议,茶碗端起又放下。
韩骆非好似记得什么,欲言又止。
“师兄。”
韩骆非道:“武恒当初赠你的鸽哨可在身上?”
“嗯?跟这什么干系?”
“你就直说。”
“那是他平生送我的唯一一件东西,小巧可爱,我也常带在身上,现在就在包袱里。”
“那就好,那就好,虽不一定用得上,但我也放心许多。你晓得,我是不赞同你去苏门山的。以往苏门山可能是求学之地,但总有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时候。还莫如留在真定,要么去济南也成,那里你的好多师兄都在那里,照应你自不在话下,就论当地人才,也绝不差苏门山半分。又何苦死心眼去那里。”
“父亲所说,不敢不从。”梁澍郑重道。
韩骆非沉思片刻:“果真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么?”
“人各有志,亦各有命。我只知壮志当行,你何苦说些凄凄之语。”
“我打赌你会回来的。不为别的,我信我的想法,教书授业,老的那套法子该改改了。”
梁澍略略思索,道:“顺时生变,古来有之。今新人辈出,我想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