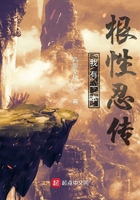王岘望着刘琦远去的身影,一时也是失神。再反应过来,乃是因听见一阵突兀地划水声,循声望去,只见脚下实则是一处向江面延伸出丈许的石壁,此时一条乌篷船正从石壁下划出,一人端坐船头,披着蓑衣,带着斗笠,缩着脖子,手执鱼竿扬手一甩,将鱼钩甩入江中,露出飘飘然的白色衣袂。
待潇洒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只听那人朗声说道:“普天之下,能用三言两语把荆州骗入囊中的也只有王宗之了。”
王岘闻言,不禁一笑,回道:“大战将至,还能如此安然垂钓于寒江的,也只有你崔州平了。”
说罢纵身一跃,跳到了船上,船身摇晃了一下,崔州平身边空空的鱼篓险些掉入江中。
崔州平以颇为夸张的姿势抓住鱼篓,全然失了风雅,白了一眼王岘,目光又集中在了鱼漂上。
王岘在这个老熟人面前毫不客套,大大咧咧地蹲在崔州平身边和他一起看着鱼漂,盯了半晌,才问道:“昔日姜子牙直钩垂钓,引来了周文王,崔兄今日效法古人,是想钓着哪条大鱼?曹孟德乎?刘玄德乎?”
崔州平不答,面露不屑之色,恰巧此时,鱼漂异动,崔州平登时喜上眉梢,抬手收杆,一条肥硕的江鲤挣扎着被提到了半空中。
崔州平麻利地将鱼取下,交给身边的随侍的小童,才搓着手对王岘说道:
“谁有功夫直钩垂钓,这天寒地冻的,他们谁的高官厚禄都比不上这条肥鱼炖的热羹。你既然来了,总得喝上几杯再走。”
说罢将王岘推进了舱内。
崔州平是个讲究人,船舱内衬都已经换上了挡风的兽皮,连地上都铺着没及脚踝的皮毛,将一江寒气阻隔在外。船中几案是鸡翅木,暖洋洋的金黄色上透着柔和含蓄的纹理,四脚被牢牢钉在地板上,防止船上颠簸造成的位移。桌上的青铜小鼎乘着滚烫的开水,温着一壶黄酒,烘得舱内如阳春三月。那个青铜小鼎王岘也认得,是几年前一伙逃至襄阳的散兵从一座楚国墓里盗出来的,那墓主人地位尊贵,不过是个将军,陪葬却用了七鼎六簋的诸侯规格。这桌上的,便是其中最小的一只,一个明器拿来温酒,倒是也只有崔州平能不嫌晦气。
二人落座,互斟一爵美酒,闲话三两家常,不外乎曹操入主襄阳后,旧地故友的近况。得知故人处境大抵照旧,唯有自己的老师司马徽天天被曹孟德相邀谋求治世之法,不胜其烦,生生是被盛名所累。
不多时,鱼羹已然烹好,用一只铜簋端上来,奶白色的鱼汤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带着黑皮的鱼肉半露出汤汁,和着寒冷的天气简直绝配。
崔州平喝着鱼羹,大赞美哉。
王岘失笑,这鱼羹的确美味,但崔州平的表现也过于夸张,像刚吸了五石散一样,于是揶揄道:“天下奇人非州平兄莫属,三公九卿之位在你心里都比不上这一口鱼汤。”
崔州平酒过三巡,双眼半眯着,口齿不清地说道:“宗之贤弟你也是不同寻常,天下霸主之多,在你心里也比不上刘琦呀。”
崔州平用手指点了点桌子,继续说:“刘琦是什么人,能耐,他没有;德行,他有,但是别人看不到。这么一个人却可以继承荆州这样让天下诸侯垂涎三尺的膏腴之壤、用武之国,这和当年揣着传国玉玺的孙文台有何区别,你拿走他手上的荆州,实则是又救了刘琦一命。为孙权谋荆州,不过就是个明面上的幌子,顺带的。”
王岘素来喝完酒就嘴硬,对此死不承认:“顺带拿个荆州?你高看我了。”
崔州平知道王岘的性子,也不再花心思反驳他,慢悠悠道:“既然你们刚才说起秦王子婴,那我也得给你提个醒,当年的秦王子婴,虽是将咸阳交给了高祖皇帝,但是关中之地仍然被西楚霸王收入囊中。今时今日的刘琦,势力恐不及当年的高祖,就凭他这个二十来岁半大小子的话当真可堪左右荆襄七郡?我怕就算刘琦能听你的,你最终能给孙权的,不过就是个’名’而已。”
王岘向后一倒,舒舒服服地靠在包裹船篷的兽皮上。
“的确是图个’名’,江东三军有提领荆州的实力,缺的不就是提领之名么。况且这名也不是想要就能有的。“
王岘说这话时一脸得意,崔州平不用猜也知道他口中那个想要提领荆州之名的旁人正是刘备,立刻明白了其中乾坤。
“说什么是谋划天下,说到底你还是想跟孔明一决高下罢了。”
王岘不以为然:“是又如何,天下诸侯势同水火,我和孔明各为其主,我与他的较量和谋定天下不也是一回事么。左右我们师兄弟几人,都是这乱世中的劳碌之人,比不得州平兄弟作壁上观来得逍遥自在。”
崔州平听出王岘的口气;觉得甚酸,很是有趣,便又卖了一个乖:“托你们几个的福,各自追随了孙、曹、刘三君,将成三足鼎立之势,我这观棋之人还得大呼:’精彩、精彩。’方才对得起你、孔明、元直三人的大才。”
王岘微微仰起头,满眼不屑。“刘玄德徒有汉室宗亲之名,而无军备重镇之实,有何资格与我主公相提并论。”
崔州平颇感意外,细想王岘之前对刘琦的态度,照应归照应着,可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人家什么好话;他这般回护什么人,崔州平是第一次见,立刻来了兴趣,有意激他一激:“你这怕是看低了刘豫州这个枭雄,他再不济,身边还有关羽、张飞、赵云,三员可以一敌百的勇将,还有个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诸葛孔明。你可还记得当日隆中对乎?”
王岘听到“隆中对”不禁哂笑:
“幸亏他的隆中对是个对策,要是副对子,我就送他个横批曰:纸上谈兵!诚然,依荆、益以成霸业固然可行。但是刘璋暗弱,张鲁失仁,不代表他们中任何一人会将益州拱手相让;刘景升不能守荆州固然也没错,但也不代表刘玄德就可堪大任。如今看来,是他刘皇叔既争不过刘琮,又打不过曹操,如今刘琦都要将荆州托付给吴侯,刘皇叔还想争天下,他凭什么?”
“哎,宗之,你自己听听你这口气;分明现在刘豫州是你家主公的盟友,怎么我听着,像他才是你的大敌一般。”
崔州平说着又为王岘斟酒半爵。
王岘拿起酒爵说道:
“迟早是祸患,倒也不足为大敌。”
他嘴上这么说,但心中隐约觉得自己对刘备其人的判断或许是有偏差的。仔细想来,当年檀溪的的卢一跃也好,今时长坂坡死里逃生也好,老天爷似乎总是不愿意收了刘备的性命。刘备是上天护佑之人,这还是他曾经亲口说的,本来为了恶心蔡瑁,现在看来马上就能恶心他自己了。
“既然是迟早,宗之也当着眼于现下,自古盟军相疑,纵有六国之众,也难扣函谷一关。”
崔州平一直以来独善其身,纵观天下,就越发觉得今时今日种种不过于历史的轮回。
王岘点点头,当是感谢崔州平的提醒,但是他对战果,并没有太多忧虑,直言:
“曹操不知江左,不通水战而贸然南下;蔡氏降卒,不得齐心而匆匆应战。相反江东子弟、荆州残部,身负保卫故土之责,必然会拼死一战。此番曹氏之败,将败于尽失天时地利人和。况且……”
王岘顿了一下,看着崔州平的眼睛,纵论时局,他没有多少底气,得从崔州平的眼神中得到认可才能安心。“况且,曹操虽强,但后患无穷,就如盛夏之花,固然灿烂,却也转瞬即逝。”
“且说来听听。”崔州平显得饶有兴致。
“其后患有三:其一,曹氏嗣子之位却迟迟未决。而曹氏重臣以次子曹丕为重,曹操却偏爱少子曹冲及四子曹植。长幼无序,储君不明,则必引群臣结党营私,兄弟阋墙,同室操戈之祸,重蹈袁绍、刘表覆辙。其二,曹操麾下文武之臣,长者居多,早已不复昔日战袁绍之盛。武者,当年五子良将多已年过半百,还能驰骋沙场到几时;子侄辈中,唯曹彰或可成大器,但奈何其为曹操亲子,若委以重军职权,必为后继之人所怨。有谋之士,郭奉孝(郭嘉)、许子远(许攸)已然仙去;徐元直心系刘皇叔,素来不为曹孟德谋;贾文和(贾诩)自张绣死后三缄其口、深居简出只为明哲保身,荀文若(荀彧)、荀公达(荀攸)世食汉禄,但凡曹操篡位野心再显露一分,怕是就不能为曹氏所用了。到时也只有程仲德(程昱)独撑大局,孤掌难鸣。而风头正盛的杨德祖(杨修),不过一诡辩之才,难当大任。一言以蔽之,后继乏人。其三,则为士族……”
王岘滔滔不绝说了许久,见崔州平毫无回应,便停了下来,问道:“州平兄另有高见?”
崔州平像是走了一点神,猛地被一问,忙正襟危坐,连连摆手:“没有,没有高见。愚兄是作壁上观之人,观棋不语,观棋不语。”
王岘听出言语间的敷衍,有些赌气地说道:“你也不过是想看看我和孔明孰高孰低罢了。的确,孔明兄才华是胜过我,但他偏要给自己选条最难的路,自己去造一代君主。我没他那闲情逸致,家父曾言大汉气数已尽,刘备他依托汉室之名能走多远?曹操挟汉室天子之名如今风光无限,日后也难免作茧自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吴侯据江东三世,群贤景从,百姓亲服,邦国得兴,孙氏之功,非托汉室之福。不同于曹刘将功业建于朽木之上,江东的根基为坚石,也唯有坚石可撑起庇护天下的万丈广厦。崔钧兄您且看着,这局棋,我赢定了!”
王岘这番话说得激奋且尖锐,他幼稚的争强好胜之心不太在人前展露,却总是在崔州平面前失态。
崔州平倒是习惯了王岘这种状态,缓缓饮了口酒,款款道:“可这天下到底不是一盘棋。”
言语间,竟还有一丝从未在崔州平脸上出现过的落寞,倒是一时让王岘无言以对。
不知是不是察觉到了气氛的尴尬,崔州平转移了话题:“听说你在江东训练了一支新军,此番是否会迎战曹军?”
“这是自然。”提到他的新军,王岘颇为自豪,跃跃欲试——外人只知道,这支军队善骑射,但实则除了上天、遁地无所不能。其实,仔细想想,曹操不是也有发丘中郎将,那么遁地也未尝不可。
“如此,等大战结束,你便懂了。”
崔州平眼底闪过一丝忧虑,但立刻又换成了那副参透天地的潇洒,说出的话也玄而又玄,好似只缺一缕清风,此人就能成仙。
“懂什么?”王岘问道。
崔州平挥袖指向船外,曰:“乱世。”
“九月,魏公曹操入荆州,得表众,势甚盛,群臣畏惧,多谏帝迎之。岘夜诣帝曰:昔,袁绍会天下群雄讨贼;诸侯恐惧不前,唯君先父不惧强、行天道、破洛阳。君侯今富有江左之地,不战而降,恐有愧先公文台之德。而中原之军不识水战,君侯可依天险,葬虎狼于江河,此诚君侯问鼎之时也。
帝大悦称善。
是岁,帝谴鲁肃之夏口以盟刘备,岘随之,诣刘琦。琦,荆州牧刘表长子,岘旧主也,忠纯雅量,仁义之士。岘遂以荆州百姓安泰许之,琦以为然,献荆州于帝。”
——《吴书·王岘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