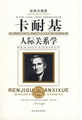念自变乱以来。军民茶苦,如在水火,擅坚执锐。卒岁靡宁,行齐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于锋刃,供忆之众,复固于征精。朕悯恤民艰,不思辄加额赋,闻施权宜之令,用济征缮之需,意在除残,事非获已。而身处宫寝之内,外廑闻闽之依,中夜屡兴,旰食不眠,正焉思治,八载于兹。夸群逆削平,疆囤赢定,悉翦除历年之蟊喊,永消异日之隐忧。甩是荡涤烦苛,雏新庶正,大沛宽和之泽……诞告天下,成使闻知。
这是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完全是从清朝的立场对这一事件做了总结,观点未必尽正确,事实未必尽真切。不管怎么说,清朝胜利了,吴三桂失败了。清朝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力来按自己的政治需要书写历史!
十四、“诸逆”授首,后代子孙永为奴
吴氏政权的覆亡,招致整个家庭的毁灭。吴氏是一个庞大的家庭,几乎没有一个善终的。除了吴三桂和他的妻子张氏死于昆明城陷之前,免受斧钺之苦,其余无不死于非命:其子吴应熊、其孙世霖、世璠,侄吴应期、女婿等等。或惨死于阙下,或毙命疆场,或饮刃于宫室,或相残于萧墙,而他们的家属或株连同死,或进人官府为奴,连吴三桂的美妾亦被夺占。他储积的庞大家产也于一日之间化为乌有,结局是很悲惨的。吴三桂的部属、同盟者,其首要分子和骨干也几乎难逃厄运,纷纷被押上断头台。这是吴三桂失败的直接后果之一。
吴氏满门灭绝,并未使圣祖和廷臣们感到丝毫怜悯,相反,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他们看到吴氏家族一颗颗人头落地,报以满意的欣慰。政治斗争如同战场上两军格斗,你不杀他,他一定会杀你,二者必居其一。谁若手软,或稍一迟疑,性命就会被对方取去!所以,同自己的最危险的政敌作殊死之斗,根本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有点滴的同情,要的是铁的手腕,流血的镇压。这才是一个政治家的特色。圣祖当之无愧!战争已经结束了,一切生死予夺大权重新操在圣祖和朝廷之手。本来,乱源业已清除,照理说,一切都成为过去,应面向未来,如何治理国家。但是,事情远未结束。他们还感到只镇压吴三桂一族还是不够的,必欲把其党羽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掉,如斩草必须除根,不留一点令人不安的隐忧。于是,清洗与镇压同时进行……
在战争进行期间,圣祖为了分化、瓦解和孤立吴三桂,一再施以招抚之策,百般诱使“归正”。政策相当宽大,待遇相当优厚。不管谁在吴氏政权中任何种职务,犯有多么严重的“罪过”,只要放下武器,立即会得到极优厚的待遇,对以往之事,一概免究。圣祖表示,“朕决不食言”,可“昭之日月”。这些诺言,都行之于文字,载入件件诏书之中。可是,当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特别是在攻下昆明之后,圣祖马上想到处置已降的吴三桂的党羽,时机已经来到。在他的指示下,朝廷开始甄别,以种种理由和口实,将已降的原属从叛的骨干分子逐一查出,定罪处死。举其要者,叙其原委,以明历史真相。
耿精忠与其子耿显诈及骨干分子曾养性等被凌迟处死,家产没收。对尚之信及有关人员作出判决:“同谋者尚可喜、妻舒氏、胡氏从宽免死,并免家产籍投;尚之孝、之璋、之隆等都从宽,革职枷责。”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接亲王,从宽赐死”。
康熙十九年七月十七日,钦差奉命至广州,向尚之信宣读完旨意,赐一条帛,令其自尽。上午七时许,尚之信气绝身亡,葬于广州城西报资寺后山下。他的弟弟尚之节、长史李天植等人被押上刑场斩首。尚之信等人的妻子都籍没人官。圣祖又指示,尚之信所有资财,用来充作军饷;过去属平南王的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两,“当尽充国赋,以济军需。”
从历史资料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康熙对耿精忠、尚之信的处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圣祖撤藩,是既定国策,体现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当然也符合封建中央集权的要求。耿、尚连同吴三桂及其子孙,再推而扩之,累及他们的部众,都成了撤藩的牺牲品。
圣祖对他们采取的政策,前赦而后治,不能不认为是言行不一,背信弃义。在战争进行中,圣祖千方百计地招抚,许以种种诺言,无论有多大“罪过”,概行宽免,一律不究,官复原职,待遇不变,甚至稍有微劳,即加官晋爵,极尽笼络之能事。他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吴三桂,并借用他们的力量来消灭吴三桂。当他大功告成时,这些人已无使用价值;相反,又视此等曾从叛的人为心腹之患,痛恨起他们曾从恶反对朝廷,尤其对其首要分子和骨干不肯放过,必罗织罪名予以彻底消灭掉,才肯罢休!
三藩以外的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王辅臣,他的结局,也朱能逃脱一死。不过死法不同而已。
据清官方史书记载,王辅臣系“病故”,未曾受刀斧之伐。其实不然。他这个人颇有政治头脑,当康熙二十年七月,清军正围困昆明时,圣祖下诏,令他随经略图海进京“陛见”,他便料知此去凶多吉少,打好了主意。行前,他命人取出库中银两,各分成一封,多的达百两,少的也有数袭,又罢免王继贞之职,其家属归旗。由此可知,圣祖令王辅臣进京陛见,是不怀好意的。他死后,其婿薛英等请携王辅臣骸骨及家口回平凉。兵部不准,令将王辅臣骸骨及家口一并送到京师。这不难看出,朝廷本意是把辅臣调来京师,准备拿问的。比较起来,耿精忠、尚之信却看不清楚“狡兔死,走拘烹”的道理,王辅臣倒有先见之明。早在奉命进京之前,王辅臣随图海驻汉中,圣祖频频给他父子俩加官进爵,他不但没有欣喜,却惶惶不安。越发疑惧朝廷此意不善,曾白缢死过一回,被救醒过来。直到这次叫他进京,便预感朝廷要跟他算总账,不会放过他,让他不得好死,这才决心以此死法,哄瞒朝廷。使各方都不受牵累。
祖泽清,是明束辽东明将祖大寿第四子,他据广东高州响应吴三桂,康熙十六年“归正”,次年叉叛。尚之信奉命率部迎击,曾一夜驰行一百八十里抵高州,祖泽清携家口遁入山中。十八年四月,圣祖明示:凡属从三桂叛的各处大小官员,不管出于何种情况,只要归降一概宽免。惟祖泽清父子受国家厚养,前叛时以为出于不得已,而降后复叛,可知他们父子“甘心从逆”,情罪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务令各路大军搜山擒获。至八月,祖泽清和他的儿子祖良梗等被搜出,押送京师。十九年二月,父子都被凌迟处死,他的几个儿子的家口也都被籍没为奴。
从康熙二十年年底攻下昆明后,至次年二十一年五月,圣祖又逐批处决了吴三桂属下已投诚的将吏,他们是:
原任贵州提督李本琛,以“从逆”论处,判磔刑,他的孙子李象乾、李象坤和民籍亲弟之子李济善、李济民一律处斩;
吴三桂任命的将军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即行处斩”。原任清镇远副将、受吴三桂封为将军、镇远伯江义,以“情罪甚重”凌迟处死。以上被处死者的首级皆“悬示”。他们各自的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一并处斩,家产籍没,其妻及未及成年之子,查交内务府,其余一般人员可分发山东、河南、期广、江西安插。
胡国柱、王绪、李匡已自缢、自焚死,他们的家属投诚。圣祖以胡国柱三人情罪重大,伊等子弟法难宽宥竹,“悉行处斩,妻女、家口、财物籍没,送交内务府。”
彭时亨、谭天秘先叛于四川,后投诚,复叛,“情急归降”,以“罪恶重大”,“即凌迟正法”,割首级示众。
仅据清官方记录,满族人获逆罪被处死的有三人,原任布政使成额、笔帖式书舒处以绞刑,笔帖式巴席因参与甘肃巴三纲之乱,又系满洲人,“情罪甚为可恶”,判斩首,立即执行。
以上备案犯皆系要犯,而没有载人官方记录的被处决的“从叛”或“胁从”之人,又不知凡几!这从圣祖的原则规定,可以知道被处死的人非常之多。这条规定是:“凡逆属旧人,及副将以上,悉令进京;参将以下,分插四省。”(指河南、湖广、江西、山东四省)又补充规定,其云南或别省后投靠到藩下的,释放为民,免迁徙四省安插。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都是“为逆贼济恶之人,务使离逆贼旧踞之地,斯根株清而萌檗不复生也。”这就是“斩草除根”的意思。
吴三桂藩中,副将以上的将官,究竟有多少手尚难统计,估计不会少于干名。所谓“逆属旧人”,是指“吴三桂名下真正家仆旧人”,在云南或别省投靠来的人,不在此内。一句话,清朝视为危险的是从早年就追随吴三桂、与他共命运的那批人。如在辽东时期,或入关后,辽东人投到他门下而被收留下来的人,清朝还把“逆贼所属匠役人口”,也包括在这批人之内。他们因为跟随最久,与吴三桂已结成了共同的利益,这些人才是吴三桂的“真正家仆旧人”。他们“助逆”最多,但未曾领过兵,未同清军对抗过,一律处死,处分太过;如留在云南,惟恐不知何时故态复萌,敌将这批人悉数迁移北京。他们的人数远比副将以上的人多。据平吴后任云贵总督范承勋报告,他“通查伪包人(指王府服役人员)数”,据原档册报官役人共一千一百六十四名,而实际起发京师的达六千三百零五名,还有续收候发的人口为一百二十名,原藩下兵士,原档册报为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八名,而已起发赴京师的则有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二名,还有一百八十一名尚待续发。这就是说。实际清查出来的“真正家仆旧人”,包括其兵丁,比原报官记录在册的人数要多出不少。这说明,吴三桂当初有意隐瞒了藩下大量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