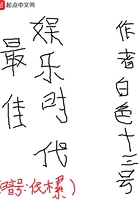“啼姑娘,奴婢送来些熏香驱蚊。”
夜还未深时,锦花楼大大小小的楼阁都已经燃满了烛台,亮如白昼。年轻的侍女小心的敲了敲门,询问。
“进来吧,门没有锁。”推开门的时候,啼女正握着一卷竹牒,橘红色的烛光下,认认真真的品读。
“啼姑娘,天变寒了,还是加件衣服吧。”侍女放下手中的熏香,点燃后,对着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客人提醒。
“嗯!谢谢你。”或许看到了一些精彩的地方,案上的女子拿着朱笔埋头记录着什么竟顾不及抬头,只是微笑着点头示意。
“那啼姑娘早些歇息吧,奴婢告退了。”轻轻作礼,侍女弯腰倒退,却还是忍不住又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瞄着了案上女子。
关上房门,侍女不甘心的透过门缝瞧了一眼——果然,这位新来的女客人很像阁主房里画像上那位女子呢,连笑容都很像,难不成……难不成就是一个人吧?想到这里她连忙拍了几下嘴。
呸呸呸,这怎么可能呢,听那些早年入阁的侍女说,在几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本是要嫁给阁主的女子已在一场混乱中不幸丧生了,尸体据说还是阁主亲自掩埋就在阁中禁地内的某个地方呢,啼姑娘又怎么会是她。再说,以前在阁主房间打扫时见到的那个画上女子,比起这位啼姑娘来虽长的七八分相似,却还是有些不同,比如说画上的女子笑起来眼睛里尽是活泼,举手投足的小动作都显得十分俏皮可爱,可是,这位啼姑娘却淡雅安静的像是常年养在深闺中的大家闺秀一样,这又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人呢?
叹出一口气,侍女用力晃了晃脑袋,还是不要在胡乱猜测的好,要是被阁主知道了,可是要被杀头的,想起那个因为和旁人议论画上女子的容貌而被阁主亲手杀死在广场上的老仆,侍女不由的又打了一个寒颤,下意识加快了脚步。
夜渐深,楼阁静谧的只剩下烛火燃烧的声音。
忽地,起了一阵微风,穿过楼廊,‘砰’的一下吹开了侍女刚刚关上的门,屋中书柜上纸笺顺着风被吹的满屋都是,啼女赶紧用手中的竹简护住案上摇摇欲坠的烛火,不小心的,手中朱笔刚沾的墨水落在了案上,溅起无数的墨水花。
“哎呀!”啼女连忙坐起,却已经晚了,洁白如雪的裙裾,盘踞着几点朱红的墨水,一如深冬落如雪地里的残梅。
“看来,你竟和她有着完全相反的性格!”
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啼女拿起手帕擦拭着裙上污痕,听到后抬起头,又复吓了一次,本来空荡荡的屋子里,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一个人。
是一个看起来很神秘的男子,不同于玉阁主的冷淡,他竟带着微笑,若有若无的,神秘的像是一眼看不到边际的晨雾。
“她?”听得他那样说,啼女又想起了玉阁主说过的话,同样是提到了一个‘她’,‘她’是谁?啼女心下有了些好奇,对于这个突然出现带着许多微笑的人反而没有了警惕。
踌躇着,正要问出口的时候,却已又听见了像是带着微笑的声音,“她是这处锦花楼的主人”男子微微笑着,指了指桌案的另一端“也是你身旁那柄琴的上一任主人。”
啼女下意识看向那张古桐色的琴——那是在她来到这里或者说是被救到这里的时候,那个青衣阁主送给她的,而她随身带出来的那张琴被火焚在了那个地狱一样的地方,想起这些,啼女的胸口不由的有些起伏,那是她这一生中经历过最害怕的事情。
是在去云都的路上,她正要去参加‘乐岚节’——云都十年一次的乐岚节据说是天下所有喜爱音律之人的盛事,而她之前在苦索《雪莲引》的最后一音数月无果后,一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顿时生出了想要去那里碰碰运气的想法,就在她兴致勃勃说于琴骨、幽篁听后,却不料直接遭到了否定,说是担心她的安危。可是啼女还是心有不甘心,便又去找潇湘子,谁知一向宠她的潇湘子这一次居然也持着反对的意见。这下连潇湘子都反对了她就再不敢去找萧姐姐。可是自从有此心思后啼女自己竟也无法抑制,终于,那一日,她下定决心后偷偷跑出了那些林立的楼阁,抱着琴,第一次踏出那个曾经只能远远看着的大门,他们不愿她去,那她便自己去。
可是,啼女那里知道围墙外面的世界竟是这般大的天地,她自幼养于深院,又那里知道世上居然还有一种叫做钱财的东西,然而让她更没有想到的却是人说出来的话竟然还会有假的,只是抱着一张瑶琴的她,天真到相信了那些说会带她去云都的人,还为此开心了好久好久。
就在被送入那个院子的时候,她还对着那些送她来到这里的人屈膝万福道了声谢谢,当即弹了一首乐曲作为回报,那时她很天真的以为这里就是云都了,甚至就在那个自称云都城主的人取走了她怀中的瑶琴时她都还在相信这些都只是习俗而已。
她的这种认为一直持续到那个肥胖的城主把她关进房间后去扯她身上的衣衫时,她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到底要干嘛,那一刻,她只是吓得不知所措,闭起眼睛躲在床脚的角落一动也不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影破窗而入。
那个青衣长发的公子,抱着她点足飞起,一句话都没有说,不知为何,她竟就那样信任了他,任凭他抱着一句话也不问,直到她想起那张他唯一带出的瑶琴还在那里,回身看时后面已是一片火海,她的琴恐怕已葬在那里,他说他会再送她一柄新的,就那样简单的一句话,她又相信了。
他抱着她飞了很长的时间,没问她的名字,没问她从哪来为何会在那?甚至都没告诉她又为何会知道她在那里?他只是静静的抱着她,而她就那样在他的怀里靠着他的胸口,安静到静静的风声里只剩下心跳。
然后,就在这个楼阁里,她用着他放在房间里的瑶琴,在满楼的落红里弹起《雪莲引》,才知道原来他叫念秋碎。
其实他不用告诉她他叫什么啼女也是知道的,‘阁主大人’——在琴骨逼着她背下的那些苦涩绕口的名字里,只有一个阁主,秋玉阁,玉阁主,念秋碎。琴骨告诉她,那个一身青衣的玉阁主是她此生最大的敌人,大到势不两立。敌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会是自己的敌人呢?她问琴骨,第一次,那个背着琴格的男子在她面前皱起了眉,也是第一次,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就转身离开。
一个救下她的男子,怎么会是她的敌人呢?啼女想不明白。
轻轻的抚摸着琴身冰一样的弦,啼女在指尖感受着那股淡淡的寒气,原来,这把玉阁主送来的琴,她才是它的主人。
“她不及你安静,若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恐怕早就大叫出了声。”男子淡淡的笑着,就连声音里都带着些笑意一样:“锦花楼里的花也尽是她种下的,她喜欢弹琴做曲,更喜欢花草的香气,于是,我们的阁主大人便筑下这处锦花楼送于她。”
她一定很美吧?曾经的那位女子,是站在她现在的地方,弹着这张古琴的么?想来她定是那位青衣阁主的情人了,啼女想着,心头微微一暖,问:“那她现在……”
“她已去世多年。”蓦然的,微笑的男子不知从何处取来一朵花瓣,夹在指尖静静的看着,打断了她的话。
去世?啼女抬起头,他依旧在笑着,可是,啼女却依稀的看到,他在看着花瓣的月牙一样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轻微的恨意,是恨天地不仁夺去了她的性命?还是再恨些其他?
“啼姑娘是不是想说红颜薄命?”反复观看着手指间的花瓣,男子若有若无的微笑着,猜出了啼女的心思:“想来……形容她原也只有这个词是最合适不过的,只可惜……。”
男子顿了一下,笑容变得越来越深,深的像是看不见底的深渊一样:“像她那样的人,却是远远配不起这几个美丽的字眼。”
那样的语气,居然带着好不加掩的恶意,啼女的心口忽然一紧,听到后面紧跟着的冷笑声,再也忍不住皱了皱眉:“既她已成为亡人,公子又何以出言伤及?”
“出言伤及?”那人蓦然定住,突然大声笑了起来“你可知,她不但要骗去念秋碎的心,而且还要捎上他的性命。”手指间的花瓣徒然裂为两段,他微笑的眼睛瞬间变得凌厉的像是刀剑一样,盯的啼女心头发麻。对于无数人连正眼都不敢瞧一下的秋玉阁阁主,他居然也直接叫出了名字。
他冷笑着,骤然弹出手指间裂成两半的花瓣,花瓣贴着啼女的鞋尖,‘夺’的一声钉入地板。
“啊!”啼女一惊,下意识的后退一步,不小心碰到了后面书柜,一本竹简掉落下来,很不幸的碰落案上烛台,清脆的碎玉声里,烛台碎成了数段,燃着的烛油倾进漫地的纸笺,唰的一下,阁楼里瞬间变成了火海。
“你……你真的是宫商坊坊主?”看着已然呆愣成木偶的啼女,那人有些不可思议,:“能有如此琴艺自是不会错的,不过,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的修为?”听不得他接连的问题,啼女只是缩在一旁,呆呆的看着越来越大的火光,眼睛里泛着泪水,不争气的,几欲哭出声来。
“呵呵……有谁会知道名满天下的宫坊主远不过只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他盯着啼女,冷笑:“箫若绮那个女魔头难道就靠你来维持宫坊主三主之中第三主的名号?”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恶作剧,男子唇角的笑意渐浓,微红的火光把他的笑照的清晰无比:“宫商坊为何不都转行去乐坊,那样岂非更是师有所长!”他笑着,毫无顾忌的嘲笑。
“啼女!我记下你的名字了!”大笑之中的讽刺夹渣着漫天的火光,他笑着轻轻挥了下衣袖,莫名的,燃着的烈火在他挥袖的动作里徒然烟消云散,燃着的纸笺静静的飘散在地,连一点烧着的痕迹都没有,刚才发生的一切在啼女的眼里竟完全像是幻觉一样。只有刚才那盏摔碎玉烛台依旧躺在地板上,暗红色的烛油倾出了一朵血液一般的红梅。
这突然的骤变,让啼女惊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的捂着嘴巴,一分分的听着他的嘲笑。
“水飞红,溪水的水,飞雪的飞,血红的红,希望你能记下这三个字,因为……这是我的姓名。”唇角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他定眼笑看着那个绝美出尘的女子此刻的狼狈,像是又想到了什么一样,惊声:“哦……对了,忘记告诉你,她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男子故意停顿一下,嘴角扬起更高“这个身份……也是宫商坊坊主,跟你一样呢,真是……巧的很!”
风又吹了起来,门轻轻的关上,没有发出声响,他的嘲笑声逐渐模糊。
昏暗的屋子,燃着的熏香飘着袅袅的烟气,缥缈着散在了整个房间,啼女曲卷在书柜旁角落,抱着膝盖,终于,泪水再也忍不住的滴了出来。